柴祖衡、君衡兄弟二位见访,说今年是他们的父亲青峰(德赓)先生诞辰八十周年,要我为纪念集写一篇文章。我立刻答应了,我是该写了。
青峰如果活着,都八十岁了么,这使我大吃一惊。我总记得一九四四年我们在白苍山初相识的时候,我还是二十二岁的青年,青峰那时三十六岁,要按现在的标准来说,也还算青年,充其量也只是刚刚进入中年罢了。我们贴邻而居,朝夕相见,年龄相近,很谈得来,常常两人一同上街买米买菜,间或也同到黑石山赏梅花。我们都是“夜猫子”,差不多每晚都要谈到半夜,在一个小炭炉上用小陶壶烧开水冲茶,每一小壶恰好两碗,够一人沏一次,再要沏时再烧。后来他赠我的诗说:“剧谈吾可续,豪饮子宜先。”我赠他的诗说:“回首空山风雨夜,可能还结对炉缘。”说的都是那时的情景,“对炉”“豪饮”指烹茶和饮茶,并不如通常的用法指煮酒和饮酒。此情此景如在眼前,青峰如果活着竟已八十岁了么?然而青峰没有活到今天。“文化大革命”中,他受的磨难比我多,他是直接与翦伯赞连得上的“反动学术权威”,比我这个“摘帽右派”有现实价值,一九七〇年他在苦役中死去之年才六十二岁,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四岁呢。
那么,我怎能不趁未死之年写出我说的话呢?死者已矣,我是说给生者和来者的。
我们相识在白苍山,那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院址,在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现在听说成渝铁路已有白沙一站,当时那地方却很偏僻,从重庆去,只能乘小火轮,溯长江而上约九十公里。晨发暮至,两头不见太阳,途中有险滩,覆舟惨祸时有所闻;从白沙去重庆则是下水,当然要快一些。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创办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初,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时,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存在的时间很短。院址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抗站胜利后虽迁往重庆附近的九龙坡,其时的重庆又不是战时首都了。学院规模很小,一共只有六百多个女学生,当时除了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以外,纯收女生的高等院校似乎只有这一个,被人嘲为“女儿国”“大观园”。因为这些缘故,很多人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学院,知道一点的人又往往把它的名字错写成“白沙女师”,其实它的名称就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不多不少就这八个字。当时也有人口头上随便简称为“白沙女师”,可是院名上本无“白沙”二字,而且“女师”似乎是中级师范学校,所以我们自己不这么简称,我们简称曰:“女师学院”,或“女师院”,甚至干脆叫“女院”。
现在回想,着实有些奇怪,那么一个历史短、规模小、地方偏、设备差的学院,不知怎么竟有一个很可观的教师阵容。院长是谢循初教授,教育系主任是罗季林教授,教育系还有鲁世英教授,作为师范学院的首席系的阵容就是如此。此外,英语系主任是李霁野教授,历史系主任是张维华教授,音乐系主任是张洪岛教授,数学系主任的萧文灿教授……都是各该学科里面数得着的。国文系的情形,我当然更熟悉了,历届的系主任是胡小石教授、黄淬伯教授、台静农教授。台原是国文专修科主任,魏建功教授则是国语专修科主任。这两个专修科与国文系关系密切,若分若合。魏后来又当教务主任,仍在国文系授课。国文系当时的副教授有吴白匋、宛敏灏、姚奠中、詹锳、张盛祥等,青峰是历史系副教授,实跨文史两系。他们年龄相近,青峰还是居于中间的,现在只有青锋先去了,别的几位幸而都还健在。当时女师学院各系的讲师助教,也是济济多才。歌唱家张权当时是音乐系助教,我有幸在女师学院学生大饭厅(一座大芦席棚里),听过她的独唱会,也许是她第一次举行独唱会吧。以上说的只是我在那里时的情况,不包括以前和以后的。先前历史系主任是梁园东教授,音乐系主任是杨大钧教授,在国文系教过的还有佘雪曼,在音乐系教过的还有郑沙梅,我去时都已经走了。我没有随学院迁至九龙坡,学院迁去以后,院长换了劳君展教授,听说还有萧蔓若、黄贤俊等先生到国文系教过,我都不在那里了。
总之,这是一个物质上很简陋而又很有学术空气的环境,我以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由黄淬伯教授的推荐,受聘去教书,给我的聘书上竟也写的是副教授,我实在很惶恐。大学的助教我当过,就是给黄淬伯教授当的助教,替他改作文习作,并未讲过课,现在跳过了讲师来当副教授,正如去年我在一篇小文中说的:“回想初登讲台的时候,心理真虚得很。那是一九四四年,自己明白只有高中二年级的学历,一年小学教师、一年半中学教师和两年半大学助教的经历,一下子就对着(有比我还大)学生讲起课来”,说的就是初到女师学院的情形。在女师学院的那几年,我是抓紧一切机会,向同事的前辈如台静农先生等好好学习,也抓紧一切机会向老长兄们学习,其中因贴邻而居,于朝夕相聚中承教最多的一位老长兄,便是青峰。我离开女师学院以后,曾作有《白苍山四君咏》,怀念我最难忘的四位:
午醉先生睡正酣,
晚凉心事晚眠蚕。
文章总向秋风哭,
又到人间歇脚庵。
(台静农伯简)
横眉向我说无生,
下智昏尘听未明。
进退去来宁有碍,
转看破衲是非情。
(罗志甫破衲)
四十生涯浪漫过,
青衫落拓伴清歌。
词人枉自留灵锁,
一例匆匆可奈何。
(吴白匋灵琐)
豪谈高唱不知慵,
起看阶前月影重。
话到白苍山上事,
天荒地老忆青峰。
(柴德赓青峰)
入洛机云未敢俦,
追随端属少年流。
他时感旧渔洋集,
可附狂奇左道楼。
(余曾有室名曰左道楼)
诗不成诗,人却是永远难忘的。“天荒地老”不是泛泛之言,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话还是得从“豪谈高唱不知慵,起看阶前月影重”说起。
一九四四年我来到女师学院,已是残秋。下船后上白沙镇码头,再走出镇街,还得走五六里路,才到白苍山。女师学院便建在山上,无非是几十排土墙瓦顶的校舍,还有一些更简陋,是编篱糊泥的,学生的大饭厅干脆是个大芦席棚,开会时则用作大礼堂,所以张权女士在那里举行独唱会。电灯当然没有,点的是严监生那种桐油灯,夜行则用纸糊小灯笼提在手上。巴山多雨,通常夜雨昼晴,伞固然不可少,更不可少的是当地出产的桐油的钉鞋,走在任何泥泞的山路上都很把稳,虽不美观,女学生们却不得不穿。学生宿舍在半山以上,那座芦席棚的饭厅兼礼堂靠近山麓,每当雨后她们下山来吃饭时,几百双钉鞋的声音之流,以及晚间开什么大会时,几百盏手提小白纸灯笼的光影之流,我以为可称白苍山的两景。我曾有一联诗句:“半山灯火清歌里,一径蘼芜薄醉时。”不一定就是写这两景,然而不妨说有这两景的影子在内。我们当教师的还多一项随身法宝:“手杖”,这也是雨后和夜间山路上有很大用处的;我尤其行动不离,为的是要显得比实际年龄尽量老些,较便于置身在女子学校之中,置身在老长辈老长兄的行列(当时我不得不把年龄报成三十,实际年龄二十二岁)。有一次我和青峰一同到镇上去,他还带着女公子令文,那时还是个小女孩。我说:“你看我们两人,一样的钉鞋,一样的手杖,一样的小灯笼。全是一样;不一样的只是你戴了眼镜,还带了一个女儿。”他说:“眼镜也许你不久就会戴上,只是你要有这么大的女儿,却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是不是丢掉这根手杖吧,还可以快一点。”那时我还未婚,他开这个玩笑,大概是猜到了我手杖不离手的用意。
我们从初次相识,到能够这样闲谈开玩笑,没经过多久。我们的宿舍是贴邻,我第一次看见青峰,是到校次日礼节性拜访同事的时候,他正坐在小竹凳上洗一大盆衣服,璧子夫人手上生湿疹,不能下水,全家老小七口的衣服都是青峰包洗,他一面揉着搓着,一面兴会淋漓地和我谈着,没有一点辛苦狼狈的样子。这个初次印象,我是非常深切的。后来二十年的交往,证明这个初次印象没有错,青峰什么时候都是那么精神奕奕、兴高采烈,至少在我心目中这是青峰一贯的形象,此刻我在记忆中怎么搜寻也没有他意气消沉、怨苦叹惜的形象。
其实,我们初识时,青峰是很辛苦的。抗战爆发,平津沦陷,青峰留在北平,在辅仁大学教书。当时留在北平的高等院校中,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因为是外国教会办的,还有中国大学那种私立大学,没有被敌伪政府接管,不算伪校。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势力对辅仁大学的压迫日益加重,青峰忍受不了,终于偕同璧子夫人,携带四个儿女,冒险潜逃出来,投奔抗战大后方。经过西安,辗转来到白沙,大约也是一九四四年下学期,他到校就在我之前不久。这一路的辛苦不必说了,一点积蓄也用完了,当时国统区正是经济混乱,知识分子生活困难之时,青峰一家六口,加上一位岳母老太太,负担之重超过了女师学院我们相熟的几家中任何一家。这里情形他对我从不隐讳,可是他和璧子夫人仍是什么时候都那么兴致勃勃,高谈大笑。他们对于国统区的黑暗,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特别失望和愤怒,时时痛斥,可是并不羼杂着旧知识分子的“恨恨而死”和小市民式的“愤愤不平”。这种态度,尽管我自己做不到,或者说,正因为我自己做不到,我特别地欣赏。我初到白苍山,冷雨连绵,心情就很坏,有句云:“雨洗苍山白,天招下士魂。休歌迎子夜,按剑对黄昏。”可见一斑。难得一个初冬下午,天放晴了,我独坐在室内,听见青峰在隔壁大声吟诗:“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这是陆放翁的沈园诗,也是我一向爱吟的。我便走过去谈天,他将他的诗稿拿出来给我看,我才知道他自己作的诗就是放翁一路,所得很深,入蜀途中诗作特别亲切有味。谈着谈着,他忽然提议我们各自回房间去作绝句四首,交换了看过,再同去黑后山看梅花。我作的末一首便是以这样两句作结:“等是无聊消永昼,不如乘兴探梅花。”这可以就是我们“以诗订交”之始。我那句“豪谈高唱不知慵”,企图写出他老是兴致勃勃的形象,本来该是“高吟”,限于平仄改为“高唱”,勉强可以通融吧。后来我又有赠他的诗云:“高吟嵯峨纪剑门,当时倾听几晨昏。”就是指拜读他的入蜀诸诗,中有《剑门》一首他自己很得意,我也很欣赏。
青峰多才多艺,吟诗之外,写得一笔好字,是二王一路。启元白先生和他是同门好友,都是陈援庵(垣)先生的高足弟子,我第一次知道“启功”这个名字,便是由青峰给我看一把扇子,上面有启元白先生写其自作《论书绝句》,中有一首云:“大地平沉万国鱼,昭陵玉匣劫灰余。先茔松柏惧零落,肠断羲之丧乱书。”我至今还记得。青峰写应用文字,笔下很是来得快。后来女师学院师生反对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风潮中,大家推青峰为教授会的秘书,专门同教育部笔战,很是得力,这成了他被教育部解聘的原因,亦即“天荒地老”云云的本事了。
青峰是史学家,我从他得益的主要是史学方面,更确切地说是文史哲相通相关的方面。我不治史学,年轻时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是学过的,对几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者的论著,对他们争论的问题,例如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之类,也曾钻过一阵,我还遵照鲁迅的教方,对野史笔记,特别是南宋、明末、清末的野史笔记,一向留心,也培养出了兴趣。除了这些之外,近代现代史学家,我所知极少。如果说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章嵚、钱穆、孟森、邓之诚、萧一山、陈恭禄他们的著作,我或者读过一两部,至少翻查过,至少在书架上见过的话,不知什么缘故,唯独于陈垣,几乎一无所知。认识青峰之前,我只见过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由于没有需要,从未翻检过,从不知陈氏还有什么著作。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我看过,印象不深,更记不得那是为陈氏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作的序言了。我与青峰的相识,恰好弥补了我这个缺陷。陈垣的几篇著名论文:《元西域人华化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通鉴胡注表微》,现在我记不准这几篇是当时从青峰处借读的,哪几篇是后来才读到的了,但当时都从青峰口中常听到提起。但《明季滇黔佛教考》则是确实当时读过的,陈寅恪所作的小序,也是青峰向我极力推荐的,其中如“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等语,至今尚能背诵。去年黄裳特地著文推荐陈寅恪这篇序,眼光确实不差。
话说回来,青峰给我最大的教益,便是使我略能望见陈垣之学的门墙。我知道,陈门弟子的入门第一步功夫,是从头到尾点读《资治通鉴》,从这一步入手,以后便不至于放言高论,游谈无根。陈氏自己那些论著,都是用了“竭泽而渔”的方法,网罗了最完备的材料,处处凭材料说话。他引用材料,往往动辄便引录全篇文字,起初我很奇怪这种做法;青峰解释道:“摘引容易断章取义。现在全引出来,即使引用者有误会之处,也易于得到纠正。”我非常佩服这种严肃态度。陈氏是治中国宗教史的。但是他那些著名的论文,并不着重宗教的神秘的方面和教理教义的玄虚深奥的方面,而是着重在宗教的政治社会背景和作用,宗派的断续存亡,教徒的生活与矛盾等等现实方面,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宗教史,而不是教义史或宗教哲学史,这是陈氏的创造性的独特贡献,至今似乎还没有第二人。我不治史学,而在这种地方文史哲之会通,受益尤多。陈氏史学,又特重民族思想,《通鉴胡注表微》当然是代表作。我是由青峰的鼓吹才懂得看重清人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他用了桐城义法,一篇一篇地给全祖望改文章,于是我更懂得桐城义法完全是另一路,也更对桐城义法失去了信心。文史不分家,是中国的好传统,陈氏史学是这样,青峰身上也是这样体现出来的。前面说过青峰作得一手很像样的放翁一路的诗,写得一手很像样的二王一路的字,原来这也是很多陈门弟子共同的。我还知道,陈氏史学固然是高度的专门之学,而同时又很讲究博雅,陈氏曾将《四库全书》全部翻检过一遍,这是艺林佳话,我最初亦即闻之于青峰。青峰自己讲授“史学要籍解题”,并曾对《书目答问》做过深入研究,都是博雅的表现。我本来遵照鲁迅的教言,很喜欢拿了《书目答问》来检索或闲看,现在遇到一位专门研究者,加以台静农当时也常说,新文学书也要有一部《书目答问》才好,引得我暗自想过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虽然太无自知,也可见受影响之深了。
除了论学,青峰谈得最多的是沦陷后北平高等教育界的情形,例如高校中有伪校与非伪校之分,后者就是外国教会办的和中国人私立的高校,他们如何在困难条件下抵制“伪化”,坚持民族气节的教师如何集中在这几个非伪校里艰苦撑持,等等。这些都是大后方不大知道的,我有幸听青峰谈说,至今这方面的知识,在抗战期间大后方的人们当中,大概可算是较多一些的。
青峰笃于师生之谊,常向我谈起“陈老夫子”(指陈垣)的立身治学的许多逸事,这里不一一举出。有一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却不是青峰谈的,而是台静农谈的:说是有一次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一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到教师休息室来请胡适为之题签,陈垣当时也在那里,笑道:“这真是请宋江来题《水浒传》了。”
我们当时活得很清寒,然而有朋友之乐,又似乎活得很高兴。然而这局面并不长久,一九四五年日寇一投降,抗战一结束,大局的变动引起了小局的变动,女师学院便因“复员”问题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教育的风潮。
所谓“复员”,当时是指抗战期间原由何处迁入大后方的机关团体学校,抗战胜利后迁回原处。凡列入“复员”计划的,交通工具由政府统一安排;个人回家乡的也称为“复员”,但那个时候个人挤购车船票,难于上青天,所以凡说“复员”还是主要指机关团体学校而言。女师学院是抗战期间新办起来的,它的原址就是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本来没有“复员”问题。但当时全国师院学院,院名之上皆冠以省名或市民,只有两个是秃头不冠地名的,一是“国立师范学院”,通常简称“国师院”或“国师”,初在湖南蓝田,后在湖南南岳,钱锺书小说《围城》即以在蓝田时的该校为背景,另一个就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当时如此命名,似有意要以此二校为全国师范学院的首席次席,将来随着中央政府走,据说教育部某大员对女师学院生做过这类的许诺。抗战胜利之后,女师学院招生,无论外省人本省人,一致切盼教育部兑现这个诺言。外省人切盼早日离开困守八年的四川,本省人大部分也切盼早日走出夔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大家希望新的院址靠近南京,院长谢循初教授是当涂人,所以当时有过一种传说,新院址就在采石矶云云。不料教育部正式决定下来,女师学院迁是迁的,却只是迁到重庆附近的九龙坡,那里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战时校址,现在交通大学“复员”回上海去了,遗下的空房子就让女师学院搬进去。这个决定激怒了女师学院的师生,学生会宣言罢课,教授会跟着宣言罢教,态度都很坚决。教育部当时为什么如此决定,表面理由之下,似乎有一个用意,就是当时全国大学生对国民党政府不满,民主运动方兴未艾,所以有必要尽可能不让高等院校聚在几个大城市里。例如素有“西南民主堡垒”之称的桂林师院,抗战胜利后被强令迁到南宁,桂林当时是广西的省会,南宁不过是一个边陲小城,进步师生都认为是要把他们“装进闷罐”,也曾激起长久的强烈的风潮。女师学院的风潮,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性,也许正因此,在学院内部更便于团结最广大的群众。青峰当时任教授会的秘书,起草各种宣言、启事,与教育部公开笔战,真是所向披靡,驳得对方招架不住。最后,教育部只好下令解散女师学院,撤了院长谢循初的职,另行指派一个以伍叔傥为首的“院务整理委员会”来实行镇压,规定学生赞成迁往九龙坡的向该会去登记,否则该会不承认其学籍;教师则由该会换发新聘书,但是有几个被认为祸首的,不发新聘书,也就是予以解聘,台静农、宛敏灏和青峰都在解聘之列,我算是得到了新聘书,却也不想到九龙坡去了,学院搬走后我便留在白苍山了。
这是一个“食尽鸟投林”“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学院搬走了,青峰全家去重庆另找关系弄车票去了,最后,偌大一个白苍山,只剩下台静农和我母子这两家,还有白苍山隔溪的桂花庄宿舍区只剩宛敏灏一家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夏初的事。青峰既去之后,忽然又有什么事回到白沙空山上来,盘桓数日,他有留别一绝云:“惊心草木无情长,回首弦歌未易哀。流水高山君且住,天荒地老我还来。”这是他的诗里我最喜欢的一首,说到这里才算说清楚我那两句“话到白苍山上事,天荒地老忆青峰”的本事。
起先我欣赏的还偏重在“流水高山君且住”一句。青峰去后又过了若干日子,一个晚上,台静农邀我到图书馆一带去散步,那原是每晚坐满了学生在夜读,门前收拾得很整洁的。不料一二十天无人收拾,树枝便长得伸进了空屋的窗内,满地乱草,抬头不见夜空,只是从树叶缝里闪现出朦胧的月影,我们吃了一惊,默默地赶快走开,颇有点“大观园月夜警幽魂”的意味。台静农后来在一篇文章里描写道:“槐阴蔽道,鼯鼠当阶,昨犹弦歌,今若败刹”,原来那时我因为一直未离开,眼睛习惯于渐变,还不怎么觉察,青峰走开了一段再来看,已经看出草木的无情怒长,有惊心动魄之感。这样,我才特别欣赏“天荒地老我还来”一句,一点也不是夸张,十分恰切地写出了他的深挚珍重的友情。
“天荒地老忆青峰”忆的就是“天荒地老我还来”的青峰。此后,他回到北平,我在徐州教书,一九四七年五月我从徐州来北平小住经旬,我们别后重逢,青峰有《喜方重禹自徐州至》五律四首见赠,首首都极有真情,前引的“剧谈吾可续,豪饮子宜先”一联即在第四首中。一九五三年我由南宁调来北京,直到一九五五年青峰由北京调苏州,那几年中,我们都是解放初斯的那股劲头,各自忙于工作,同在一地而相见不多。“文革”前夕,青峰正在北京,一九六六年大约四月间,我邀青峰到我寓处来,同时邀了周绍良先生,他们同是陈门弟子而不相识,我给他们做了介绍,那是我和青峰最后一见。不久,我进了“牛棚”,听说他被掀回苏州,从此我们断绝了音信。一九七一年秋,周绍良由文化部咸宁干校专程到北京参加陈垣追悼会,回干校后,我问他见到柴青峰没有,周绍良说柴青峰已在“牛棚”中死于急病了。这些经过当中,可以回忆的事也还不少,但总不如从白苍山初见订交到“天荒地老我还来”那一段那么朝夕相见,那么对我有深切的教益。所以我这篇回忆集中地写了那一段,希望多少写出亡友的学行的一些活的风貌,特别希望他的学生们子女们能学到他的无论何时都是“豪谈高唱不知慵”的精神,学到他的“天荒地老我还来”的精神。
(本文写于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二日,摘自《忆天涯》,舒芜/著,方竹/编,北京出版社2020年3月第一版,定价: 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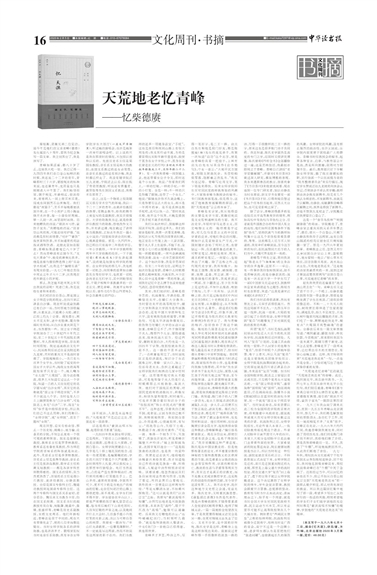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