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三夫,工匠要有跨越千年的眼光
几年前第一次去法隆寺时,辗转火车和公交车,在酷热天气里终于站在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群当中。西院伽蓝乍一看呈水平分布,没有显眼的高度。但是因为看了西冈常一在《法隆寺》一书里还原的建造过程,觉得这碎石地上深褐色的建筑与周围环境极其吻合,让人忘记时光。
法隆寺有2300余件日本国宝,最为震撼的,还是木建本身。建筑学家井上充夫认为,古代日本对于建筑造型的关心主要集中于外部结构,而非内部空间,追求的是实体部分。法隆寺最著名的“柔性结构”,至今仍在被日本乃至全世界的超高层建筑采用,也是隈研吾为东京奥运新场馆采用的核心概念。
位于奈良生驹郡斑鸠町,远离热闹的游人如织的奈良市,法隆寺的标志是一只斑鸠。法隆寺的兴建者圣德太子的家族“上宫王家”以奈良斑鸠宫为中心,法隆寺也叫斑鸠寺,不仅仅是佛教建筑,也是王权象征。在日本,以这只斑鸠为标志的,就是小川三夫。有趣的是解体维修时发现,天花板格子掩盖之下的几百处涂鸦,有不少始建时日本手艺人的自画像,还有动物的蹄印。我心里想的法隆寺建造者的样子,大概就是那样戴着头巾,和唐代人差不多的形象。后来看到多年前药师寺上梁仪式,西冈与小川身穿白色的宫大工传统服装,头戴黑色纱帽,居然和想象颇为吻合。
西冈常一的血缘可以追溯到镰仓时代法隆寺四大工匠之一。梁思成考察唐代木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时,对于它能保留下来有“为后世朝山者所罕至,烟火冷落,寺极贫寒,因而得幸免重建之厄”的论断,佛光寺至今依然寂寥。法隆寺在1300年岁月里,历代始终有名工和名匠环绕,薪火相传,近代也陷入了“废佛毁释”的衰败。
到了20世纪初,西冈家祖孙三代成为法隆寺的“人化”的代表,三代人不仅仅是专属木匠,也作为栋梁,用50年时间,将千年法隆寺解体维修,将古老技艺传播于今世。小川三夫是西冈常一唯一的弟子,在西冈去世后,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宫大工。
“人有跨越千年的眼光,这可以用建筑来证明。”
坚持千年的栋梁
坚持千年的栋梁
“木匠是没有时间概念的。”仿佛爱丽丝掉进了兔子洞,小川给我的第一个口诀是关于时间的。面对上千年的佛塔、上千年的树,他请我忘记知识,“用自己的眼睛,自己来判断”。对法隆寺入门之前,学徒们和我一样,只听过“快点快点”的催促,做事情都是以快和短为目的。在普罗大众的知识体系里,找不到关于时间和法隆寺的论断。
半个世纪以前,西冈常一曾经写信给还未入门的小川,说“尘芥和俗臭”让人们预先被灌输了知识,观看法隆寺的国宝佛像和建筑,个个像评论家一样,却并不能理解圣德太子“以此三宝为报国泰民安”的初衷。
“日本千年文化,都因佛塔和这些粗大的柱子传承至今。艺术是心灵的表现,佛塔、大殿、绘画、佛像都应该是深深铭刻在人们心里的作品。这些,都要看建造它的人,拥有几度深浅的灵魂。”
作为全世界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法隆寺焕发出的统一和稳定,已经成为精神意义的象征。法隆寺放置木材的材料库里,存放着的都是从建造寺院的年代里栽种下的侧柏,存在于同一个时空的材料和建筑,是法隆寺活着的根基。我看到的标着“悬鱼”“破风”“虹梁”字样的图纸,在这里一一对应着古老的实物。
小川一生工作的起点就是法隆寺。“如果一开始从江户时代的建筑入门,可能吸引我的就是华丽。”飞鸟时代匠人们建造的法隆寺,“不是摇摇欲坠地勉强站立,而是和从前一样,凛然耸立”。五重塔是素色的,没有加特别的装饰。以梁、柱、斗拱为特征的木结构,空间布局以“间”为基本单位,几个间并肩排列,立面构成横向的长方形。屋顶成曲面,建筑飞檐的翼角、槅扇等细节都体现了当时中国建筑传入日本的特点。这样的楼阁式塔进入日本后成为佛教建筑的主流。
从一般概念上,日本古建筑观是以无常观作为指导的。伊势神宫每20年就拆除一次重新大修,从公元690年开始,这种“式年迁宫”的规则,贯穿了绝大多数日本建筑本身无法永久保存的观点,在神道建筑中具有统治性。大量古建筑风格华丽,园林庭院优美,富于变换,营造了日本最擅长的空间流动感。而恰恰相反的,法隆寺岿然不动了1300年,成为一本活着的最老的木建教科书。
“上千个斗拱,整齐的柱子,没有一处是完全一样的,都不规则。这是当时的手艺人用魂魄所建。”西冈常一5岁时就被祖父强行带到了法隆寺的工地现场。20世纪初,法隆寺准备举行1300年庆典大祭,祖父西冈常吉已经担任栋梁。西冈一家世代住在法隆寺旁边的西里。西里一带现在很多已经成为普通民宅,这里曾是日本最优秀的工匠群落。和古建有关的手艺人,世代围绕法隆寺居住。
在物质与精神上,法隆寺与人彼此依存。支持了西冈三代的法隆寺住持佐伯定胤,10岁在法隆寺出家,担任法隆寺劝学院讲师后,坚持了恢复、保留宫大工的栋梁之责。正是在他的培养和帮助下,西冈一家三代用超过一百年的时间,完成了最后的使命。在宫大工这个职业已经几乎被废除的艰难时代里,从1934年开始,佐伯主导了法隆寺始建1300年以来,第一次解体大维修。
此前法隆寺一丝一毫都没有被人为动过。西冈家三代栋梁之前,虽然也是世代法隆寺木匠,但没有担当过组织全寺院维修建设的领导人。废佛毁释以后,佛教衰微,“栋梁”一职,多年里一直空悬有名无实。法隆寺依旧屹立,直到等来了“飞鸟再现”。
“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建筑了。你看五重塔的椽头,它们都在朝向天上的同一条直线上,经过了1300 年都没有丝毫的改变。上千年来,法隆寺的木料还活着,当压在塔顶的瓦掀开去掉土,慢慢露出木头,木料还有侧柏的香气。你要让它再活千年,否则对不起这样的树。”西冈这样对徒弟小川说。
西冈常一作为末代栋梁,是法隆寺名气最大的宫大工。解体维修横跨半个世纪,从1934年一直进行到1984年,后期日本经济腾飞,佛教复兴,而西冈有如远古而来的风范出现在报纸、电视里,在当时刮起了“鬼木匠”的风潮。1971年西冈建造药师寺的大殿和西塔的时候,就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手艺好的匠人,大家都抱着一种“这也许是今生唯一的一次机会”的想法来建造殿塔,也希望能够在西冈手下干活。西冈的文章入选了日本中小学教科书。“在他的话里,既没有推测,也没有来自别人的理论和说明。全部都是他亲身的经历。”
这不仅仅是飞鸟时代古建技术的一个现代的重新发掘,也让日本宗教界、手艺界、古建筑界持续讨论了一个世纪。整个法隆寺乃至周边同时代建筑群维修一直进行了50年,是日本现代最重要的大事件之一。
外号“法隆寺的魔鬼”的西冈常一,是在这个“现场”长大的。6岁时就被祖父常吉冠以名义上的“栋梁”。西冈常一对于自己身份的定义是“神佛的护法者”,绝非一般工匠。日本全国上下,以法隆寺“栋梁”为尊。西冈这种扑身奉献的姿态使人产生了“魔鬼”的看法。因为长久的贫困和过于用功,西冈染上了肺结核,他的孩子从未享受过宫大工的荣耀。在最贫困的时候他只能以种地为生,而不盖民房,包括自住的。他阅读法华经,把法隆寺当作圣德太子弘扬佛教治理国家的实证。宫大工世家还有太子讲经会,探讨佛法与建筑的关系的传统。
西冈常吉对孙子实行精英教育,从佛法典籍到农业技术无不精通。20世纪初的日本,孩子们已经开始流行打棒球,常一却被禁止玩耍,一个月只有两天时间可以在场外观看。儿时特别希望逃离法隆寺现场的常一,只要稍微一表达不高兴,母亲就马上要他听祖父的话。其实祖父并没体罚过他,但一家人从不敢回应“是”以外的字。西冈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法隆寺的专职木匠。但法隆寺栋梁,一代木匠里只有一人。
按照祖训,法隆寺木匠可以被派去为天皇修缮京都御所,完工后会得到赏赐一匹马、一斩刀、两百俵米(一俵60公斤)。这是因为宫大工身份尊贵,基本上只能面对自己守护的寺院本身,接受外部邀约非同寻常,西冈祖父的祖父曾经参与修建过大阪城。这些规矩到了20世纪战乱时代依然被西冈家坚守着。
尽管地位崇高,西冈常一却没让儿子们继承手艺。工匠之家的规则不仅超越现实,还要高于血缘。常一就觉得父亲楢光的工具用得不好,哪怕父亲已经担任了法隆寺栋梁,也得到了各种国家荣誉。楢光是入赘女婿,与常一都师从常吉,从伦理上来说是师兄弟。小川说,他们父子的关系一直不好,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在西冈家,师徒关系优先于父子关系。在儿童时常一上农业学校还是工业学校的选择上,祖父坚持必须上农业学校,“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父亲却认为上工业学校学习建筑和绘图,对宫大工的人生更有帮助。这唯一一次意见相左,以祖父胜利告终。
西冈常一进入农业学校不仅学会了农业基础技能,而且上了经济课。第一节课学习“要用最小的劳动获取最大价值”的理论,但校长亲自来向学生解释:“现在西洋经济的理论太多,这是极大的错误。你们是日本人,一个人种出大米要给几个人吃,这才是日本的农业之本。”西冈常一一生对金钱从没有产生过概念,1945年维修法隆寺时,他每天的工资是8.5日元,而一升米的价格是25日元。一家人吃不饱饭,最贫困的岁月不得不卖掉祖产,但他依然记得谨遵祖父的教诲,不盖民宅,埋头务农只求填饱肚子。“宫大工理解的是有巨大年轮的木头,没有时间和精力考虑盖一平方米的房子需要多少钱。”
去大学学习科学,还是向古代、向汗水学习
小川三夫18岁时第一次在修学旅行时来到法隆寺,被千年的建筑感动,一心想成为建造法隆寺佛塔的木匠。经济困难,信息闭塞。高中生小川先询问了老师,就背着行李前往奈良县政府,政府给他指引了“西冈栋梁”的家。小川并不知道应该找哪位西冈,当时常一和楢光都是栋梁,但小川歪打正着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西冈常一正在后院做锅盖。当时法隆寺没有工作,西冈拒绝了小川学习的请求。但他为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孩子写了给“文部省古建保护委员会建造物科”的推荐信,毛笔在白信封上写的落款:大和法隆寺大工 西冈常一。
小川至今仍然记得师傅当年的认真。“我年轻的时候,人类已经到达了可以进入外太空的年代。在科学先导的发达时代里,宇宙飞船和登陆月球,都依靠非常精密的数据和技术完成了。我当时的选择是,去大学学习这些科学,还是向古代、向汗水学习?”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科技崇拜当中,同学们不少在汽车公司工作,企业职员是最主流、最受欢迎的身份。小川三夫的父亲是银行职员,“知道什么工作好,什么工作不好”。
宫大工的工作,在父亲看来,和在顺流而下的河里努力撑着杆子不被河水冲走没什么区别。小川坚持走木匠之路的决心虽大,但文部省对一个不会用任何工具的孩子却无法安排工作,只让他先去学习运用工具。小川先去板材家具制造厂认识粗料,又去偏远地区的佛龛作坊学凿子和刀的用法,在贫苦的小作坊里,一个小伙子不得不一边背着雇主的婴儿一边干活。艰辛而迷茫的岁月里,西冈常一的信是他唯一的精神动力。
西冈坦诚自己的实际情况无法负担小川的学习,“自古名工多赤贫,我已经赤贫得如同名工一样了”,告诉他要热爱自己的工作。西冈当时的考虑一方面是小川年纪大了,学徒最好是自幼开始的;另一方面法隆寺的工作断断续续,无法养活一个人。一直到报纸上刊登西冈即将开始修缮法隆寺的新闻,离小川第一次申请学徒已经过去了3年。“也请贵下作为一个具有文化知识的社会人,用一生的激情,来支持我等这些常年隐身不见天日的宫殿木匠。”西冈的信中写道。21岁的小川终于来到了法隆寺。
没有活干就不能带徒弟。在“教育”里,西冈采取的是“育的现场”。在这漫长的修行里,日本人努力保存的不仅仅是形体本身,还有最重要的样式。法隆寺具有代代相传的样式,有高度秩序感的形体。宫大工通过农业劳动,认识形式与秩序的意义,又把对结构原理的认识发挥到了神殿、宫殿等巨大的建筑上。法隆寺反过来,以具体直接的方式孕育了人们的秩序感。匠人的性格和人品都得不偏不倚。
小川首先发现西冈和父亲说话的方式不一样。父亲见多识广,说话冠冕堂皇却让人无法接话。西冈话很少,但是每句都很深奥,而且自己没有一点欲望。西冈从来不给小川边角废料让他练习,而是只给一片刨花。“毫无个性的怎么用都不坏的东西,培养了人们用什么都无所谓的心情。”这就是西冈对大部分现代物品无动于衷的根源。而读懂这一片刨花所蕴含的知识,需要很长久的时间。
西冈收下小川作为“唯一弟子”,第一天就随手扔了小川夜以继日打磨了三年的凿子。他正式向家人介绍徒弟,说“小川是我的继承人,这是难得的事,从今以后,我的儿子们的地位要排在他后面”。吃饭时小川坐在西冈手边,西冈的长子太郎比小川大一轮,却帮小川烧洗澡水。觉得别扭的小川也要帮太郎烧水,但太郎很紧张,“三夫你别帮我,老爷子看到了我会挨骂的”。
小川被严禁看书看报,连建筑和绘图的书也不能看,集中专心打磨手的技艺。每天两个人走同样的路,无话,西冈骑车,小川步行,他也想买自行车的愿望被师傅骂了回去。有时徒弟走得慢了,师傅到了现场还是无话,但干活的动作能看出生气。只有两个人在一起工作,一天到头依然无话。“手把手地告诉怎么做,掌握技巧倒很快,但是它并没有渗透到身体里。” “那一层膜去掉了,你就会让手和木材真正接触和了解,最后木材通过你的手,伸向你的身体,直到你的大脑。”遇到阻碍是因为修炼的时间还不够。“慢慢煮,慢慢熬,最终会让你的直觉敏锐起来”,西冈从来不说这么做不对。两个人对一根大料加工,一人一半,小川速度又慢又没用过古工具,师傅也不等他,做好了就翻面,小川只好拼命地做。“不要诡辩,不要矫情,只管用身体记住活计。”
“一点不苦,也不悲壮。”小川身上同样有一种超然物外的品性,“无论花多少年,我也要学会那样的技术和智慧。”面对一片刨花和沉默的师傅,他一点不着急,“想要模仿师傅,变成他的手。他说乌鸦是白的就是白的,要让自己尽可能成为师傅意志的一部分。”他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天性,极其专注。“徒弟要时刻觉察师傅对事物的感受和反应,以及思考的问题。每天跟他吃住干活都在一起,师傅摸的东西我也摸摸,保持跟他步调一致。”西冈早年非常严厉,经常在法隆寺现场生气发怒,骂人、踹东西,只要他在,所有人都蹑手蹑脚。但小川从来不多想。“师傅让我打扫工棚,实际上是让我去看屋里的工具,打扫另一间,是让我看图纸。”小川到来时就发现,如果仅仅从做事的角度,西冈其实并不需要徒弟。“法隆寺一有大工程,他手下就会云集全国一流的匠人。”同时西冈也发现,小川是一个连觉都不睡来磨工具的孩子。“我心里觉得他能成才,也觉得没有让儿子们继承我的手艺是对的。”
向树学习是西冈自己的方法。“木头不会撒谎。”就是在法隆寺解体维修的过程中,西冈研究了法隆寺无数木材的刀痕。“飞鸟时代在建筑上居于最高地位,用最简单的方式留存下来独特的建筑美。那些柱子上留下的用枪刨刨过的痕迹,梁上留下的用手斧砍过的痕迹,刻在插木上的凿子的痕迹,这些是获得当时匠人们的信息的唯一途径。”这是他和古人对话的方式。他认为所有的痕迹都是前人有意留下的信息。磨炼对事物的感觉,这就是西冈对小川的要求,不仅是技术合格,还要智慧合格。
“让树木进入手和身体。”听起来好听,但是在现在的社会里,这样的做法会被认为是浪费时间。日本传统节日对于小川后来收的徒弟们来说是个节点,有的人回了家就不愿意再回来了。那种做什么都快,总能得到要领,又喜欢受到表扬的人,反而不太适合做手艺人。“因为不是靠快,而是靠熟练。”
飞鸟再现
“在寺庙行走,当你路过巨大的杉树楠树,心会颤抖一下,还会有小小的恐惧。日本的巨大树木被视为神树。我每天跟它们打交道,对木材很敏感。”木构建筑不是按照尺寸来建造的,而是按照树的癖性。这是法隆寺宫大工的基本口诀。用省事好用的木料,不用有“癖性”的,是机器最喜欢的,因为不用改变刀刃的磨法和角度。慢慢匠人手上功夫就退化了。
“宫大匠一直跟侧柏打交道,这树就跟人一样,每一根都不同。千年的侧柏,成为千年的建筑,这就是法隆寺给我最好的印证。”法隆寺的柱子在基石的部分,都留有一定的“游空”空间。当时没有水泥,每一根木材跟自然石结合立于地下,每一根底部的朝向都不同。与此不同,现代建筑柱子的底部朝向完全一致,也就是地震来了所有的柱子都朝一个方向摆动。而游空使柱子没有被固定死,这样晃动停止后柱子很快就能复位。
日本的建筑不是采取与自然对抗的方式,而是保有与自然融合的谦逊。这也决定了大部分日本建筑走向水平,而非垂直。早在法隆寺开始维修的时候,学者们几乎众口一致地,希望加入钢筋水泥。只有西冈认为,侧柏比钢筋结实。侧柏有品位、香气好,在《日本书纪》里有“建造宫殿要用侧柏”的记载。侧柏癖性很好,新木料容易加工、钉钉子,时间长了,木质会收紧,钉子就拔不出来了。这样的论战在西冈的后半生始终不断,导致他对学界非常抵触。到药师寺还是如此,学者考察的结果,建议西冈在修药师寺的时候加入钢筋。但西冈认为:“飞鸟时期的建筑从没用过钢筋,但它们已经存在了1300年之久。”
长久,是建筑佛寺的关键词。不同于艺术品、工艺品,它既要顶天立地优美的形态,又要能在大自然当中长久地存活。树的性质就很重要,木头的生命和癖性才是自然的戒律。小川说自己的建筑决不能掺假,因为面对的是1300年的法隆寺。“每一层塔的高度都是经过严密计算的,每一层都要按比例缩,当塔建成,最后按上顶部的相轮、顶瓦这些来自外部的重力,这时候,整个塔就会慢慢地往下沉了。如果是用中国台湾侧柏的话,因为它比日本的木材质地硬,所以,要想让它最终缩3寸的话,就得完全凭自己的感觉计算了。”因此他面对每个寺院都好像在战场上。每次完工后徒弟们很高兴,只有他开始担心,300年,一个木构寺庙才算真正变化完成,进入稳定的阶段。所有的变化、树的癖性,要在木匠的预料之中。檐角有些翘起,是为了300年后,檐角下降到正常的程度,此后就保持不变了。他给未来300年留出的变化余地只有3寸。说出这个答案时,他眼神极为坚定。
因为日本境内最古老的长野的侧柏,也只有500年了,西冈到我国台湾地区深山里购买了巨大的千年大树。“那些树木让人想要双手合十。”宫大工不是买树,而是买山。“机器挑选的木材是好用的,人挑选的木材是有个性的。而那些有个性的树生命力才顽强,越是温顺的,生命力也弱。砍树的同时栽下树苗,给两百年以后的人留下材料,这是我祖父的做法。”
西冈从不给任何人期待,也不吹牛说大话。干脆就把按照自己想法做的模型用蓝色塑料布盖起来,不让学者们看到。与此同时,他与小川为东京国立博物馆做了法隆寺五重塔十分之一比例的学术模型,为近铁历史教室做了药师寺的模型,学术模型是从斗拱、柱子到椽子,每一处都要跟实物一样准确无误的复原制作,一个模型就需要两年时间。
“药师寺聚拢能工巧匠的时候,我看到那些真正厉害的老师傅们,第一次接触到千年木材还是受到不小的震撼。大树,给人带来的震撼和它的魄力,无法用语言表达。”小川碰到自己的徒弟们对大树不敢下手的情况,从来不去干涉。“有的人量了一遍又一遍,有的人上来就做。都没关系,当一棵巨大的树木在你面前,你最终都得慢慢适应,用平常心来面对,让它帮助你成长。如果盖普通建筑你一辈子也碰不到这样的树,年轻时为时间和金钱操心,心理会变得越来越弱小。但做宫大工,你没时间弱小。”
如果想要了解“时间”的话,必须要体验“忍耐”,小川三夫手下,出徒的标准时间在十年以上。“十年以后你有了手艺,再去实现理想也不迟,而不是先有理想。”“轻描淡写地给他一根巨大的木材。他已经通过几年的观察,知道了三四百年的木料的价值,也因为用脏手碰挨过拳头。”
当年西冈常一突然让小川担任法轮寺栋梁的时候,他只有31岁。学者们建议西冈采用钢筋水泥修复法隆寺、药师寺的一个重大理由是“不是每个时代的工匠都像西冈这样拥有精湛的手艺”。西冈和小川都认为,只要“不掺假”的寺庙还在,后人一定能从中领悟到前人的智慧,这就是他们从法隆寺身上学到的。“认为以后没有这样的手艺,对后人是很失礼的。是一种侮辱。”
佛寺建造资金量非常大,而且必须一次到位,才能购买昂贵的木材。对于寺院来说,信任一个宫大工就是百分之百的。“你如果有毛病,就不是80分,也不是0分,而是负分,彻头彻尾的失败。”在法轮寺大修的几年里,外面一直掩盖着脚手架和篷布,直到全部落成。“那天拆的时候正好是傍晚。我专门跑到一个有些距离的地方去看,结果看到塔檐翘得特别厉害,简直成了飞檐,心说‘坏了’,当时就吓得不行了。”小川用了“切腹自杀”这个最严重的词,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一晚上他没能睡着,辗转反侧直到清晨又去看塔,这次法轮寺却呈现出特别漂亮的线条,美! 这个工程成为小川三夫的立身之本。
“我们干的事,活着的时候听不到什么夸奖。300年后,我建的药师寺西塔,和原本树立千年的东塔一样高了,那时候我才能对自己说‘干得好’,那颗悬着的心才能真正放下吧。”只要那里还有塔,就一定会有了解它的人,怀着“从前的人是怎么造的”的心去研究它。西岗对小川的嘱咐是:“我们要把这个时代最好的东西留给后人,随随便便建造的东西传达不了真正的文化,甚至会把我们已经传承下来的东西也毁掉。”“想要留住真正的文化,就要做真正的好东西。”
(本文作者葛维樱,摘自《守破离:一流日本匠人精神的修炼》,葛维樱、王丹阳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1月第一版,定价:69.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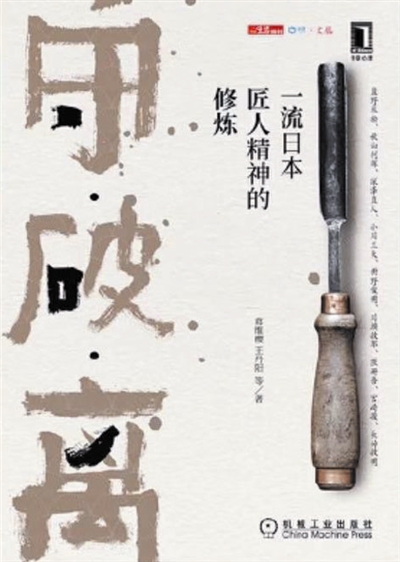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