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钧
我1954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到哲学系,学的专业是逻辑,系里让我去找逻辑教研室主任王宪钧,听他的安排。
王先生住燕南园62号。它东面是中文系林熹先生的61号,和62号乃同一座平房的两分。南边是燕南园的南墙,南墙外就是学生区。西面63号是校长马寅初的住宅,正在修缮。王先生的住房约有120平米。一个卧室和一间作接待客人用的客厅,另有一个大约40多平米的房间,被中间隔开,一东一西。西边一间是逻辑教研室开会的地方。
我是第一次到王先生家。他在客厅里见我。他先问了我的家乡和家庭情况。王先生是山东福山县人,我是山东牟平人,我们是邻县老乡。他问我大学一、二年级都学过什么课,学过高等数学没有。我说我没选过这课。他又问我外语情况,我说我的外语不好。初中学的的日语、每周只有一堂英语。念高中时英文跟不上班,补习了三年也没赶上别人。大学一二年级学的是俄语,也没学好。王先生说,当大学教师,外语非常重要,是作学问的重要工具,尤其我们搞逻辑,得借助外国书籍刊物,他希望我把两门外语英语俄语都捡起来,能够看懂外文的逻辑著作,掌握国外的研究动态。他还向我介绍了教研室情况,说以后有事情就找晏成书先生,她是教研室的秘书。
王先生家世显赫,祖父王懿荣出身官宦世家,中进士,任过翰林院祭酒,学识人品服众。他还是甲骨文发现者和研究者。任京师团练大臣,是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的城防司令,城破自杀殉国。这一切等等,我都一点不知。所以第一次和王先生见面,我除回答王先生的提问外,聊不上一点旁事。
新学期开始,我第一次参加逻辑教研室的会议。我一进屋,里面已坐满了人,围成一个圈子。我后来发现,教研室老师在这里都据有各人习惯的坐位,绝不更改。这间房东边是木制的隔墙,靠墙中间部位放一张小茶几。两边各有一个厚的高蒲团。王先生坐在北面的蒲团上,吴允曾先生坐在南边的蒲团上。吴先生南面靠近这屋的拐角,放一把椅子,那是周礼全先生的坐位。然后是南墙,放一把长沙发,江天骥先生坐东面,李世繁先生坐西面。这屋的西南拐角放着一把大摇椅,那是金岳霖先生的座位。金先生北面有两个单人沙发,沈有鼎先生和何兆清先生一南一北。再往北,放一把藤椅,汪奠基先生坐在那里。在他旁边是一把椅子,那是我坐的。晏成书先生则坐我东面那把椅子上。她靠着王宪钧先生。这样实际上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座位圈。
王、吴两先生是抽烟的。每次开会,小桌上必放上两盒10支盒的哈德门烟。周先生有时也取一支来抽。
第一次进会场我相当紧张,很拘谨地和这些先生坐在一起,也不敢端详这些老师。倒是周先生和我较熟,曾教过我们两门课,他一一给我介绍我不认识的江天骥、李世繁、沈有鼎、吴允曾诸先生。
第一次会记得是安排教学,这些是早就定下来的。王先生在会上说说也是让教研室的人都了解一下。那时逻辑室担负着逻辑专门化的课。有三个年级。给这些学生开的课有普通逻辑、数理逻辑,西方逻辑史、逻辑的理论问题,逻辑教学实习,开课者有王宪钧、汪奠基、何兆清、周礼全诸先生。此外,还有江先生给哲学系开普通逻辑,李先生和吴先生给法律和经济系开普通逻辑。
会议的最后是安排我的工作。王先生说,教研室的老师们都没有会俄语的,我们需要一个人懂俄语,翻译些资料,了解些苏联逻辑的动态。他说他已取得俄语系的同意,让宋文坚正式选俄语系的课,视他原有程度选两门,希望能在一年后达到流利看俄文杂志和书籍的水平。安排我的第二项工作是给江先生的逻辑课做辅导,答疑和改习题作业。这得听江先生的课,说可以从江先生那学到不少东西。第三项任务是参加讨论老师们讲课的讲稿。那时讲普通逻辑课的老师都自己编写讲稿,但要由这些老师集体讨论一下。参与讨论的有江天骥、李世繁、吴允曾和晏成书诸先生。我则还负责讲稿的传递。最后一项是作毕业论文。王先生说,清华的毕业生都作毕业论文,有导师带领,可以从导师那学到一些更深入的知识和作学问的方法。说宋文坚的毕业论文是补作,是一项要求。时间可以延长点,一年半、两年都可以。我记得汪奠基先生、何兆清先生都很赞成,并说愿意带我作毕业论文。王先生说,二位先生已有课程,金先生没有教学任务,是否可请金先生指导这毕业论文。这可能已经和金先生说好。金先生当即同意了,说可以到他燕东园的家里多讨论讨论。
这以后,在王先生家开的教研室会议挺多,一个月得有两三次。那时在学术界已展开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学校和系里都时有报告。听了都安排讨论。其次,院系调整一个目的是对旧的资产阶级哲学系的改造。在逻辑教研室就是开展对逻辑的讨论,以苏联的逻辑教材曹葆华等译的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为范本来改造逻辑课程。这个改造过程在我进教研室之前就开始了。此时,苏联的辩证逻辑文章也通过《学习》杂志不断引进我国。教研室的一些先生如江天骥、李世繁对辩证逻辑甚有好感,他们在教研室会上也时常抛出这方面的话题。此外,王先生已开了数理逻辑课,金、沈、周、晏诸先生都是推崇数理逻辑的。这个科目有甚么作用,有没有问题,也不时地在逻辑室引起争论。
经过多次教研室会,我渐渐看到教研室会议一些有兴味的动态画面。下面偏重讲讲这些。
沈有鼎
遇有什么讨论,沈先生是最爱发言的一个。我印象里,不论什么问题,他都可参与发言。我还有印象,他的发言甚少顾忌,有自己独立见解。辟如那时批判胡适,系里开过几次会,金岳霖、任继愈、石峻、冯友兰诸先生都作报告。沈先生在讨论时常常对这些报告作点评。他对金先生的报告也能当面表述一些自己的见解。我觉得沈先生是一个很能自主思考且愿讲自己见解的人。不过沈先生讲话声音不大,也从不看人,像是自言自语。我一般是听不懂他的发言,能准确听清楚沈先生意思的是吴先生。其他诸位也可能听懂,但他们一般都不太理会。只有当别人误解沈先生的意思时,常常是吴先生出来说话,说沈先生的意思是什么、什么,一,二,三。
沈先生爱发言,金先生的回忆录也有记载。据社科院哲学所刘培育先生整理的《金岳霖回忆录》,金先生说,“《哲学评论》是在北京出版的,在北洋军阀时代没有出什么问题,可是后来问题发生了。南京要我们去开会,瞿、林都没有去。那时候贺麟和沈有鼎先生都回国了,都预备去开会。我们的安排是冯友兰为理事,贺自昭为秘书,同南京的人打交道。我的任务是坐在沈有鼎先生的旁边,阻止他发言。南京的人出来讲话的是陈大齐先生。”……“沈先生果然有两三次要发言,都是我把他的衣服抓住,阻止了他发言。”
有一次,哲学系的教师分两个大组学习讨论,逻辑教研室编在郑昕先生领导的组里。沈先生虽然天天到会,但他似乎不太明白运动是怎么回事。一天,会场上冷场了许久,没人发言。这时忽然鼾声大作,大家都愣住了,一看,沈先生歪在椅子上睡着了。大家一阵哈哈大笑。当然,沈先生挨了郑先生一顿批。不过他似乎并没在意,好像在批别人似的。
沈先生有点怪。不修边幅。他一年四季都披着一件黑色旧呢大衣,呢毛磨损,有的地方油光发亮。他一年都不戴帽子,头半秃,有几缕长发撩过头顶。还有是,他一年四季都拿一把破芭蕉扇。从后面看他走路,有点跛脚,左肩低,右肩高,走得慢,似乎一拐一拐。他这副装扮在北大可属第一份,像是在世济公。
周先生曾给我们讲过一些沈先生的趣事。有些不好提笔,怕损了这位逻辑才子和大师。但这些和沈先生能做好学问都无关。他写出中国第一部系统深入的墨经逻辑学,在数理逻辑方面也做出如初基演算、所有有根的类的类的悖论、他的两个语义悖论等称世的创作和贡献。沈先生的这些趣事和他的学问相比,只能衬托而不会损及沈先生的大师风范。
据说,金先生最为欣赏他这位高足。听金先生的课,金先生的评语是,沈有鼎不用考试也得给100分。金先生对沈先生生活也多有关照。据说,日本侵华,清华教师南下避难。沈先生和金先生同行,金先生照顾了他一路,包括他的行李。
沈先生那个不修边幅的样子以及他光棍的身份,让人感觉他是不近女色的柳下惠。其实不是。据说,沈先生在德国弗莱堡大学深造,喜欢上一个在德国的英国女子,那女人告诉沈她有了男朋友。沈先生死缠不休。有次女方开门,竟发现沈先生在她床上呼呼大睡。该女招呼来她的男友把沈先生抬到了街上。
沈先生会唱昆曲,对这门高雅艺术据说有一定造诣。那时也有年节喜庆聚会,每此场合,老先生们必邀沈先生演唱一段,沈先生也每邀不拒。我第一次听他唱是在才斋和德斋之间的一座横向楼的楼上。可能是1954年的年末,好像并没有既定的表演日程,是临时谁把沈先生哄起来的。沈先生仍然是那套呢大衣芭蕉扇的济公装束,站在广众间,咿咿呀呀地唱了几曲,大家鼓掌。沈先生不仅会唱昆曲,还会作曲。据冯友兰先生《三松堂自序》,沈先生还为冯友兰作词的西南联大校歌作过曲,被西南联大校常委会采用并公布,是后来又改用了张清常的曲谱,这就是后来沿用的西南联大校歌。
1956年沈先生调到中国科学院,后来又结了婚。结婚后沈先生外貌完全变了样,沈师母把沈先生调理得又年青又率脱。
吴允曾
教研室另一个单身吴允曾先生也像沈先生一样有才华。但吴先生不像沈先生在北大时那样不讲究穿戴,而是天天都穿戴干净整齐,衣裤笔挺。这些整齐衣服都不是吴先生自己洗烫的。那时未名湖北面几幢单身教师宿舍,每天都有学校职工的家属来收要洗的衣服。洗净熨好再送回来,收点费。吴先生的衣服都是这样洗出来的。
吴先生生活上不太自理,做学问却很棒,这是哲学系和计算机系公认的。他也是北大极少数从讲师直升教授者之一。
在教研室开会时,吴先生也是说话较多的一位。吴先生说话沉稳,吐字清晰,注意用词的准确恰切。最厉害的是,吴先生记忆力超常惊人。在学校听完报告来教研室讨论时,大家常常是请吴先生再复述一下报告。不论当日或时隔多日,吴先生都能准确地把报告从头至尾一、二、三、四地捋一遍。他的复述简直就是报告的一个详细提纲。在讨论什么的时候,吴先生虽是发言积极,但他每言都不多说,慢吞吞,句句都能切中要的。另一个是他在别人讲话时除常插话外,常常都是安稳静听,但只要他一讲话,就满脸堆笑。吴先生是独身,据说他在燕大时曾追过当时的校花邬某,后来邬某嫁给了沈乃璋。吴先生再也没有找其他女友。
吴先生是燕京大学毕业的。由于他的记忆力好,他的英文也相当好。他没出国留学,英语口译却很棒。抗战胜利,他曾在当时的美国军调处当翻译,军调处是抗战胜利后为调解国共两党军事冲突而设立的。
由于英语好,吴先生在文革后掌握了我国引进的最先进的美国计算机方面的资料、讯息。他被抽调到学校开发研制我校第一台计算机的研究团队,在那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后他也调到计算机系工作。在数理逻辑与计算机科学的关系、计算机理论基础、计算机软件设计和可靠性研究等方面他都有成果。吴先生对我校和国际计算机学界的国际交流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先生对我这个后辈也有许多入微的关照和帮助。我入教研室不久,吴先生就对我讲,你可以把俄文学好,但得想办法把英语捡起来。他说,苏联高层次的逻辑学家不多,只有个诺维科夫还算点儿。他们的书籍也不先进。引进英文方面的书籍和资料也不多,如果你想搞逻辑,跟着苏联走是没有出路的。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文革后我开始翻译美国苏佩斯的《逻辑导论》和美国科庇的《符号逻辑》,遇到不甚有把握的地方都去向吴先生求教,他不厌其烦地给我校正了许多不妥的译笔。
吴先生也受到邻里老师的尊敬和照料,他住蔚秀园22楼二楼一套二间房,我系陈葆华老师住他楼上,他楼下是另一外系老师,很遗憾我忘记他名字了。这两家都在自己家装了电铃,线头安在吴先生房间里。以便吴先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呼叫他们。
我任教研室主任后,我们教研室的博士生导师王宪钧先生已离休,晏成书先生是有能力胜任博导的,可是她也退休了。我是资格不够的。为此,我找到系主任黄楠森,提出让吴先生参评我们教研室的博士生导师,黄先生同意了。我就找到吴先生向他说明。他很高兴。不想就在这不久,吴先生突患心脏病辞世。
吴先生为人谦逊,平和。他的学问功力是全校闻名的。北大当时的校长丁石孙对吴先生有极高评价。可参见《吴允曾选集》丁石孙的代序《忆允曾》。吴先生孤身一人,寂寥终生。听说,沈乃璋先生去世后,他的夫人邬某,吴先生早年追逐的情人,曾托人代言,想和吴先生重修旧好。可吴先生说,“算了吧,我一人已习惯了。”这是一个太不幸的选择,如果两人事成,吴先生可能不会在70岁就那么早离世了。
《吴允曾选集》是吴先生去世后由他的学生和他的挚友们合力搜集编成的,内容主要是吴先生在数理逻辑和计算机以及二者关系等方面的一些文章、报告、讲话,有许多吴先生的创见。这是吴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份重要宝贵遗产。
周礼全
在教研室中,我最为熟悉的是周礼全先生。他还带我们做教学实习,共同讨论较多。虽然他在1956年就和金、汪、沈三位先生调到中科院哲学所,但由于哲学所逻辑室和北大逻辑室有较密切的关系,其后我和他仍多有接触和受他指教。所以我一直就觉得周先生是我很亲近的师长。
周先生是清华来的。清华有四位在逻辑室,而且三位都是教授级和知名人物,所以,我体察,别人会有存在一个“清华帮”之感,而且在逻辑教研室,“清华帮”无疑起着引领作用。教研室内在一些相关的议事上,往往都是由这些人来定音的。而这“音”一般都是由周先生发出的。不是周先生提议别人复议,就是别人提议周先生复议而确定下来的。
在讨论学校的各种报告的会上,周先生也是发言较多的一位。我印象中那时发言者一般都能畅所欲言。听说,周先生在西南联大时不是进步学生。我是崇信共产党的,思想相当进步。因而在开会时,在讨论什么政治报告时,我印象里周先生的发言会时常走调。有时候金先生也常出来纠正几句。顺便说说,金先生每次开会必到,他坐在那把大摇椅上。有时也晃悠摇几下,一般他不怎么发言,也不评价什么。但当听有可笑之处时,也会情不自禁地呵呵大笑。遇有激烈争论不可开交的场合,他还会探出身子审听。但即便这时他也是只听听而不参与争执。王宪钧先生说,周礼全是金先生的学生。因为有此层关系,加之金先生解放后非常进步靠拢党,所以他对周先生还能出于爱护而纠正他一些不当言论。
周先生性格好张罗,他最爱张罗的一件事就是教研室集体到北京的名餐馆会餐。王府井的翠花楼,西单的同和居,颐和园的听鹂馆,还有东来顺、全聚德,我们都吃过。都是周先生(有时也有吴先生)张罗联系的。那时,教师发表文章出书有稿费,教研室留十分之一。别的教研室用这笔钱来置备教研室的家具沙发等。逻辑教研室在王先生家开会,省了这笔钱。有钱常用来吃。吃吃馆子也是教研室和谐感情的一种手段。记得我第一次吃是在翠花楼,那是我有生第一次来这样的场面。大圆桌,菜肴丰盛。还有我第一次吃的烤鸭。我记得周先生还教我怎样卷烤鸭饼。
周先生离开北大后,我也常和他见面。还到他家给他过80大寿。调到哲学所以后,周先生在做学问方面似乎更加努力了。他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的模态逻辑及其发展史的著作;他开创了自然语言逻辑这一逻辑新领域的研究;他担任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多年,对中国逻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先生几个儿子在美国。后来他也去了美国定居,曾回国几次,恋旧,常和旧日学生包括我聚聚,感到很畅心。他的夫人张瑞芝去世后,周先生更郁闷了。一个人住到养老院里。我们都劝他回来,有房子,有退休金,又有诸多同事,好友,学生,绝不会像在美国那么寂寞孤零。
后来听说周先生去世了,我心情很惨然,久久难平。
周礼全先生有自己的学术观点,也为此爱发言和争论。他在教研室会议争论的对象主要是李世繁先生和江天骥先生。其他诸位,除吴先生和沈先生外,多是不怎么参与的。李先生爱发言,有言可发。江天骥先生也爱讲话,更是有东西可讲。教研室会议上的大戏常常在他们几位中间展开。
江天骥
江天骥先生最先开展了辩证逻辑的研究。他在《新建设》1955年第六期上发表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此前他也在教研室会上多次提出他文中关于辩证逻辑的见解,他认为辩证逻辑是理性思维的逻辑,是关于理性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逻辑。而形式逻辑则是经验思维的逻辑。他的文章一发表,在逻辑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在教研室也一样。
王宪钧先生是反对有所谓辩证逻辑的,认为它不是逻辑,而是哲学。但他不怎么讲他的理由。周先生在离开北大之前,和江先生有多次关于这问题的交锋。他认为,只有黑格尔的大逻辑和小逻辑讲的才是辩证逻辑。他后来专门写了一篇长文《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李先生不同意江先生的是,他认为辩证逻辑也是一般思维的逻辑,但有它特有的思维形式和规律。如辩证判断形式,辨证推理形式等等。这争论一直持续到1956年江先生调到武大,周先生调到哲学所。
关于苏联逻辑的争论是因为系里组织逻辑老师到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尼基金的逻辑课引发的。除王、汪、何、金几位老先生不去,别的老师都去了多次。他们都觉得这个专家不怎么样。尤其周先生,他在教研室会上举了不少尼基金讲得不对的例子。李、江则认为,尼基金不讲数理逻辑,只讲传统逻辑,且也讲的不怎么样,不说明苏联逻辑不怎么样。他们还认为,在大学文科开逻辑课就得讲传统逻辑,因而也得向苏联的逻辑学习。这样就把后三个问题搅在一起争论开了。
江天骥先生当时不过40岁,他1942年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1945年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研究生院,1947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到武汉大学,被聘为副教授。1952年由武汉大学来北大哲学系。那时他住在健斋三楼,一人一个大屋子。他的屋子也十分讲究,敞亮、干净、整齐,躺椅和沙发齐备,几个大书架子全是外文的精装大厚本书。江先生本人也注意仪表。他非常注重穿戴,西装精美可体,革履光亮,金丝眼镜。可说他是学校最有翩翩风度的学者之一。不过江先生头发白得早,长有一半银发。江先生走路也很潇洒帅气。腰板挺得很直。他爱在未名湖边散步,思考问题。
江先生爱讲话,爱发表意见。江先生有理论气息,讲话有据,讲究论证。糟的是他一口广东话,唧唧唧,不好懂。因为我要给他上辅导课,我每课必得听。我听得很艰难。由于我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能比学生多听懂许多,学生可就不知如何了。
江先生没有数理逻辑的背景。他和李先生一样都主张按苏联的教科书来改造我们的逻辑课。他欣赏苏联新兴的辩证逻辑,不断从理论上加以琢磨。
江先生在学术理论问题争论上虽寸步不让,却常常是面带着笑容。在争不倒对方时,也不过摇摇头罢休。再重新思考。因而江先生是很能钻研问题,他在理论上有一套。在形式逻辑的理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以及在对辩证逻辑的确认方面他都有一套。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是教研室中很多产的一位。在我国解放后几次逻辑问题大讨论中,他是其中一个学派的领军人物。
江先生1956年调回武大。他负责筹建了武大西方哲学研究所,担任所长。但他仍还关心逻辑问题,出版了一本归纳逻辑的专著,还主编了国内第一本西方逻辑史。晚年,江先生关于辩证逻辑的观点有所改变。他认为,没有严格的句法和形式语义学,就无所谓逻辑。他把形式逻辑定义为以语法和形式语义学为基础的关于命题和推理的理论。这和王宪钧先生的见解有许多相合了。他还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正在于缺乏分析哲学所具有的那种精致性。这一见解对于中国逻辑史学者也有启迪。
江先生2006年10月去世,享年91岁。是中国逻辑学者中年寿最长者之一。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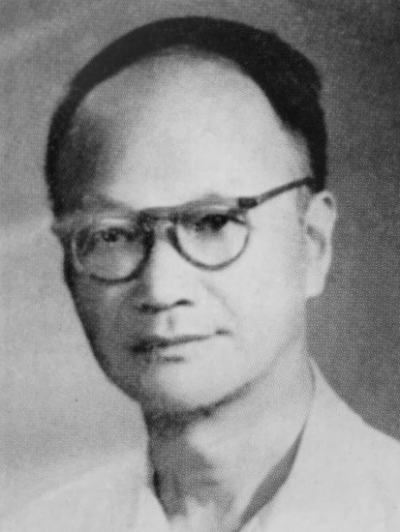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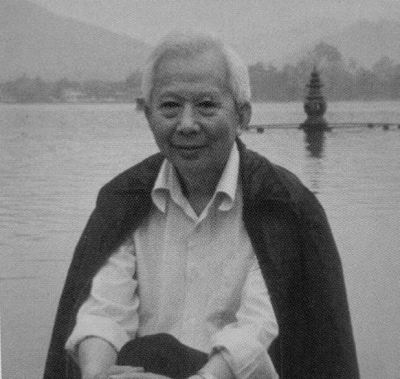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