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南唐)李煜《乌夜啼》
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类,“词”被英美译家注意到的时间要比“诗”晚得多,译介的数量、流播程度和影响层面至今也难以与诗歌比肩。但在被选译的宋代词家及他们的作品当中,李煜这一阕《乌夜啼》可算得颇为突出。
文学翻译,本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经过译者对原文的阅读解码,把握住原作的形式和内容,用目的语进行再编码、再建构,进而重新呈现,没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做不到,没有深厚的创作能力也做不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尤其难,因为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并非现代口语,懂汉语并不等于能解读古诗词。其次,古典诗词往往借由大量传统意象来表达,这些意象的内涵与外延都比字面要丰富、复杂得多,即便能读懂,诗歌译文又必然被字数所限,不可能扩展太多。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之大,东西双方的文化隔膜之深,又为翻译加上了种种宏观因素的制约,真可谓山一重水一重,障碍数不胜数。
所以每每在一大堆英译中国古典诗词里抬起头来,忍不住感慨在没有资料库,没有网络,甚至连字典都难得的时代,若不是真心热爱,谁愿意主动选择一项如此艰难的工作?!那些值得敬佩的译家队伍中,有一位女性,名叫克拉拉·甘淋(Clara M.Candlin),是较早关注宋词,并有相当数量的译介作品传世的美国译家。
克拉拉出生于1883年,当时她的父亲,乔治·甘淋(GeorgeThomasCandlin)神父已在燕京大学教授神学。老甘淋神父热爱文学,他189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一书,以《以利亚特》比《三国演义》,以《天路历程》比《西游记》,以《一千零一夜》比《聊斋志异》,是早期中国小说英文译介的重要文本。他在书里说:
“这些(中国)人被赋予了充满丰富想象的神秘创造力。这种创造力照亮了天才作家们并促使他们热爱它的荣光……这种创造力从红尘里举起了他们——就像举起了我们一样——去承继时间的恩赐,并从粗俗、丑陋的现实当中构建出一个理想世界,一个广阔的,形态高贵的美丽世界。”
老甘淋神父对中国文学的推重,深深感染了克拉拉。她在浩瀚的中国古典诗词海洋中选择了宋词,而非追随英美诗坛十九世纪末以来偏重“正统中国经典”的倾向去译介《诗经》或唐诗,因为她精通音乐,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歌词作家。1933年,她的《先驱之风:宋词及其他歌词选译》(TheHeraldWind:TranslationsofSungDynas⁃tyPoems,Lyricsand Songs)出版,由胡适先生作序,译介包括李煜、欧阳修、李清照、辛弃疾在内的宋代词人26家和数首民歌,其中就有这一曲《乌夜啼》:
TheEmperor'sLamentI/帝王的哀歌·其一
Fadedarethewoodlandflowersofspring,/林中的春花已凋残,
Alltoosoon,toosoon./都太匆匆。
Chillyrainunbiddencomesatdawn,/黎明时分突如其来的寒雨,
Lateatnightthewind./深夜里的风。
Gutteringcandles:/烛光摇曳:Friendlyrevelries:/友好的欢宴:
Whenwilldayslikethesereturnagain?/这样的日子几时再有?
Lifeiseverfraughtwithwoe:/人生满是悲苦:Riversevereastwardflow./江河长向东流。
克拉拉用散体意译,习惯于给原作另加一个诗题。李煜入宋之后,所有作品都可以归为“帝王的哀歌”,单为这一阕词作标题似乎太宽泛。可是,如果将译诗置于当时西方民众对中国文学普遍的陌生感当中,克拉拉这样做就有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有利于读者更准确地了解原作的情感。此书中的“帝王的哀歌”其二,是《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的译文,也足以说明克拉拉的译介,建立在对李煜的生平,以及原作的创作背景有相当程度了解的基础之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学艺术界,轰轰烈烈的“新诗运动”将近尾声。汲取东方诗学营养,建构美国新文学所带来的诗歌新范式趋于稳定。克拉拉译本很显然受到这种新范式的影响。她不再满足于再现诗词中的典型意象去渲染异域的,东方的情调,而将原文作为一个蓝本,用浅白的语言、自由的格式来渲染她自己的,唯美的艺术理想。
细究李煜原作,“胭脂泪、留人醉”一句,惋惜凄风冷雨摧残落红满地,景语情语相生相扣。所谓“胭脂泪”,或许是残花令伤逝的人泪泣如血,又或许是雨打花落,满地如泪湿胭脂。“留人醉”,可以是见落红而心醉,也可以因伤春而酒醉,问题是究竟是一人独醉还是几人同醉?也有的版本在此处作“相留醉”,更费人思量:到底是花留人,人留花,还是人与花各自留?——中国古典诗词是如此言不尽意,克拉拉领会不到那么多,只能凭借一个“醉”字望文生义,改成对“欢宴”的追忆,还要加上倘恍迷离的摇曳“烛光”。实际上切断了与上阕的情景关联,使得后续的“几时重”一问失去了原有的力度。
足见克拉拉如诸多作家背景的译者一样,并不苛求与原文的精准对应。从严格的“翻译”角度来讲,她的译笔不算出色,因此不为文坛或汉学界所重。但她的译文语言简洁跳跃,借由原作的脉络得到了新颖的文本布局,作为英文歌词,不落俗套又自成一统,为英美音乐界注入了一股迥异于西方传统审美意趣的“汉风”。这一阕《乌夜啼》以及她翻译的很多首李煜或其他词家如辛弃疾、秦观等人的作品,都曾先后被谱成声乐曲,传唱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社会持续动荡,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深刻影响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心理、生活和精神状态。对近代工业文明弊病的忧虑,对西方优越感的质疑,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立足本土,借鉴东方的大变革、大重构。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汉学研究重新出发,并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各领域、各阶层对中华文明的兴趣和认知水平都比过去大为拓展,中国古典诗词译介顺势进入第二次高潮期,译者阵容迅速扩展。1965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比较文学教授赛利·柏芝(CyrilBirch)编选的《中国文学选集·上卷》(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Volume I: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出版,“宋代卷”译介韦庄、李煜、苏轼、李清照等十四位词家的作品三十余首,其中李煜词十一首,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柏芝本人和英国著名东方学家、翻译家亚瑟·韦利(ArthurWalley)各译出一首,包括这一阕《乌夜啼》在内的其余九首出自另外一位译家,萨姆·布罗克(Sam Houston Brock)之手。
布罗克不是汉学家,也不是作家,他是一位口腔科医生。他曾经接受过日本语言文学的正规教育,一度旅居日本研习东方绘画艺术。此后开始学习汉语,进而系统学习中国古典诗词。早期的西方译家们把所有押韵的中国文字都归在英文“poetry”的概念之下,从诗、词、曲、赋到对联、民谣、《三字经》,统统都被用来作为例证,说明中国“诗歌”的特点。到这个时候,经院派汉学家们已经明白,汉语的“词”和“诗”是不同的文体,不能一概以“诗歌”笼统对待。所以柏芝选本中所有宋词都保留原词牌为标题,布罗克也遵循了这个体例:
Tune:"NightCrowCalling"/调寄:乌夜啼
The floweredwoods are droppedtheirspringtimerosefestoon,/开花的树凋落了春天的粉彩,
Sosoon,sosoon./太匆匆,太匆匆。
Butnight-blowingwindsandthecolddawnrainwereboundtobe./但夜风和清晨寒雨注定要来。
Yourtear-stainedrougewillkeepme,/你泪湿的胭脂留住我,
Drinkingherebesideyou./痛饮在你身边。
Then—whoknowswhenagain?/可——谁知下回是几时?
Ourlivesaresadlikeriversturningalwaystowardthesea./我们生命的悲哀如江河长流入海。
和克拉拉相比,布罗克的散体直译至少从形式上更接近原作。他将“林花”译成“开花的树”,虽是简单的字面对应转换,也呈现出一派视野开阔的,花谢花飞的残春哀景。“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一句,“无奈”的主词本是作者或林花,布罗克替换成了冷雨寒风,再加上“boundtobe(必然/肯定)”来限定这个新的主词。虽然改换了原文,读来却不难从中体味到作者的情绪凄苦,是整首词中译得最出彩的一句。然而当他将“胭脂泪”坐实为美人的泪湿胭脂,李煜的词境中便多出了一个女性角色,场景随之从户外转入室内。如此归结到最后的长恨入海,也就从国破家亡之痛,变成了男女欢情难永之叹。
汉语的句法没有词尾变化,尤其是在诗词当中,名词出现时不见得能看出单数复数,动词也没有时态,还要时常隐去主语,有时甚至连动词、介词也都省略。于是为了切合英文的句法,译家们就必须“补出”缺失的部分。“补出”多少,如何“补出”,完全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主观理解。
“胭脂泪,留人醉”,原文没有主语,在结构上又转入了下半阕,自学成才的诗人克拉拉理解不了,干脆整句掐掉,用自己的想象添枝加叶,补出一场无中生有的“欢宴”;布罗克则根据“胭脂”字面的,女性化的指向,补出一位与李煜对饮的美人,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关联了上下文,是符合文意逻辑的。在这个问题上,后来更专业的经院派译家也未能比布罗克更进一步,比如加拿大汉学家白润德(DanielBryant)。
白润德出生在美国,因为反感越战离开,到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就读,成为叶嘉莹先生的弟子。从1977年起,白润德执教于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大学,他生平的研究兴趣并不限于中国古典文学,却也是较早系统译介并研究宋词的英美汉学家。1982年,他的《南唐词人:冯延巳和李煜》(Lyric Poets of the Southern T'Ang:FengYenssu,903-960andLiYü,937-978)一书出版,集中性地译介冯延巳和李煜的重要作品,注释详尽。而早在这本译著出版之前,他的宋词译介已享誉学术界。
1975年,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罗郁正、柳无忌联手合编《葵晔集:历代诗词曲》(Sun flower Splendor: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中、英文版同时问世。此书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英文版荟集英美汉学界大批宿将新秀,译出中国历代共145位诗人近七百余篇诗、词、曲作品。书中“宋代卷”收入李煜词十二首,这一阕《乌夜啼》和《一斛珠·晚妆初过》《清平乐·别来春半》《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等十首脍炙人口的李煜名篇为白润德所译。
Tune:"CrowsCryingatNight"(Wuyehti)/调寄:乌夜啼
Thespringscarletoftheforestblossomsfadesandfalls./林中花春天的绯红谢了,落了。
Toosoon,toosoon:/太匆匆,太匆匆。
Thereisnoescapefromthecoldrainofmorning,thewindatdusk./无法逃脱朝来寒雨、暮色里的风。
Thetearsonyourrougedcheeks./泪水在你胭脂的脸颊。
Keepusdrinkingtogether,/留住我们对饮,
Forwhenshallwemeetagain?—/为我们几时能再见?
Thustheeternalsorrowsofhumanlife,likegreatrivers,/这样深长的生命忧伤,如大河,
Flowingevereast./一直流向东去。
罗、柳两位教授合编《葵晔集》的目的,在于给当时高校里刚兴起的英译中国古典文学课程提供教材,所以在意译的词牌名之外,统一加注了汉语拼音,便于学生查考。作为经院派译介李煜的代表,白润德译本除了“太匆匆”一句而外,总体上句式规范而遣词拘谨。单看“乌夜啼”这个词牌,布罗克译成“NightCrowCalling”,对应的意思是“夜乌啼”,英文简洁生动;白润德译为“CrowsCryingatNight”,是“乌啼夜”,句法正确,而拖沓刻板。到“胭脂泪”,白润德也加了美人并转换了场景。不过布罗克的“泪湿胭脂”里,“胭脂”只是一个颜色的代称,可以指代女性的妆容或她衣裳的颜色,白润德则干脆让眼泪直接挂在美人脸上,与李煜对饮的女性益发形象鲜明。而美人的形象越鲜明,李煜的家国情怀就越模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大批汉学界以外的新生力量加入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译介队伍,各种译本和译诗选本迭出。既然译者的汉语文学功底深浅不一,不同译本的诠释角度各不相同,质量各有参差,那么,在单纯的文本译介之外,引导读者深入体味中国诗词韵味的赏析类书籍便顺势出现了。1976年,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著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ermannt Frankel)的《梅花与宫闱佳丽:中国诗选译随谈》(The Flowering Plumand the Palace Lady: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oetry)问世。全书分“人与自然”“男人与友情”“孤独的女性”“民谣”“离别”“情诗”等十三个主题,分类拣选一些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不受朝代和诗体的限制,只为便于赏鉴品评。李煜这一阕被归在“离别”的主题下:
Form: Tz'u; Tune Pattern: "Crows Cawing atNight"/调寄“乌夜啼”
The flowering trees ofthe grove have droppedtheirspring./林中的花树凋残了它们的春天,
Alltooquickly./都太迅疾。
Unbearable, thecoldraincominginthemorningandthewindatnight./难以承受,那早晨袭来的冷雨和夜里的风。
Tearssmeartherouge,/泪痕污损了胭脂。Drunkatthefarewell./在道别声中酩酊,Whenagain?/几时重?
Inevitablyhumanlifeisalwaysgrief,theriveral-ways/人生的创痛无从逃避,如江河总是
Flowseast./流向东方。
傅汉思用“Unbearable”对应“无奈”,将“胭脂泪”译成“Tearssmeartherouge”,已经很接近原文的含蓄美。他所重现的整体意境中,也不再有“美人”含泪与李煜把酒相对。傅汉思曾应胡适先生之邀,担任过北京大学的西班牙语系主任,有深厚的西方文学理论功底。旅居中国期间他对中国文学有了更直接的认识,返回美国后一直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其汉赋乐府和唐代诗人的研究成果享誉学术界。他的品析一方面引入西方文论,细说中国古典诗词意象叠加、并列和拼合的独特美学特征,一方面与西方诗歌作平行比较,对西方读者把握李煜的情思和艺术风格大有裨益。
以这一阕词为例,傅汉思首先交代了李煜是“弱小王朝南唐的最后一位君主”,厘清了此前关于李煜到底是“唐代诗人”还是“李唐皇朝王子”的模糊状态。其次,他指出这一阕《乌夜啼》以及《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这些抒写凄凉境遇和痛苦无奈情态的词章,是李煜亡国被囚时期的作品,明确交代了原文的创作缘由和背景。其三,他对词中“林花”“暮风朝雨”“胭脂泪”“水长东”等关键意象的进一步解说,也言简意赅。比如他说下阕的“胭脂泪”由上阕的风雨摧花承接而来,是实写残花带雨如泪,伤春之泪成血;“无奈”一句字面上缺失主语,似乎模棱两可,却起到了同时关合花与人的作用,是李煜喟叹命运多舛,自恨无力改变环境,人与景、物相融的精妙笔法。他还提到,以流水写离情或哀愁,是东西方文学里都很常见的化虚为实的表现手法,而中国诗词里的江河水一律“长东”,不是中国诗人们缺乏想象力,也不是确指他们思念或思绪的地理方位一律在东方,只因为中国的河流大多自西向东入海。布罗克译本舍弃“向东”而直接用“入海”,实际上是出于同样的,唯恐西方读者误解的良苦用心,只是傅汉思的解释更加清晰完整了。
经过近半个世纪,英美译家们斟词酌句,为李煜词打造了一条从文学艺术界走到学术界,从被随意、零散地拣选抵达被专门研究的道路。自学成才的克拉拉,半路出家的布罗克,师从名家的白润德,学养深厚的傅汉思,相继追寻着李煜即景抒情的遥远背影,为不同阶层的读者群提供了一个互为参照的,《乌夜啼》的英文样貌拼图。不论他们各自的译本与原文有多少出入,最后都用结句回到了一般意义上的永生长恨,则李煜的词句到此便超出了他个体的经验和感触,足以与共有生命缺憾、失意怅恨的全人类情同一恸。
优秀的古典诗词作品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英美译家们努力突破语言与文化的隔膜,谱写出了他们代中国人向西方讲中国故事的篇章。尽管诗词的翻译实在难以做到绝对等值,他们也证明了中国古典诗词整体审美体验的有效传达可以实现。到今天,一个“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从文化本源的诠释角度出发,主动向世界表达自己、展示自己。随着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便捷和深化,各国不同民族的文学意象也越来越容易被彼此理解、欣赏和接受。如何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达到内容和美感的自然和谐,为目标读者喜闻乐见,与域外译家互为镜像,共同描绘一幅更清晰、更完整的中国文学图景,是有志于向世界讲述中国的人们共同的重大命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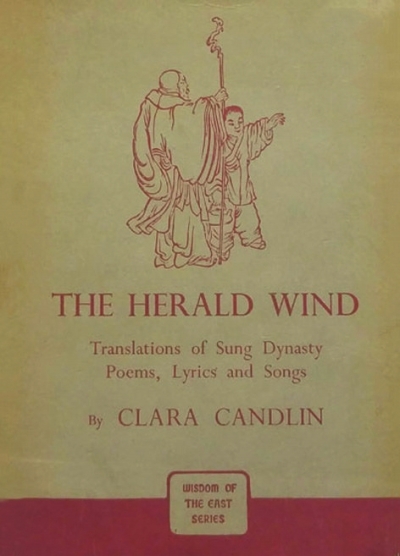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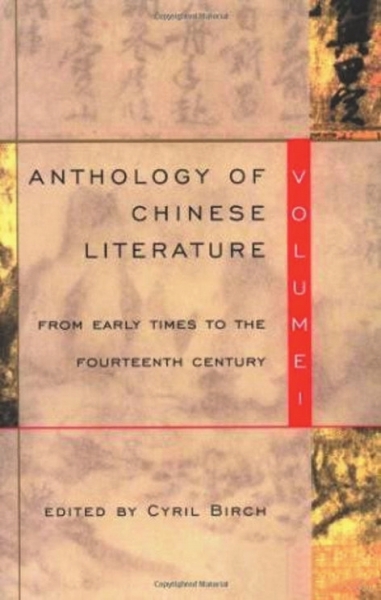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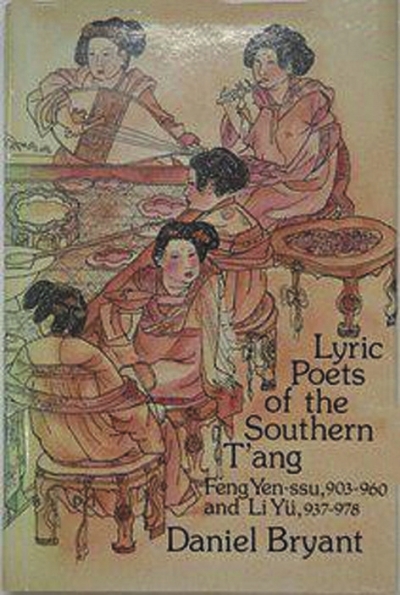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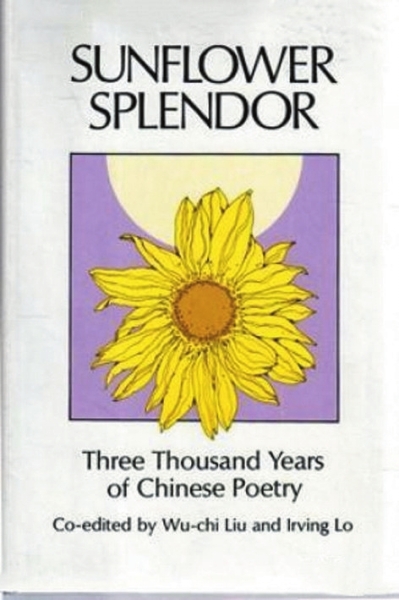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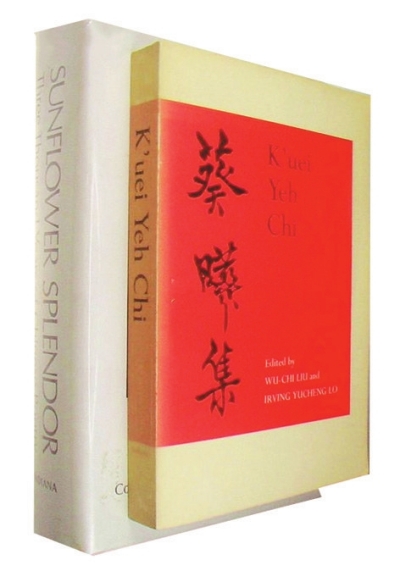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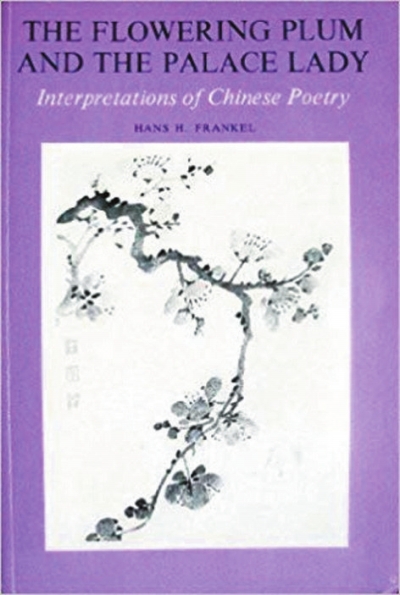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