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记得以前我们在对谈中,你时不时要对“创新”冷嘲热讽一两下。也许你嘲讽的不是“创新”本身,而是我们对“创新”的迷信或不适当的强调,但总是给我一种“创新在刘兵那儿讨不了好”的感觉。这件事情,我本来倒是“不持立场”的,或者说我自认为是一种超然的中立立场:我既不排斥创新,也不迷信创新。
等我读到这本《老科技的全球史》,我发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完全可以再进一步深入。
作者认为,我们以往习惯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描述,往往是以“创新”为中心的,如果我们尝试另一种思路,就可能有大不相同的结果。他主张以“使用中的科技“(technol⁃ogy-in-use)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这样,“将会出现一幅完全不同的科技图景,甚至也可能形成一幅完全不同的发明与创新图景”。这甚至让他认同了布鲁诺·拉图尔的激进观点:“现代人所相信的现代,从未存在过。”
我们习惯的以创新为中心来看待科学技术发展的思路,被作者称为“未来主义”。他写道:“我们因而把焦点放在发明与创新以及那些我们认定为最重要的科技上,这样的文献是二三流知识分子和宣传家的作品,像是韦尔斯(H.G.Wells)的书以及NASA公关人员的新闻稿,我们从那里得到的是关于科技与历史的一套陈腔滥调。”这番话还真有点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气势。
刘:
在开始我们的对谈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对一些概念和说法进行一点说明。诚如你所说,“似乎”我总是时不时要对“创新”冷嘲热讽一两下,当然这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因为,毕竟从科学史来看,整个科学史似乎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没有“创新”何谈科学的发展?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创新,本应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看的,但在过去很长时间,人们没像今天这样大谈“创新”,好像也没有太影响科学发展,反倒是今天人们过于频繁地让“创新”一词出现在各种场合,甚至形成一种贬值的滥用,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本书书名中的“科技”,原文是“技术”,这一译法上的问题,本身就意味深长。
尽管谈论的只是技术(这是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的),但本书确实有趣、有想法,说出了许多与当下主流声音有所不同的观点。不过这本书所讲的,与一开头你所提到的我的说法,在所指对象上并不完全一致,却也从另一个方向切入了我们关心的问题。
江:
本书主要讨论的确实不是对“创新”一词的态度和用法本身,但作者其实是希望通过他讨论的那些技术应用情况,来改变人们对“创新”的盲目推崇和迷信。你莫非被“反对创新”的可能罪名吓着了?我觉得你的说明和我上面对你的描述并无矛盾,你只是补充得更为全面了。事实上我们都不赞成对“创新”一词进行“贬值的滥用”,所以才会对本书表示欣赏,我才会推测本书能让你有“吾道不孤”之感。
我很久以来一直在想象(或者说盼望)一种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究竟有多少创新是真正有用的?比如,在足够长的时间段中对某个领域的专利进行统计分析,看到底有多大比例的专利是最终得到应用的?也许这样的研究项目实施起来非常困难,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一直没见过这样的研究成果发表。
和我上面想象的统计学研究不同,本书近似地采用了个案分析的路径。论述了作者选择的一些比较“老”的发明,是如何被长期使用的,比如美国已经使用了半个世纪的轰炸机B-52;而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创新,或者一直得不到实际应用,或者得到了应用也只是云烟过眼,很快就被人淡忘了。
作者主要是采用正面论述,提请读者注意身边许多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事物,其实是技术史上的重要发明——它们的重要性主要是以它们的长期应用来背书的。作者希望读者在阅读这些正面论述的内容时,能够引发思考:那些层出不穷的创新中,能够有几项得到广泛持久的应用?人们将太多的赞美给了那些不值一提的创新,却几乎忽视了那些一直在身边造福于我们的发明。
我倒不是被“反对创新”的可能罪名吓着了,尽管这样的“罪名”还真是会吓到不少人。也许,很多人根本就不曾想到过居然还可以这样思考问题。
要论证这种科技发展,是需要实际的例证的。科技史,就是提供这种例证的最合适的学科之一。此书作者恰好以这样的身份,以科学史的研究为基础,给出了似乎不那么有利于当下的“创新热”的观点和证据。
此书作者也并不只是中性地立足于科学技术史来谈问题,其论述也有着鲜明的当代问题意识。例如,他在讨论我们这里非常关注的“国家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的话题时,就提到了“国家经济与科技的表现取决于国家发明与创新的速度,这样的假设隐含了一种极端而广泛的科技国族主义”。而且这原是20世纪50年代晚期出现在美国的一种观点,现今却被我们广泛接受。“这一论点主张,如果想要赶上富裕国家,国家就要有更多的发明与创新;如果不能做到这点,该国就会沦落到最贫穷国家的水平。”“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或许是:全球性的创新或许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这点并不能套用到特定的民族国家。既然国内的创新并不是国家技术的主要来源,那么国内的创新和国家经济增长率之间没有正相关也就不足为奇了。富裕国家彼此之间以及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全球科技分享是常态。那么我们是否该抛弃科技国族主义而采取全球性科技的视角来思考呢?”这样的观点,哪怕只是作为一家之言,也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江:
除了“导言”和“结论”之外,本书正文的八章,可以理解为作者考察创新的八个方面。应该承认,作者的思虑相当周全,从这样八个方面考察创新,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而且具有示范意义。其中的“国族”一章,主要从国家层面讨论对技术创新的看法,涉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冷战、跨国公司等多个与创新有关的方面。
不过,对于作者的主要观点,我感觉还有讨论的余地。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为那些过眼云烟的创新辩护:
没有量,哪来质?没有那么多的过眼云烟,哪来那些持久应用的发明?例如,没有那些众多的过眼云烟的飞机创新,哪来成功的B-52?那么人们对所有新出现的创新都歌颂称赞,就有了足够的合理性。我们要采纳的本书作者的意见,应该是它的后半部分——我们确实应该对那些得到长久应用、因而为改善我们的生活作出了更大贡献的创新,表现出更多的敬意和关注。
你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已经从我们开头讨论的问题上有所转移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绝大部分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成果”,都在大浪淘沙中被淘汰了,只有少数存留下来,这也就是你所说的量与质的问题。这其实并不令人惊讶。按照学术的规则,没有“新”进展的研究甚至都没有资格进入这样的淘汰赛。但在我们的对谈中,我更关注的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会比以往更迷恋于大谈创新?甚至是在“贬值的滥用”的意义上言必称创新?以及这样近乎于反常的迷恋,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固然,《老科技的全球史》的主要案例谈的是那些并非最新的“创新”但却被持久应用的发现和发明,在这些发现和发明出现之时连“创新”一词都还没变得流行,但学术的规范也一直在起作用。这表明,至少相当多有用且好用的发现和发明,并不一定就是最新的创新,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而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还会去思考,我们如今大谈创新,又真的就直接带来了更多有用的创新成果吗?抑或更多地只是一种在概念和语言上的装饰,一种表态,一种夸张,一种掩饰,甚至是一种潜在的忧虑?
江:
我认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其实我们常见的关于创新的论述,通常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口号式的、歌颂的,用意当然是正面的;另一类稍微“深入”一点,基本上是“评功摆好”式的功劳簿,说创新带来了如何如何好的后果。但是和本书作者的论述相比,上述两类都明显缺乏深度。
作者试图区分,到底哪些创新才是重要的?他认为有必要考虑一些更为合理的标准:“根本重点是要区分使用(use)与有用(usefulness)、普遍(pervasiveness)与重要(signifi⁃cance)”。这当然不是文字游戏,作者有比较明确的所指。在他看来,许多昙花一现的创新成果虽然也曾被“使用”过,但很快就成为过眼云烟;而那些真正“有用”的创新和发明则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也是被使用),但人们往往对这些成果熟视无睹,反而不停地去追捧那些过眼云烟。
作为例证,作者特别提到了美国的B-52轰炸机(同温层堡垒),这种飞机1952年首飞,1962年停产,前后总共生产了8个型号共744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轰炸机至今仍在美国空军中服役,而且仍然是美军远程战略轰炸的主力机种。作者认为这样的技术成果就是“有用”的典范。也就是作者所强调的:“关于发明最重要而且有趣的一件事,是它展现出重要的延续性,而这些延续性却从来没有获得充分的认识。”
就算你讲的第一种“用意正面”的口号式、歌颂的谈论“创新”(其实要远超出此范围),也仍然需要直面其弊端。这种时时处处谈创新(甚至于带来诸多伪创新)的方式,现在几乎已经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各种场合,甚至影响到教育和研究的方式和评价。其实这样的做法,反而等于消解了创新,让诸多青年学者从一开始便觉得,所谓创新不过是口头上的说法,但又不得不按之行事,以至于“编造”所谓的创新点。对于科学研究立项和评价亦是如此。这样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是对真正的创新的最大威胁之一。所以,才会有你开头所说的我“时不时要对‘创新’冷嘲热讽一两下”。
这本《老科技的全球史》则部分地与我刚说的问题具有相关性,即让人们意识到即使创新重要,也不宜过分地时时挂在口头,反过来,对于“创新”的重要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也有必要进行一些反思。换言之,我们为什么要创新?这个问题在谈论创新时却往往被人们忽略。其实,创新最终极的目标,不还是为了让“有用”的“创新”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吗?如果以此为目标,那我们自然也就不应该因某种理念的先行而过分地去追求那些很可能是“过眼云烟”的“创新”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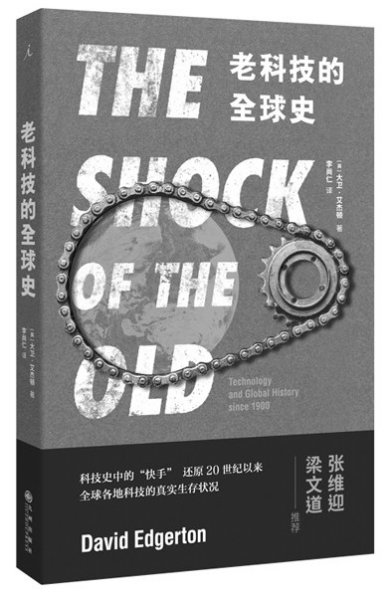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