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同样都是奥匈帝国治下犹太商人的儿子,但约瑟夫·罗特却是与弗兰茨·卡夫卡完全不同的一种人。他是一个有着出人头地野心的小镇青年,个性热情豪爽,热爱交际,是魏玛共和国的明星记者和作家。他嗜酒如命,也从不拒绝女性的好感,但却嫉妒心理极强,让每个爱上他的女人都备感痛苦。而造成这一差异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不像卡夫卡那样有一个强大的父亲,恰恰相反,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因为在他出生之前,他父亲就因为行为异常住进了精神病院,而家里人对此讳莫如深。可以说,“丧父”乃是罗特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件,而这也直接影响了他后面的创作。
矛盾的无家可归者
无父的身份为他的童年一定带来了很多困扰和麻烦,没准还要忍受边陲小镇(位于波兰境内的布罗迪)上的风言风语。这也使得罗特在人际交往中发展出两种矛盾的态度:时而拘谨审慎,时而傲慢自大。这其实是某种寻求认同感的病理表现。他要向周围人证明,那些父母双全的孩子并不比他出色。于是,他拼命用功读书,在代表权威与机会的德语学习上表现尤为突出,他成了他们那个年级唯一一个通过了高中会考的犹太人。因为没有父亲,他把德意志文化作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精神寄托,等于变相为自己寻找一个更加强大的父亲。他后来甚至在出身上故意矫饰,说自己可能是某个奥地利军官、某个维也纳商人或是某位波兰伯爵的私生子。
而童年与青年时期遭遇到的反犹主义浪潮,也使得他愈发坚定了融入德意志社会的决心。他开始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象牙塔来躲避外界的纷扰,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研读德意志思想的精髓来让自己进一步实现同化。在大学里,他也一直努力于取得好的分数以及受到教授们的重视。身份与认同其实是他内心最纠结的部分。他真的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国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把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看成了自己的“精神父亲”。所以,他在一战中自愿参军,据他自称还曾被俄军俘获,然而可能的证据都没有得到保存。但是,86岁老皇帝的去世,奥匈帝国的覆灭却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与转折:他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变成了无家可归者。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皇帝的死,给我的童年和整个祖国都划上了句号,所以我哀悼皇帝,同时也哀悼祖国和童年。”而这种“丧父”与“失去祖国”交织的失落感也集中反映在了他的两部长篇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以及《先王冢》里。终其一生,罗特都在哀悼旧世界的陨落,而新兴的民族主义在他看来则是毫无顾忌和危险的。
战后艰难的生活迫使他放弃学业,转而从事新闻业,逐渐变得小有名气。1923年是他取得突破性的一年。在这一年,他正式当上了德国《法兰克福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同时也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蛛网》。他以一战后的小人物为主角,刻画了被时代巨轮碾轧过的芸芸众生。在讽刺与情感投入上双方面的天赋为他的作品与评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他俨然是魏玛共和国的明星记者。漂泊的记者生涯似乎成了他的新身份。酒店成了他的长期住所,咖啡馆与酒吧也成了他安身立命的场所,那里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家和艺术家经常聚会的地点,他们的朋友们经常在那里看到他的身影。他们在高谈阔论,而他则在一旁写着小说。他是一名咖啡馆文学家。
他也终于成了家,他的太太弗里德莉克却因为生活上的种种问题得了精神疾病,被送去疗养,最后死在了纳粹集中营。而罗德则一直认为自己对太太的精神问题负有责任,因为他需要经常出差,对于太太关心不够。他也因此陷入了精神危机,为了承受住真相,他从此开始嗜酒如命。而这又加重了他的经济负担。太太的治疗费用、他对美食华服的喜好、酒店生活的各种开销、他对待朋友的豪爽大方让他债台高筑。他对报社和出版商都提出了极高的价格以及预付资金,这也让报社最终与他决裂。有一段时间,迫于生计,他甚至为极右翼的报纸写过文章。
1925年的苏联之行,让他失望地偏离了左翼立场,但他犹太人的身份以及对于纳粹的反感还是让他的书籍在1933年被毁禁。这也让他本就困难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茨威格帮助了他。两人从1928年开始相识,都是犹太人,都来自奥地利,又都喜欢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又都是当时的明星作者,经常旅行和漂泊,而且也都受到了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两人都最终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茨威格选择了自杀,而罗特则因酗酒走向死亡。罗特开始对他的犹太身份重新审视,他重新发现了自己对于犹太教的热爱,那是他的生命之根,而这也体现在了他的小说《约伯记》中。
1929年,他与太太离婚,迎娶了第二任太太安德莉亚,后一起流亡国外。但经济上的困难、罗特的酗酒与嫉妒问题最终让这段婚姻在1936年结束。他在比利时逗留期间,认识了第三任太太,一个和他一样喜欢喝酒的女作家科伊恩,两人一同来到了巴黎,但最终还是因为各种问题分道扬镳。他在巴黎寓居的酒店被拆迁,他又一次失去了家园。“我告诉我自己,家园总是会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于是,在流亡之中,他开始创作时代小说《先王冢》,反思自己的酗酒生涯《神圣饮者的传说》。他最后的一部作品是《一千零二夜》,但他没有等到这部作品的发表,在他得知犹太作家托勒尔自杀的消息后,彻底崩溃,常年因为酗酒而恶化的身体再也无法维持,他在1939年孤独地死在了收容病院里,享年45岁。
现代世界的激进批评者
与马克思一样,罗特也同样看到了现代性带给整个世界的巨大变革与伤害。在这样一个“摩登时代”,人们似乎一直生活在矛盾的时代感觉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商品物资的极大丰富,地球与自然被人类不断探索与征服,人似乎登上了一列叫作“进步”的历史火车,从此向着前方胜利进军;但另一方面,曾经支配传统社会的血缘纽带、邻里关系和世袭生活等传统情感已经不复存在,共同情感的匮乏,加剧的竞争关系,技术造成的人的“物化”和“异化”,职业分工造成的单子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壑加深,个体没有感受到温暖的包围,反而备感孤独。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一现代性问题的集中体现。旧有的家园彻底烟消云散,乡关何处、生命与情感何处安放成了罗特思考的永恒主题。而流亡似乎成了罗特以及现代人的永恒命运。
面对命运,是努力缅怀逝去的美好时光,还是憧憬先锋派的乌托邦幻象,罗特的选择无疑是前者。库切曾这样评论罗特的作品:“缅怀失去的过去,忧虑无家可归的未来,是奥地利小说家约瑟夫·罗特成熟作品的核心。罗特深情地回望奥匈王朝,把它当作他唯一曾有过的祖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与其他现代派作家一样,都是现代世界的激烈批评者,因此他依然是一位“现代小说家”。他一再强调要把文明上的进步与道德上的进步区别开来,“人可以发明收音机,可以发明电影,但他依然可以是一个恶棍”。所以,他对于未来充满了忧虑,他并不认为人类拥有实现乌托邦的可能性。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感伤与忧郁。
但在另一方面,罗特在艺术上的选择却与当时的先锋艺术家们大相径庭。从他的作品不难看出,他对现代性的怀疑已经深入骨髓,他拒绝使用现代文学的各种先锋实验,反而在作品中追求起秩序和统一,他把自己看作是19世纪那些伟大小说的继承者。他是一位观察与描写的大师,小说精准而且形象,但从语言实验的角度而言,却不会对后世的文学带来太大的新意。尤其是在他后期的小说中,他根本不关心现代艺术的各种尝试,反而坚定地选择了传统的叙述方式。所以,战后德国第一位诺奖作家伯尔才会将其称为德意志散文写作的“创造性保存者”。
罗特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作家,他虽然十分多产,但对自己的文字却非常负责。他从未使用生硬的语气和矫揉造作的句子,他不会用文字滔滔雄辩,也不会故意卖弄俏皮和风情。他的散文风格隽永且富有弹性,虽然纤细但不憔悴,筋肉发达但不瘦骨。虽然罗特是一个活在深渊边缘的人,总是在命运流亡中,但他的语言却总是透出一种完美的平静,是从容和宁静。
他的睿智是轻松、平静和愉快的。他喜欢运用柔和的色彩和强烈的对比。与那些擅写的作家相比,他的对话描写显得短小且寡言,很多关键性的东西都是通过停顿来表达。而他笔下的英雄总是沉默的。他的描述异常尖锐和精确,但他的用词却永远不会不雅或草率。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冷静分析者,又是个审慎克制的健谈者,一位多情却又总无情的叙述者:他创造了他的人物,他从不谴责他们,但他会把他们浸透在清晰的光线中,于是,所有的细节都变得清晰起来。与施尼茨勒和霍夫曼斯塔尔一样,他也是奥地利文学艺术的杰出代表。而奥地利文学艺术的鲜明特点就在于,能够以同情友善的形式讲述作家对苦难和生命易逝的洞察,并从生活的厌倦中提炼出真正的、充满爱的杰作。这也就是罗特带给我们的启示吧。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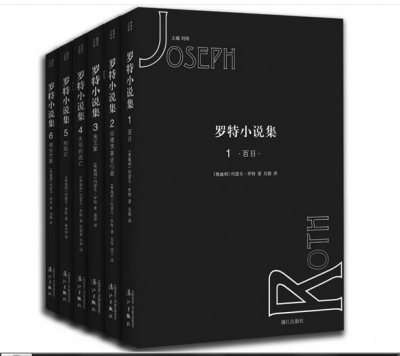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