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湖”的心结和眷恋
父亲陈旭麓,1918年3月31日出生于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一个名为白源湾的村落。幼时他随姐姐去田间捉泥鳅拾稻穗,徜徉在青山绿水之间,这种恬静而充满亲情的生活养成了他对故乡十分浓厚的情意,使日后远行的他始终对这片土地情牵梦绕。寻着父亲成长的脚印,我曾专程探访了他儿时读私塾的原址,学校的校史栏中还挂着他作为校友的简历。尽管爷爷供其读书的出发点是希望他日后从商,并由此光宗耀祖,可是他却并非如此想。因为父亲从小常听村里的老人说某某人“出湖”了,那也就是在说此人出息了。而“出湖”的本意就是越过洞庭湖,意味着胸怀大的境界,去见大的世面。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从乡间的私塾先后来到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以及当时在贵阳的大夏大学求学,“出湖”之说时时激励着他努力学习,孜孜以求。以后,他又受到进步思想的感召,筑下教育、科学救国的理念,并因此开启了他长达45年的教育生涯。
我们姊妹兄弟五个自小耳濡目染父亲的为人处事,也深受湘人生活习俗的影响。一口腊鱼腊肉、猪血丸子,总会勾起他对家乡的浓浓情思,而出生在上海的我们对这些也常常食之如饴。父亲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来到上海的,尽管在此生活了40多年,浓重的湘音却始终未改。他给研究生上课竟然需要高年级的同学作翻译,由此出现了多种不同方言版本的传译,引为笑谈。
1982年,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车文仪回湘任职,力邀父亲就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长。为此,父亲踌躇再三,一边是故乡在召唤,另一边却是家庭的难以割舍。因为母亲去世后父亲未再婚娶,要是成行,我们子女一时又无法陪伴前往,再则看着我们姊妹兄弟多未成家,心动之余,他打消了赴湘的念头。可是即便如此,父亲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仍溢于言表,他在《湖山情思》一文中这样写道:“人对哺育了他的土地,到老不能忘怀。尽管年光流逝,趁腿脚尚健,一有机缘,当再渡洞庭,品茗君山;还想攀登祝融峰,以偿平生未了之愿;也很向往张家界的千岩万壑。我爱故乡的名山大川,更爱那里的土丘小流,土丘小流里有着丰富的生活,还有自己童年的足迹。”
颠沛流离的三地教员
2011年清明前,春雨绵绵,春寒料峭。我从黔省城驱车一路高速40分钟便到了修文县,去寻找父亲母亲在那里留下的足迹。1943年3月,父亲刚满25岁,就出任了修文中学校长。68年之后,我也来到这所学校,时任校长,也是该校毕业生的袁曜热情接待了我们。修文中学建在龙岗山上,立于此间,俯身望去,修文县城尽收眼底。蜚声中外的明代大儒王阳明创立的龙岗书院旧址就在此地,这为修文中学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修文是父亲从事教育事业的起步之地,这对于他来说意义非比寻常。1982年秋,他重访这里,就留有“休忆年华伤逝水,眼前风物细评量”的诗句,抒发了久别后的感叹与感慨。
父亲在修文任教任职仅一学期,因闻报爷爷病重,便赶回湖南,遂即就教于家乡青树坪起陆中学(今双峰二中)四个学期。起陆之创建,是为了完成辛亥志士禹之谟兴学育才的遗愿。如今那儿人丁兴旺,二中也成了当地的骨干学校,小有声望。
1945年的初夏,父亲又来到了陪都重庆,通过大学同学介绍进入赣江中学任教。父亲的性格耿直,他在此校亦不顺遂,特别是在渝接受了民主文化人士的进步思潮的感召,在那他也仅待了不到一个学年。赣江中学是抗战时大后方为江西籍子弟办的学校,抗战结束不久,学校就已停办。寻找旧址,如果没有重庆同事的帮助,确是不知方向。当今大名鼎鼎的国宝级水稻专家袁隆平也曾是赣江中学的学生,我们循着他的线索,找到了昔日的“冷水场”(现已改称为“人和场”),而原有的万寿宫庙宇早已不复原来模样,只剩石门斑驳,残垣断壁。武汉大学的夏渌教授在父亲去世的唁函中曾提及,他与父亲曾在赣江中学共事。
留给儿女的印痕
人名只是个符号。从字面上看,我们的名字直白而易读,但都有着明显的历史印迹或寓意。大姐林林是五人中仅有的双名,却是叠字。我曾问父亲:“大家都是单名,为何姐姐搞特殊化?”他笑着反问:“单木能成林吗?林林就能成森林。”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国家号召植树造林。哥哥名“思”,与当年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着直接关联。随后,单名开始延续。二姐曰“克”,克敌制胜。她出生时,正逢抗美援朝凯旋,是名副其实的男孩名。我名中的“辛”字,则直接取自《辛亥革命》书名的第一个字,此书由父亲所写,于我出生的那年出版,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辛亥革命研究专著。弟弟称“同”,源自“天下大同”这一传统中国对理想社会的表述。近人康南海有《大同书》对此加以新的阐释,这也是父亲治近代史所思考的重要问题。从取名的不同缘由来看,我们五个子女的名字多少都与父亲研究历史有着一定的联系。
1970年3月30日,父亲52岁生日的前一天,刚满15岁的我赴江西临川插队,此前思兄已奔皖东和县,克姐远走东北延边,我们三人不行同道,天南地北。为此,父亲特意写了一首《送辛儿赴江西插队》的词。尽管词中透露出那个年代的浓厚气息,但也表达出了一个为父者对子女成长的殷切期望,并体现出他深切的爱国情怀。如今再读,我会想起儿时每周父亲要求我们练毛笔字、写作文。作文题目同一,不分年纪大小,我想那是他读私塾因材施教的翻版。父亲不是圣人,诗中抹不去时代的印痕,但是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拳拳之心跃然诗外,存我心窝。
一个男人带着五个孩子
1970年4月19日,母亲陆鸿逵患宫颈癌离世,时年仅51岁。母亲是抗战时大夏大学的学生,也是父亲的学生。1947年她与父亲在重庆订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沪上时代中学任史地教师。此前她还做过护士、法院的调解员。母亲非常能干,内外兼具,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那一代知识女性。我们姊妹兄弟的衣裳都是她亲手裁制的,她炒得一手黔湘川菜,至今想起还回味无穷。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熟悉病理常识,所患病症她本人早有觉察,只是不敢去医院医治,错过了早期手术的时机。因为那时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身陷长兴岛五七干校劳动,母亲怕被当作躲避运动的典型牵连父亲。半夜时分,母亲弥留之际,父亲是靠着一位好心的学生,踩着自行车驮着他,从长兴岛往家赶,一路走到天明……母亲撒手于家中,父亲总算在榻前诀别。
母亲离去,父亲很是悲伤。我当时刚去江西农村20天,接到电报,急忙往回赶,一进家门我抱着父亲痛哭,他也不停地流泪,那一刻在我的记忆中难以抹去。父亲为排遣心中的苦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悼鸿逵》三首七绝诗:
顽强从不计艰辛,竟使恶癌误此身。撒手小楼成永诀,骨灰一盒作新坟。
梁燕离巢初学飞,归来重雾失喧闹。声声只唤妈何在,化作啼鹃泪满衣。海滨风雨久相依,垂老那堪失伴飞。夜静悄听梯步响,犹疑抱卷迟迟归。
在我们儿女的眼中,父母的感情至深,他们贵阳相识,重庆缔缘,沪上携手,一路走来,从未拌嘴红脸。在贵阳,七姨陆鸿滨告诉我,当年外公看到父亲的求婚书时,大为赞赏,多次说有文采,并对其他的女儿说,你们未来别找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对象,向姐姐看齐。
少年丧母的我,一生敬佩的就是父亲。他在身陷长兴岛干校劳动的逆境中,每月去邮局给我们三个身处农村的孩子寄钱,还不时地书信勉励我们。那时我看到抬头“辛儿”的来信,总是泪流满面。特别是母亲逝去后,父亲没有续弦,一直护着我们五个孩子都成家立业,同时把自己的学术思辨推向新的境界。
高教三级的254元月薪
在小时候的记忆中,我家应该是高收入家庭,父母亲月薪分别为254元和94元。那时的1元钱可以买好多吃的,请个在家吃住的全天候保姆,一个月5元钱酬劳足矣。
父亲254元的薪酬是我出生的1955年评定的,标准是高教三级。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份月收入很高了。自小我没有感受过城市平民的拮据生活。“文革”起始,那一代爱党爱国爱民的专家学者,大多以不同的方式自减工资。父亲则以多缴党费150元的名义,将月薪减为104元。纵然如此,我家三代八口也生计无虞。到了1970年,因母亲去世,加之早先奶奶遣返双峰原籍,更有我与思兄、克姐纷走三地农村,自此全家的开销都落在了父亲的百元收入上。除此之外,父亲既要接济因姑父入狱而失去经济来源的姑妈一家子,还不时地拿出一些钱来帮助贫困的学生和年轻教师。
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五个子女先后都有了固定的工作与收入,甚至我的工资已大大超过了父亲从教30余年一成不变的254元,他也从无怨言。一个皓月当空的中秋夜,父亲约来了他的十多位研究生家中聚会,当聊到“体脑倒挂”的话题时,学生们满腹怨气,似乎学术之路要走不下去了。父亲陡然严肃而动容地说:“别人随便干什么每月挣500元,我做学问挣50元,只要我这50元对社会的贡献超过他的500元,我就继续搞学问。”他的这番话语使弟子们无语静场了许久……80年代中期,一次父亲在广州参加学术会议,分会场设在香港。有人提醒他去港赴会需要穿西装,为了符合礼仪,他竟然去地摊买了件廉价的衣服凑数,却给我们子女购买了上好的布料。
父亲一生清贫节俭,选择授业解惑就恪尽操守,追寻思辨就耐住寂寞潜心学术,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操和情怀在他身上得到彰显。尽管我们达不到父亲那样的境界,但从他身上传递出的人格魅力却在无形中感染、影响着我们。
永远的受重
1988年12月1日,适逢农历冬至前,父亲上午开会,中午未歇,下午又兴致勃勃与学生聊近期学术会议的思潮,傍晚破天荒地徒步三公里去托儿所接尚不足两岁的孙子。奇怪的是,那天我也破例地早回家,父亲高兴地让我陪他喝酒。菜已摆上桌,酒刚斟满,他突然站起身来拉着我的手,欲言难启,旋即痛苦地倒下。父亲随即被送到医院实施抢救,但为时已晚,医生也无力回天,父亲就这样因心肌梗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1989年5月,父亲安寝在钱塘江畔玉皇山脚下的南山公墓。每年的冬至、清明,我们姊妹兄弟都会去父亲的墓地祭拜。1992年父亲的祭日,我们同父亲的学生们一起带上刚问世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前去杭州。在父亲的墓前,我们将父亲的这本书点燃,徐徐升起的青烟寄托着我们对他的思念之情,同时也在告慰父亲,他的呕心之作终于出版了!
在我眼里,生活中的父亲是真正的男人,一个性格凸显、堂堂正正、挥洒自如、独立思考的男子汉,有责任、敢担当、顾亲情、兼柔情。常言云:施比受重。作为儿女,父亲给予我们的呵护关爱常怀心田,而无形中精神上接受转换至传承更重。
(《陈旭麓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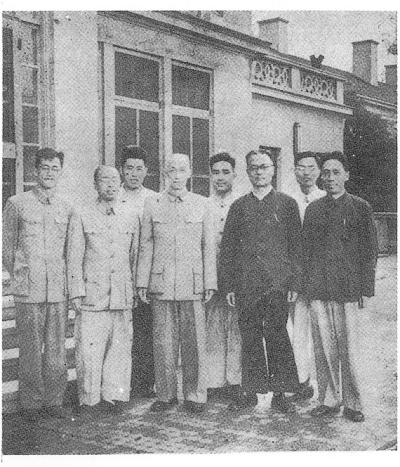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