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鍾山》在南京创刊,是伴随改革开放首先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依托江苏和南京丰厚的文学土壤,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化环境,经过几代优秀办刊人的探索创新,《鍾山》以其文学性与思想性兼具的特点、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质、坚定的人文立场,享誉汉语文学界。同年8月,在北京市东兴隆街一栋旧式木楼里,一本名为《十月》的大型文学期刊悄然面世。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本创刊号依然可谓装帧精美。创刊号刊发的作品散发出强烈的时代信号。茅盾、臧克家、杨沫等文坛大家的文学宣示,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以及“学习与借鉴”栏目中久违的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无不昭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划时代的告别与开启。
40年来,《鍾山》杂志的创刊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一同奔涌向前,曾以“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新状态文学”“非虚构文学”独领中国当代文学潮头,推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被誉为新时期文学最大的实验场、桥头堡和节拍器。而《十月》杂志也迅速攀上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制高点。《小镇上的将军》《蝴蝶》《相见时难》《高山下的花环》《黑骏马》《北方的河》《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绿化树》《腊月·正月》《花园街五号》《沉重的翅膀》《天堂蒜薹之歌》《雪城》等一系列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相继推出,不断引发读者的阅读热潮。据统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举办的历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获奖篇目中,接近三分之一首发于《十月》。
40年来,《十月》和《锺山》和同时期创刊的其他刊物一起,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卓著成就和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光辉历程,以大量优秀作品记录时代变化、反映时代精神,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中国当代历史不可或缺的载体。
中华读书报:您是哪年进的杂志社?对文学杂志是怎样的认识?
陈东捷:1991年,我研究生毕业来到《十月》杂志社当编辑,一晃27年过去了。其实我从上初中时就知道这本杂志了。我父母都是老师,我们家就住在我父亲所在的高中校园里,记得他们学校阅览室里就有《十月》《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这几份杂志。
1982年我进入大学中文系读书,才真正明白了这份杂志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地位。许多名作都是大学期间从《十月》读到的,如《高山下的花环》《黑骏马》《绿化树》《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晚霞消失的时候》等。当时图书馆里文学杂志非常受欢迎,抢到手非常不易。有时一篇作品读完上半部分还回杂志,什么时候能借到杂志读下半部分,要靠运气。当时感觉《十月》太牛了!想象中的编辑部更是一个神秘的所在。能到《十月》工作,在当时是完全不敢设想的。我很幸运能陪伴《十月》近三十年,并且继续陪伴。
贾梦玮:我是1996年进《锺山》,至今已是22年。28岁到50岁,我人生的黄金时段是在《锺山》度过的。因为读的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学校就知道《锺山》是名刊、大刊,而且知道编辑不要每天坐班,所以毕业时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到《锺山》当编辑。
中华读书报:刊物在40年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陈东捷:40年来,《十月》有些坚持一直没有改变。如坚持精品战略,不跟风、不媚俗;如坚守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办刊宗旨和包容、大气的风格;如致力于发掘和推出青年作者等。40年来,《十月》的影响力一直处于同类期刊前列,这一点也没有改变。但杂志40年间还是发生了不少变化,主要有:第一,从杂志刊期来讲,从1978年的以书代刊,到1980年改为邮局发行的双月刊,再到2004年改为月刊,出版《十月》《十月·长篇小说》两个序列,杂志容量大幅增加。第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闲暇时间面临更多的选择。特别是媒体技术的飞速进步和各种新媒体的迅速普及,使文学期刊逐步远离了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文学期刊发行量大幅下滑、生存和发展面临危机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十月》虽然发行量仍居国内文学期刊前列,也同样面临困难。事实上,国外纯文学期刊的发行量更低,但在大学、出版商和各种文化基金的支持下,仍然在记录时代、发现作者、文体创新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国内文学期刊可能以后也要向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十月》得到北京市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此前面临的困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第三,除了做好杂志内容,近些年来杂志社还围绕文学筹划和实施了多种多样的文学活动。如举办“十月文学奖”、在海内外设立“十月作家居住地”、与俄罗斯《十月》杂志联合举办“中俄《十月》文学论坛”、首创“世界文学期刊高峰论坛”、围绕青年作者的作品举办“青年作家论坛”等。第四,栏目设置更为丰富。如”小说新干线“”科技工作者纪事“”思想者说“等都成为杂志的品牌栏目。
贾梦玮:《锺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40年来《锺山》一直秉持着这样一种精神:以开放的态度不断改革。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等文学潮流中,《锺山》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后来倡导新写实小说、城市文学、非虚构文学,《锺山》是雄健的引导者;“河汉观星”栏目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发表了一大批作家论,并且倡导尖锐的批评与“锋言锋语”,对媚誉的批评风气起到了重要的纠偏作用。包括十几年前恢复诗歌栏目,也很好地接续了五四文学的传统。
40年来,《锺山》从未改变:人文立场、文学的初心从未改变,坚信文学的独特力量、坚持为人生的文学从未改变。《锺山》也一直在变,而且“善变”:这4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生遇到的问题层出不穷,文学要有所表现;文学的内外部环境也在变,文学必须变。
中华读书报:刊物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陈东捷:通过阅读大量最新创作的文学作品,可以更真切、全面地了解我们这个时代以及身处其中的人。在现实生活和虚构文本间不停地往来穿梭,是一件奇妙的体验。当然,长期的巨量阅读对身体和精神都是巨大的考验。但一篇佳作的发现、一位文学新人的推出、一场体现着自己和同事创意的活动取得成功,都会以由衷的喜悦作为补偿。在作品中看到了众多不同的人生,会让你在面对自己的人生时多一些从容和淡定。
贾梦玮:2006年我获得紫金山文学奖编辑奖的时候,有位记者在报纸上说,我把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献给了《锺山》,这话倒不完全是夸奖之辞。28岁至38岁,是一个男人激情与理性结合得最好的时光,而且是单身,没有拖累,吃住在编辑部,真正把编辑工作当成了事业。投入越多,你当然越珍惜,它对你的影响当然越大,《锺山》是我人生的平衡器,由此我知道我的时间去哪儿了,《锺山》给了我力量,也给了我稳定。
2005年我主持《锺山》工作后,我感觉自己和《锺山》越来越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就是我,我就是它。也像一对老友:互相鼓励、提携、批评、滋养。
中华读书报:现在刊物取得了哪些成就,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作为刊物主编,您又是如何应对的?
陈东捷:挑战随处存在,行业方面的、经济方面的、人员方面的、时间方面的等等。最大的压力还是内容方面的。建立优秀的团队、发现优质稿件呈现给读者,是办刊人不变的根本。以公平、公正之心对人、对事、对作品,营造杂志社良好的工作氛围和杂志的口碑,是做主编最重要的任务。目前杂志社集中了富有文学情怀和业务能力的同事。大家努力做事、相处融洽,对个人得失都看得很淡。
身处这样的工作小环境中确实能感受到幸福。我作为主编,就是要在杂志整体性要求之下,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同事的能力和积极性,共同去面对各种简单或复杂的任务。
贾梦玮:文学期刊的成绩主要体现在:首发优秀的文学作品,综合利用文学手段参与、引导文学潮流,组织文学活动,引导文学阅读、培养优秀读者等方面。发现、催生、发表优秀的文学作品当然是《锺山》的主要成就:有两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十篇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涵盖了小说、散文、评论、纪实等所有门类;还有获得其他众多奖项的作品;更有虽未获得大奖但思想新锐、带有探索性的优秀作品。《锺山》还凭着文学的敏锐性适时策划了新写实大联展、城市文学研讨会、联网四重奏、新状态文学、新生代作家研讨会、“河汉观星”作家论、非虚构、作家与知识分子讨论、江南文化与江南文学讨论、新时期十大诗人与十大长篇小说评选等重要文学活动,有力引导和推动了汉语文学的发展。在组织读者与作家、编者交流,评选优秀读者,培养纯正文学趣味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网络以及网络文学的出现和迅猛发展改变了文学生态,文学期刊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可否谈谈刊物在新媒体方面的发展?
陈东捷:目前已开设微博、微信公众号,在亚马逊kindle平台开始了电子杂志销售,已着手将创刊早期的纸质期刊进行电子化处理。新媒体是发展方向,文学期刊与新媒体结合目前尚未有理想的商业模式,我们一直在观察、准备和尝试。
贾梦玮:《锺山》世纪之交就创立了自己的官方网站,后来经过多次改版,目前已经形成了独立网站、微信、微博相配合,电子版订阅、及时评论并提供背景阅读、音频、视频等相融合的文学融媒体。据我所知,这也是目前唯一的融媒体文学期刊。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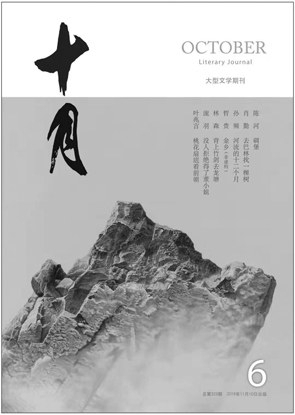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