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的交往,至少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印度的了解,从最早的传说,到后来相对详实的见闻,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知之不细,到知之渐细,前后留下了许多记载。中国古代的史书,提到印度,包括印度一些国家的名字和“国情”的不少,但直接提到印度国王的名字和个人事迹的却不多。这中间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公元七世纪印度的国王戒日王。
中国的史书中,关于戒日王的记载,为什么相对会多一些,详细一些?仅仅是因为他在印度历史上有名吗?是,也不全是。说是,是因为戒日王的确是印度历史上一位有名的国王。说不全是,是因为戒日王如果没有与中国历史上两位同样也很有名的人物有过密切的交往,中国的史书不会讲到他那么多,他在中国也不会那样为人所知。中国的这两位人物,一位是唐代的玄奘法师,一位是唐太宗。
放开来看,公元七世纪之时,在中国和印度,玄奘、唐太宗和戒日王,三位都是杰出的人物。
戒日王在印度是怎样有名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印度独立后不久,一些当时印度最好的历史学家合作,撰写了一部大部头、十余卷的印度通史,书名TheHistoryandCultureoftheIndianPeople。其中的第三卷,书名是The ClassicalAge,书中的一章,题目是HarshaVardhana and His Time。 HarshaVardhana是谁呢?就是戒日王。这一章的撰写者不是别人,是五十年代印度最有名的历史学家R. C.Majumdar,而Majumdar也正是这部大部头印度通史的主编。至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把戒日王称为“羯若鞠阇国”国王,说戒日王从羯若鞠阇国出发,经过南征北战,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几乎整个中印度和北印度,成为当时印度的“霸主”。这一点,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方面材料的证实,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的印度学者,或者把戒日王称作“羯若鞠阇国王”,或者称作“摩揭陀王”“摩腊婆王”,或者称作“邬阇衍那的庇护者”,甚至是“北印度王”,更甚者是“五印度之王”。这些都可以说明戒日王在印度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知道戒日王这个名字,还是在三十多年前。那时我在北京大学念研究生,我们的课程之一,是学习梵语,包括选读梵语的文学作品。梵文文学作品中有一部书,叫《龙喜记》,作者是戒日王。除此之外,我当时的论文题目和研究工作,很大一部分,与唐代中国求法僧,尤其是玄奘法师和义净法师的著作有关。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都有专门的段落,讲到戒日王。我因此需要了解戒日王,除了中文方面的材料,我还想看一下国外的学者有没有研究的著作。我在北大图书馆寻找,我发现,图书馆里真收藏有一本专门研究戒日王的书,作者是D.Devahuti,书名Harsha:APoliticalStudy。这多少让我有点惊喜,因为我知道,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北大图书馆收藏的外文书,五十年代前出版的不错,五十年代后的不多,中间有个明显的缺段,这本书1970年出版,但图书馆却有收藏。
D.Devahuti的书,在当时看,写得不错。只是我发现,戒日王的研究,很多地方,尤其是涉及到具体的历史年代,需要依凭的是中文方面的史料。但作者在中文史料的使用方面,却存在一些问题。作者不懂中文,依靠的是英文翻译,有的翻译得很早,已经过时,有的翻译得不好,使用起来自然会出问题。这让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既然戒日王这么重要,什么时候,中国的学者是不是也应该在这方面作出一点贡献?不过,三十多年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戒日王跟中国有不少的关系,中国学者对于戒日王的研究,多年来实在太少,已有的不多一点研究,也谈不上深入。
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现在有了改变,那就是张远这部《戒日王研究》。张远的书,基础是她2013年6月在北京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后来又加以补充和修改而成。这样的工作,依我所知,国内还没有人做过,国外虽然有学者做过,但涉及的往往是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个方面,整体性的研究也很少。
与戒日王相关的资料,张远收集的,可以说比过去研究过这个题目的任何学者都更多,更全。当然,张远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后来居上,可以利用晚近一些的新材料。但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可以排除,就是因为我上面提到的,历史上印度的国王,没有一位像戒日王这样,与中国有过这样多的、以个人为对象的接触。因为玄奘和唐太宗,汉文的文献中史无前例的有这么多的有关一位印度的国王的记载,这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切入点。
不过,切入点也只是切入点,方便也仅仅只有一点点的方便,如果不能把视野放开,不能广泛地把印度方面的资料,尤其是考古的发现,与汉文的材料结合起来,分析,考证,解读,仅仅依靠后者,要想研究戒日王,也是不可能的。做这样的研究,首先需要搭建的,是一个多语言资料、完整的研究框架,同时还要兼顾到历史、文学、宗教、考古各个方面。张远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包括在学期间争取到机会,到哈佛大学访学一年,广泛地寻找和查阅各类资料。在我看来,她完成的工作,无论对于国内的印度史研究,还是印度梵语文学史的研究,还是中印关系史的研究,都有意义。
除了资料的收集,张远的研究,还包括分析问题。这方面我只举张远书中的一个例子。
玄奘法师到印度求法,在印度的那烂陀学习佛教的时候,正是戒日王的时代。戒日王是当时印度最有影响的国王,他听说在那烂陀有一位从中国来的僧人,于是约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五有一段,记载了二人首次见面时的对话。
戒日王见到玄奘,第一句话就问:“自何国来?将何所欲?”
玄奘回答:“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
戒日王问:“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
玄奘回答:“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戒日王又问:“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民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
玄奘回答:“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前代运终,群生无主。兵戈乱起,残害生灵。秦王天纵含弘,心发慈愍,威风鼓扇,群凶殄灭,八方静谧,万国朝贡。爱育四生,敬崇三宝。薄赋敛,省刑罚。而国用有余,氓俗无穴,风猷大化,难以备举。”
戒日王于是感叹说:“盛哉,彼土群生,福感圣主!”
这一段记载,也见于玄奘弟子慧立和彦悰为玄奘撰写的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及其他的一些史书,包括《新唐书》《旧唐书》,文字上虽然稍有差异,但基本一样。玄奘这段讲述,颇具戏剧性。但就是因为太有戏剧性,后来的人就有了怀疑:这是不是玄奘为了讨好唐太宗,无中生有,编出来的一段故事?
说实话,最初读到这一段时,我也有疑问。所有的疑问中,最突出的一点,是玄奘与戒日王对话中提到的《秦王破阵乐》,当时的戒日王,能知道中国的《秦王破阵乐》吗?但张远对此做了分析,结论是有可能。我不敢说这绝对地正确,但张远的分析和推断,有一定的道理。古代世界物质和文化信息的交流,频密的程度往往超出我们今天的设想。中印是近邻,作为乐舞的《秦王破阵乐》,当时为印度人所知,不是没有可能。张远在她的书中讲了,《秦王破阵乐》在唐代传到了日本,也传到了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西藏,这在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时代相同或相近,如果说《秦王破阵乐》作为乐舞,能够完整地传到西藏,此前一个有关《秦王破阵乐》的消息传到了印度,我们似乎不应该奇怪。玄奘讲述的故事,是有些“歌德体”的风格,但放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和话语背景下考虑,可以说有套话,但不是假话。
戒日王与唐太宗,虽然没有见面,但大唐与戒日王的国家——史书里以“摩揭陀国”相称——之间正式的外交往来,却是从这两位大国君主互派使节开始。中印外交历史上的几位有名的人物,梁怀璥、李义表和王玄策,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受命出使印度,其中的王玄策最为著名,曾三次出使印度。对此张远的书也做了很好的论述,她的统计,从贞观十五年(641)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八年之间,戒日王与唐太宗之间,各派出使臣三次,双方合起来共有六次之多。这真可以说是中国和印度外交的一段“黄金时代”。
我上面所讲,仅仅是书中所讨论的一两个问题,书中更多的内容,涉及到印度历史、考古和梵语文学史。这方面的问题,真正做得多的,是印度的学者。张远的书以中文出版,而印度研究历史、考古以及梵语文学史的学者能读中文的很少。学术的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开放和交流。因此我以为,张远下一步的工作,还应该争取把她的研究成果用英语表达出来,与国外的学者作更多交流。
张远热爱学术,也很勤奋。我希望,也相信她能够继续努力,今后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有更多的成果。张远年轻,我以这样的话,与她共勉,她应该能接受吧?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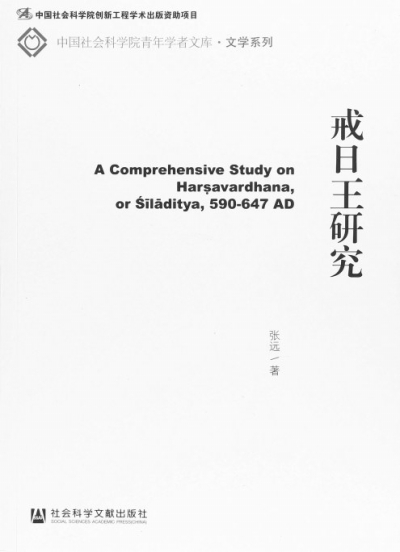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