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说
李芳(云南师范大学)
为了解村里的事情,我总要观察村民的生活并与他们聊天。今年年初的一天,我在滇南乡村的一个小菜市场里,从围观麻将大战的人群中,找到了一位满脸皱纹但据说头脑清楚的老人。
观看战况与参战的都是村里上了年纪的闲散男人,没有一个女人。看到这种情形,我心想:凑过去不合适,肯定招人话柄,等散场吧。这一等就等到了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在村边的大榕树下,我看到这位93岁的老爷爷在大日头下扛着一捆绿皮甘蔗从村头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上前与他搭话,说明意图后,李老爷子回了我一句:“和你不熟,不给你讲。”我补充了一句:“我有一个朋友和您三儿子熟,您儿子说可以找您的。”老爷子又回我一句:“我儿子不在家,等他回来再说吧。”我顿时无语,意识到这是一位不好说话的老爷爷,尽管看起来很慈祥、很面善。
晚上,我灰溜溜地回到住处,和常在村里走动且与李家老三有来往的一位朋友说起这次夭折的访谈。可能是出于对我的“同情”,朋友和我谈起了李家先辈的一些事情。朋友的讲述自然是从其他村民以及李家人那里听来的。
李姓老人的祖父早年在村里务农,但因为当时村中人多地少且土地贫瘠,生计难以维持,为谋求活路,也曾在临安到个旧的驿道上走马帮,可这样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且要面临极大的风险。后来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李家的这位祖先在个旧的一片矿尖里发现了富矿,获利丰厚并致富,摆脱了穷困的生活。李家由此跻身临安城富户之列,并与同为富豪的沈姓与郭姓联姻。因着联姻,李家在一定程度上与临安城里的豪门大族也建立了联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李家在民国初年的发展的。
李老爷子的父亲接手家业后,在临安城里成立了商号。凭借他本人卓越的经商能力,李家锡矿所采大锡出口香港,生意规模极大。与此同时,他本人也为村里做了一些事情,如出资打井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公私合营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于是,李姓老人就在改造后成立的锡矿公司上班,成为村民所说的“挣工资的人”,20世纪80年代退休后回乡养老。现在和在村里以种地为生的大儿子一家住在祖辈留下的、极为宽敞的、上下两层的木结构老房子里。但这栋老房子还有四五家其他姓氏的居民,他们均是在土改没收地主财产分配给贫下中农时搬进来的。
听完这段叙说,我顿时觉得李家祖辈的故事很有传奇性,李家的发家史也是够稀奇的,得有多好的运气啊!我想:李姓老人也是一位精明之人和“隐士”,在乡村里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和自由,比待在由混凝土、钢筋构筑的城市空间里强多了。
第二天,老人的三儿子回来了,同意我和朋友去他父亲家拜访。路上,朋友和我说,他家的门很难进的。我顿时心生困惑,村里人一般是可以随意串门的啊。
李家位于村子中央,我们在一条曲里拐弯的小巷里走着。走到巷子尽头时,看到一座门楼高耸的宅院。仔细打量了一下,发现大门两边的墙缝中还插着带灰烬的半截香条。一条灰白色的土狗突地从不甚低矮的木制门槛儿里跳出,冲我直吠,凶猛异常且非常吓人。在一连串的犬吠声中,李家老三出来喝退了他家的狗。此人一脸精明相,头发略有些花白,近五十岁的样子,衣着讲究,谈吐“不凡”,完全不同于他那位有些木讷、内向且弯腰驼背的大哥。
我们进到堂屋时,李老三的父亲不在,给我们讲故事的就是他了。他父亲对于村里的情形了如指掌因而有人借此来访,这件事显然是让他极为自豪的,可能还有几分自傲。但我看得出来,他更感兴趣的是讲自己“辉煌”的家史,如曾祖、祖父的风光、名头和排场、财富以及强大的人脉关系等。他的叙说,很明显地有“精英”史的痕迹在内,出言必谈民国时期云南政界大人物与其祖先的关联。我们谈话的时候,他主讲且谈锋甚健,他大哥几乎是不插嘴的,一直很沉默。
谈到祖先盖房的历史及盖房的巨额白银花费,李家老三于此很是自得,特意强调了自家祖先的阔绰。出于礼貌和好奇,我们参观了他家老房子上的各种装饰性的木雕、山水画、书法以及作为转角跑马楼式建筑之一的美人靠等。颇具文人雅士情趣的院子里,还有一大盆正开着紫色花的三角梅做装点。梅树下方摆着一个装满了水的龙纹石缸,细看,石缸上还有民国某名人的题字。此物显然是其祖父时代留下来的,现从事房地产开发工作的李老三很是看重这件“古董”的市场价值,貌似对它的期望很高。
李家老爷子每日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按时回家。他回来的时候,我和朋友正站在他家堂屋屋檐下,他把买来的且已经加工处理过的排骨和莲藕递给满脸沧桑的大儿子后,就径直进屋看电视去了。对于父亲的一声不吭,李老三并未在意,而是接着说:“以前我家还有自己的书房和厨房,就在这个院子里,后来都给拆掉了。”
交谈中,我回头瞥了一眼,李姓老人看的节目具有很浓的怀旧感,讲的是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的事情。此后,身着草绿色衣服的老人再没有和我们几位说过一句话,十分专注,像是一尊雕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只有家养的猫咪进进出出。
李家老三送我们出来时,倒很是客气。站在门口时,原先很凶猛的狗围着我们跑前跑后,显得很可爱、很友好。看我们注意到他家正对面的屋子时,李老三说:“这里本来是有一堵照壁的,集体化的时候给拆掉了,办起了养猪场,屋子是家里后来才建起来的,风水好。”李老三笑着说。
告辞时,李家老三仍然很有礼貌和风度。回去的路上,我和朋友谈论起他讲的“故事”的真实性。我觉得有很多夸张的成分,攀附大人物和期盼发达的心态一览无余。而朋友也有同感,说这个人喜欢吹牛和夸耀,比较势利。他进一步说,李家有位近亲,人是好人,很正派,但李老三看不起他,就因为他家穷。至此,我更是深深地明白了为什么他家的门难进。精英的“精”,对于李家的后代而言,在于精明和算计,而不在于才华、文雅和为民。
听完了一部滇南乡村的“精英”史,看到了乡村里的“精英”后,我不由想到“精英”史的背后,遮蔽的是怎样的“平民”的历史?世人或许更羡慕权势与富贵,向往“精英”或社会上层人士的生活,那平民的生活和经历如何得以表述?
在被讲述的故事中,李家历史上的贫与现实中的“平”似乎不再重要,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豪族的往昔繁华和子孙对于繁华的追求、向往与回忆。无论是李姓老人还是他的三儿子,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都是在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一部历史。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叙述者的心性与心态。谁是平民?谁是精英?平民视角与历史—现代化视角下的李家家史和村落史又会是怎样的?这似乎又是复杂而错综的,抑或是我思虑过度从而陷于过度“解构”和“反思”?也未可知吧。
文字下乡的时代际遇
王华(江南大学)
我的田野地点是一个位于太湖东岸以捕捞为支柱产业的渔村。全村总面积1.66平方公里,1969年“陆上定居”政策落实之后“围湖造田”而成。全村一共1300多户,4000多人,在册登记的专业捕捞船只共计720艘,运输铁驳船270艘。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渔民家庭被允许“单干”之后,渔家的收入逐年提高,渔村新建的一栋栋临湖别墅就是最好的证明。根据渔民的经验,每年只要工作四个月(一月至八月是太湖的法定禁捕期),人均纯收入基本上都能超过十万元。即便如此,青壮年男女还是不愿意进入老祖宗传下来的行当,纷纷撇下渔船跑去从事其他白领、蓝领的工作,哪怕收入没有渔业捕捞可观。这或许是对现代文明的追求,抑或是对自卑的逃离,年轻人们选择了去外面世界闯荡。依旧坚守此业的是那些上了岁数的老渔民,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祖先传下的生计。因此,每逢周末,在市里工作的渔民子女便纷纷开着私家车回家看望父母,离开时带上父辈们捕捞的湖鲜,这渐渐成为“渔村—城市”二元关系的一道风景线。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提着沉重的行李来到了村里唯一的一家民宿,准备暂时先安顿下来,以图后计。在与民宿老板的儿子较量了几个回合之后,我终于以较实惠的价格拿到了一间房间。房间在顶层,透过狭小的玻璃窗,我可以看到停泊在避风湾里的渔船。大大小小的渔船在波浪的颠簸下发出“咯咯咯”的声音。桅杆上高高地吊晒着一盘盘的鱼干和虾干,少数几艘船上晾晒着衣服,却见不到一个渔民的身影。偶尔有一只麻雀孤零零地驻停在房间的窗台上,给初来乍到的我平添了几许思绪。
对于一个封闭的水上社会而言,一个陌生人的到来,特别是一个以调查者的身份出现的人,无疑能让他们谈论好一阵子。当他们听到要调查渔民生活时,都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他们自认为渔民群体不值得被关注,这大概跟渔民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有关。传统时代,太湖渔民是强大的帝制共同体的“化外之民”,他们穷而无告、弱而无助,悲苦地生活在茫茫的水面上,处于整个社会的底层和边缘,其社会地位远远不及农耕文明的陆上人。
对于渔民而言,读书人是他们敬重的群体。我尽量放低自己的姿态,把自己当成好问的“小学生”。事实上,我也确实不了解渔民文化,需要潜心学习和领悟。但是,每次我跟他们交流仍令他们腼腆不安,脸上泛出一阵兴奋的红晕:“哎呀,采访我?一个大博士采访我老太婆,我不好意思咯。”吴侬软语的话音里却又掩盖不住内心的自卑:“我们都不识字,不会说话的。”对于没有接受过多少学校教育的渔民而言,让他们准确地析解和表达出系统复杂的文化,确实有点难为他们了。存在于渔民“头脑和心灵”中的文化是一回事,渔民用语言表达给我听是一回事,而我的理解却是另一回事。这让我感到若将渔村的文化现象,经过表达、翻译、理解之后,用可供阅读的术语固定于纸张上确实不容易。换言之,仅凭深度访谈,我们无法达到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意义上的理解。因此,在不善言辞的渔民群体中开展调查,身体力行地参与、体会他们的日常活动,透过局内人的眼睛去看文化显得尤为重要。
闷热的夏夜,在品尝了知名的“太湖十八浇”的夜宵后,我回到房间。正准备入睡,忽闻楼下一阵吵闹,我透过窗户看去,是几个渔民与外来建筑商发生了口角。为了不错过观察的机会,我迅速穿上衣服匆匆下楼。原来,一辆旅游大巴停靠在建筑商的办公楼前面的场地上,影响了办公室的视线。建筑商耍横地动用了两台汽车前后夹击,堵住了旅游大巴的移动,并索要两千元的“损失”费。大巴司机试图与他们沟通协商,但没有效果,反而被其中一人抡了两拳。出身于本地渔民的大巴司机无奈之下,急忙打电话通知亲朋过来帮忙。于是,一大群渔民纷纷从家里出来,聚集在建筑商的办公楼前,要求对方将大巴前后的两台车移走,并赔礼道歉。然而,建筑商非但不予理睬,反而紧闭办公室的大门,睡觉去了。渔民情绪激动起来,有些人主张砸门冲进去,有些人试图砸车,均被民宿老板和几个船老大制止了。在等待警察到来的时间里,几个年老的渔民认为今晚发生的事是外人欺负渔民的典型事件,并追忆叙述了人生经历中的一件件被欺负的血泪故事。
警察的到来并没有令情况好转,于是决定将双方带去派出所进行详细的调查处理。临走的时候,一名警察需要征询两名证人,一同前往派出所协助调查。这下渔民们犯难了,谁去合适呢?一时间大家默不作声,好像静静地等待着什么。一个最先在场的渔民自告奋勇,却被某个船老大一顿呵斥,退缩到人群里。有个大胆的妇女当众建议应当找“会说话的”人。大家小声地议论着,权衡着,民宿老板建议他的儿子去,理由是他是渔民的后代,懂得维护本地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是地方一所大学的高才生,现在市里从事人事工作。毫无疑问,他的资格选择通过了。不过,民宿老板推举的另一个渔民,虽然在村里是个捕捞能手,为人正派,但他因胆怯而自我放弃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警察开始催促,但另一个证人还没有产生。大家开始焦躁起来,议论的声音也渐渐变大。突然,在我身旁的一个老渔民大声地喊道:“我们叫王博士去吧!”霎时间,大家齐刷刷地把目光聚焦于我,开始重新认识和掂量我的存在,并七嘴八舌地分析、评估着我去做证人的后果:“他是外人,会不会帮我们?”“人家读了一肚子的书,肯定懂道理,不会瞎来的。”接着,民宿老板拉我到旁边说了一些话,强调渔民们让我“去正义一把”,不要辜负了。最终,我通过了选拔成为证人。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做证人,而且是被甄选出来的证人,内心充满了兴奋和紧张,又有些受宠若惊的惶恐。不过,我注意到,被选来作证的人有个共同点,即在渔民看来我们是“会说话”的读书人。在水上社会中,识字念书是一项比较奢侈的活动,尤其是在传统社会。在他们看来,是否读过书是区分“会不会说话”的标准。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识字、没念过书则被认为是“愚”。事实上,传统社会向来有文字崇拜一说,敬祀字祖、敬惜字纸便是其表现之一。在封建社会早期,能够掌握和运用文字的人一般属于社会的权力阶层,这无疑增加了文字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反过来看,文字崇拜却恰恰反映的是文字长期得不到普及,普通大众缺少学习文字的机会,以至于衍生出一种阶层的象征。
这种文化的特色在费孝通看来是有一定情境性的。在两篇有关文字下乡的短文中,费先生认为,乡土社会的本质决定了“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情达意的唯一象征体系”,而且批判了仅凭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断定乡土社会中的所谓“文盲”与“聪明”的轻率做法。若结合渔民的情况而言,“会不会说话”的判别标准是识不识得字、有没有读过书,恐怕这也是一种文字崇拜的表现。当然,水上社会中的渔民群体内部的面对面交往,并不是愚蠢到字都不识的地步,而是在不需要文字的情势下社会生活依然能够得以维系。但随着社会的变迁,渔民的生计基础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们不得不上岸与其他阶层群体接触。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的现代性变迁是产生渔民社交尴尬现象的缘由所在,亦是“文字下乡”的时代际遇。
两者之间
薛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2009年的夏天,我第一次来到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热贡地区(注:今同仁县)。那时我正在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择田野考察地点。热贡(Rebgong),是一个藏语名字。藏族小伙子们挂在嘴边的是一个虽不准确,但足够浪漫的汉话翻译——“金色的谷地,梦想的故乡”。
这片金色的谷地里,世世代代居住着画神的人。“唐卡”(thangka)一词也来自藏语,《藏汉大词典》中解释为卷轴画,常以天然矿植物为原料,绘制佛本生故事、历史风俗、历史人物等。在2009年,唐卡、堆绣、泥塑等热贡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藏传佛教唐卡艺术是热贡地区几个藏族村庄的主要经济来源。
男女有别、尊卑分明,仍然是这些藏族村子保守的传统。在热贡,画唐卡赚钱的主要是男人,女人的社会地位普遍比男人要低,受教育的程度也低一些。大到田间劳动、修房子、背泥土,小到烧火做饭、清理屋子,都落到女人的肩上。哪怕是几家人外出游玩野餐的时候,也常常是男人们坐在一边,女人们带着小孩儿坐在另一边,座次也是按照年纪的长幼顺序排好,丝毫不乱规矩。
我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总是以观察者的角色出现在热贡的社会生活中。在当地社会的性别划分中,我往往处于非常模糊的地带。村里人都知道我是做研究的,是个“文化人”,所以对待我和对待村里其他女人的态度十分不同。除了一些宗教禁忌以外,男人们能参加的活动,我基本都能参加。当然,女人们日常的活计,我也可以跟着一起做。虽然田野调查的工作常常让我处于一种“无性别”的状态,但毕竟我是一个女性,而且,我所生长的环境,对于女性的观念和这里有很大的不同。
这一天是农历的正月十六。白天的时候,一个措瓦(注:土语中部落的意思,指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联合)的二十几户凑在一家人那里念经。念到下午五点多,这些家的男人们临时决定,大家凑点钱,让这二十几家的媳妇晚上到县上去搓馆子。我借宿那家的嫂子也去,她把我也一道拉去。嫂子说,这二十几家的男人在几辈以前都是近亲,后来因为结婚分家,没再住一起,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平时大家都忙,没时间聚会,过年最后一天,这些家的男人和女人们才会凑到一起。虽然措瓦里的媳妇们不一定是血亲,但都来自同一个村,大家很熟,现在又沾着姻亲,所以关系特别好。一听说要去县上吃饭,媳妇们都很兴奋。她们飞快地脱下厚重的藏袍,换上五颜六色的羽绒服、牛仔裤和高跟鞋,到公路上去搭车。
天黑前,我们赶到县上一家回族人开的清真餐厅。据说,村里人请客办酒席都会选这家清真餐厅。有人家刚刚在饭庄办过婚宴,大红的“囍”字还挂在大厅的墙壁上。这会儿男人们还没到,媳妇们凑到红彤彤的墙壁前,兴奋地吆喝着,让我一张接一张地为她们照相。独照,合影,几个女人互相把衣服换来换去,很快就拍出一百多张照片。她们在镜头前显得有点羞涩,笑得也不太自然。可一拍完,便原形毕露,不顾旁边还有人等着拍照,尖叫一声从我手里一把抓过相机,急着从LCD里看自己的样子。
因为交通不便,村里的面包车来回运人,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所有人才到齐。措瓦里的男人们没全来,只来了十个,单独坐一桌。其他的二十几个女人分两桌坐。措瓦里管事的大哥一边喝酒,一边给大家分配座位。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身上已经有很浓的酒气了。我按照借宿那家大哥交代的,给了他一百元“份子钱”。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拎到女人的一桌去坐下。他一边把我按在椅子上,一边冲着我的耳朵嚷嚷:“好好吃,好好喝,今天你们女人家放松放松!”
菜先上到男人那一桌。男人们喝酒喝得厉害,菜却吃得很少。没吃完的菜,就被端到女人们的桌子上来。媳妇们即使在外面吃饭,也还是保持了勤快、持家的女主人性格。菜一端上来,一下子就被利索地分到了每个人的碗里。吃了一会儿,男人们酒劲儿上来了。一位大哥突然站起来唱歌,女人们中间嗓子好的,也跟着唱起来。虽然是在餐厅里,他们仍是放开了嗓子,如在旷野里一般豪放,而且还不忘麦克风。
当有男人起来唱歌的时候,女人们便放下碗筷,举手跟着打拍子。
闹到夜里十一点多,聚会接近尾声。管事的大哥和餐厅老板结了账,让其他几个男人把没喝完的酒水带走,他们一会儿要去县上找个地方继续喝。临走前,大家聚到大厅中间,再载歌载舞了一段才满意地出了门。出门前,管事的大哥忽然跑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怎么样,高兴吧?我们当家的今天凑些钱,就是想让你们女人高兴高兴。”我脸上笑着,但心里却有点别扭。这种感觉,就像前几日在山顶煨桑祭祀时,村落的族长向妇女和小孩儿抛撒糖果和零钱,引得所有女人和孩子们跪在地上哄抢,而男人们在一旁哈哈大笑时我感到的尴尬一样。
也许是因为我的文化背景,我不习惯看到女人被这样对待。记得在一次访谈中,村子里的一个女人告诉我,她丈夫常年在外地画画,平时很少给她打电话。即使打电话,也总是骂她笨,嫌她田里的事干不好或者小孩儿管教得不好。但她马上话锋一转,眼神如孩子一般快乐地说,过年的时候,她丈夫就会从外地带好吃的回来给她和孩子,那时她觉得自己特别幸福。我看着餐厅里挥着手臂跳舞的女人们,很少看到她们这样放松地欢笑。
这种高兴与满足非常真实,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从村里来县上的时候,只开了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小轿车。我借宿那家的大哥二话不说,自己抢先钻进他朋友的小轿车里,和几个男人走了。嫂子赶快拉我去搭面包车,所幸我们挤上了车。这辆准乘8人的车子,最后一共坐了15个人。车子“惨叫着”发动后,开始笨重地前行。我惴惴不安地坐在车里(其实是跪在车里),丝毫没有忘记司机刚才饮酒饮得是那般尽兴,没有忘记超载、无证驾驶、一盏路灯也没有的乡间小路以及汽车本身糟糕的照明……车一边行驶着,我一边紧紧地抓住门把手,同时还要不时地注意周围,避免在颠簸的时候被密密麻麻的手肘和肩头磕到脑袋。
行驶到一半时,车上的女人们突然念起了经。经文十分流畅,如同流水的歌咏一般,绵延不绝地萦绕在耳旁。司机和另外两个男人抽完了手上的香烟,也跟着念了起来。两种声音加在一起,变得浑厚悠远,车子里突然充满了静谧和坚定。这好像一个突如其来的梦境——自己正与朝圣的藏人挤在车子里,在夜色中穿过树林,穿过群山,一直缓缓地驶下去。
我时常会有这样的矛盾:作为女人,我对这里的男人对待女人的态度很不习惯;但我也清楚,这一切对于当地人来说,约定俗成,自然而然。村子里的女人,有着十分隐忍的性格。她们沉默而非无知,她们非常宽容,有着极大的同情心,懂得珍视简单的快乐,这甚至让她们显得很高贵(一个西班牙人到热贡旅行时也曾这样评价)。我知道,我不可能全盘接受村里人对女性的观念,就像我不会苟同一个极端女权主义者一样。我知道,我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他们身上,同样,理解他们的文化并不代表我要改变自己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总是处于两者之间。
(本文摘自《鹿行九野: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林红、刘怡然主编,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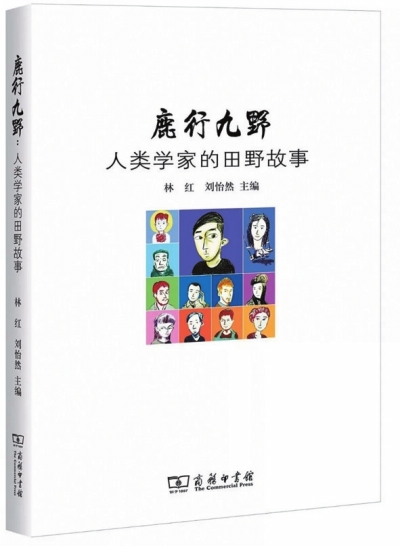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