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访谈
他被国内评论界誉为“山野间的先锋”。
那个沉默寡言的乡村少年,那个在穷困生活中怯弱卑微的农民子弟,在文字中驰骋着想象,驾驭着他构建的一座座王国,为读者所认识,所喜欢,所赞赏。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山东作家王方晨,以对中国乡村历史和乡村政治的勤奋书写,在文坛赢得了令人瞩目的一席之地。
从80年代末初登文坛,王方晨已发表中短篇小说近二百部(篇),共计六百余万字,他的长篇小说“乡土与人”三部曲(《老大》《公敌》《芬芳录》)奠定了他在文坛的60后乡村书写的地位。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老实街》,以城市现代化发展为大背景,抓住传统与现代转化的历史节点,讲述了一道北方老街的倾覆和消亡。每个人的故事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市井民众丰富、复杂的生活形态与情感世界跃然纸上,呈现着鲜明、深刻的本土文化烙印。
中华读书报:在你的作品中,乡村题材和城市题材各有千秋,能谈谈不同的感受吗?
王方晨:我觉得乡土作品更具淳朴的诗意。乡土文学令我情感亲近。另外,农村问题是涉及我的父老乡亲的大问题,我不能视而不顾。相对于农村,城市具备很多优越条件,而随着城乡距离缩小,城市的问题也更为突出。其实我也一直在写城市,比如早期的《豢狗》《笑里沉沦》《猫样年华》,现在的一大批“老济南”系列小说。
中华读书报:在90年代后期,你的创作视野逐渐拓展,如《龙卷风》《响桶》等,“塔镇”也频频出现在你的作品中。这和你本人的生活经历是否密切相关?
王方晨:本来小说多是虚构,很多作家都在回避真实地名,我也这样。小镇子比小村大一些,小村很接近乡野,自然小镇也差不多,我就决定写小镇。我的村子在县城城郊,顺便就把金乡县写成了小镇,县城有座小塔很有名,我就把小镇取名塔镇。后来觉得出现真实地名不可避免,索性就把金乡县点明来写,而且在作品中给县城另辟了地址。
中华读书报:固然不能指望小说家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在阅读作品时,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期待。但是在《乡村案件》《村长的原则》等作品中,更多地呈现了悬而未决的事件,你是有意要把问题留给读者思考吗?
王方晨:现实充满了各种可能,小说里也同样。那年《小说选刊》选载我的《人都是要死的》,编辑建议删掉结尾,他就认为没有必要把结局写清,问题应该留给读者。其实作家写作的倾向性完全渗透进了自己的作品,但如果读者能够得到不同的答案,我倒是求之不得。我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但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引起读者深入的思考。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认为你几乎所有作品中都贯彻着紧张的、不休的对峙,这种对峙不仅在情节的层面上、在人物关系中展开,在最多的情况下还是灵魂的对峙,灵魂在对峙中释放令人惊骇的能量。比如评论家李敬泽也提出你的“危险”,是可能会不由自主地钻牛角尖,在极力往下钻的时候,可能会失去对精神现象的大尺度的把握。你如何理解这样的评价?
王方晨:大概正是这些特点使李敬泽特别注意到了我。他对我的警告,我也记在了心里,因而在创作中时时保持着清醒,非常注意调整。以后的创作表明,我规避了过于追求犀利这种危险,没钻牛角尖,没往窄里去。他说过多次,你怎么变了?还说过,我抓不住你了。去年鲁迅文学院举办我的《老大》研讨会,青年作家陈集益回忆对我作品的阅读感受,说我现在的创作变得“温和开阔”了。是的,年龄大了,已经“狂暴”不起来。我自己也发现非常明显,火气小了。当然本质没变。
我有意识的调整,可能早在2003年。发表在《天涯》的《世界的幽微》里,我写女人鹅最终保有了自己的软弱,但“虽败犹荣”。那篇同属“老实街系列”的《大马士革剃刀》,也没有像《乡村案件》那样,去进行坚决酷烈的灵魂拷问,而是让被害者仁慈地转身而去。《鱼哭了水知道》中的打工青年梢子、巧玲受辱,却继续选择乐观地生活,而且坚持将和事佬送来的钱财退回,都表现出极大的忍耐,从而获得了更广阔的人性宽度。
中华读书报:你离开乡村几年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比较切近乡村的脉搏,你通过什么渠道?
王方晨:要从1983年我考上曲阜师范学校算起,离开乡村已有三十多年了。我们绝不会彻底脱离开农村的,你家人,你同事,路上见到的那些打工的人,小商小贩,周围的每个人都跟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新闻、影视、文学,遍布乡村的信息。那年看到一个民工负尸回乡的报道,我马上想到我要写个小说,我要探讨的,是农民为什么要千里遥迢离开乡村(《巨大灵》)。还有个中篇《暗处之花》也来自新闻报道。一个农村出身的女博士死也不回家看望病危的老母。我感兴趣的,是什么造就她如此绝情。切近乡村的脉搏,只要你愿意,就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另外,就是要保持足够的敏感度。不关心肯定不敏感。只要关心,不管你身处哪里,都会感到自己躺卧在大地的中心。遥遥的一瞥,有时甚至胜过深情的凝视。
中华读书报:你将如何规划自己的写作,还是顺其自然?近年来你以济南为背景创作的小说,特别是“老实街”系列,引起了文坛关注。评论家贺绍俊在评论《大马士革剃刀》时,言其为“炉火纯青”的“艺术精品”。“老实街”系列又是怎样的一个规划?
王方晨:灵感的到来,是不可预见的。有了想法,我会马上记下来,然后按自己所记陆续完成,所以,这让我好像有了写不完的东西。创作原则是有的,大的规划也是有的。
比如说,这些年来,我勉力经营“塔镇”。在我心里,塔镇有一个清晰的地图。但我不能仅写塔镇,自然又有“塔镇之外”,因是写城市,就叫“我们市”系列。我现在济南工作,不能回避济南,渐渐的济南也就清晰起来。我随之写到济南更有特色的老街巷,因为它更像都市里的“村子”。我写济南老街巷,冥冥之中,我的“老实街”就与塔镇的乡村有了精神的呼应。《大马士革剃刀》首写老实街,虽写都市,但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因而有了独特的韵味。读者喜欢,我创作才有动力。所以,不妨在“老实街”多下些工夫,给“老实街”以更生动的形象,在文学中把它鲜明地树立起来,就像做一个品牌。目前我设计的“老实街”系列,是由11个短篇组成,“老实街”系列小说的创作,将让我在现代城市里,重新找到了自己亲切的村子。
中华读书报:11个短篇,每个人的故事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为什么如此结构?
王方晨:最终还是因为老实街的故事适合这种结构。它写了老实街居民的群像,我希望它能呈现出自然的原生态风貌。所以呢,也就适合那种散文化的风格。之前也有先例,好比萧红的《呼兰河传》等。这种结构的好处是,像汪政先生说的那样,可以“反复打开和解剖”,“保持原初丰富而自在的存在”,其实这也体现了生活的复杂性。但它又有主线,也就是一道老街的覆亡。
中华读书报:其中《大马士革剃刀》是影响最大的一篇,在鲁奖评选中也颇受关注。这篇小说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写完之后,你是否也觉得最为满意?
王方晨:对这篇作品我是非常满意的,不光是因为读者的评价,还因为我在写作时分明感到自己进入了一种状态。怎么说呢?极有节制,又有自由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见读者评价小说写得如同行云流水,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吧。这个小说带给了我很多自信,发表后很多人见到我就说这是个“鲁奖”作品,获“鲁奖”无悬念,等等。我只能嘿嘿一笑。但这的确反映了大家的一种认识。还有一种说法我挺在意,是说别看这是个短篇,但它能当长篇看,正说到了我心里,因为我的确是要借此表达出自己宏大的文化意愿。在这种意愿的支持下,我决定写一篇老街巷的故事,写一下我们的文化传统,首先就是《大马士革剃刀》。
中华读书报:有人认为,《老实街》是你创作的一次“转型”,你怎么看?这部作品的出版,在你的创作中有何独特的意义?
王方晨:算是转型吧,但更体现在文风的含蓄内敛上。我看读者评价,这部作品可以视作我三十多年的“创作心得”。我非常认可。它给我创作带来的高度,前所未有。试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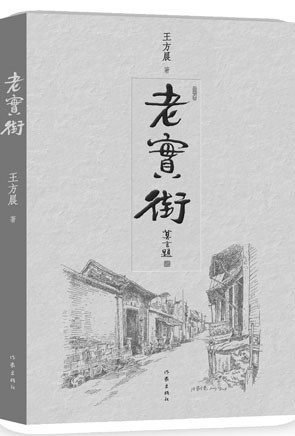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