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调到深圳并成为深圳人,是杨争光事先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
1997年中国电影“华表奖”评奖,杨争光作为评委,把宝贵的一票投给了反映深圳的电影《花季雨季》。后来这部电影获奖,而杨争光也与深圳这座新兴的城市有了某种潜在的关系。
“蓬勃、清爽、充满生气,没现在这么拥堵。特别是那条深南大道,绿草鲜花,宽阔舒展,就像铺展开去的精神和心情。”在《杨争光文字岁月》中,他如此回顾自己1998年初到深圳的印象。年轻的深圳似乎使杨争光获得了新的激情和活力,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少年张冲六章》及《驴队来到奉先畤》等小说作品,创作了电影剧作《杀手》《公羊串门》等,并扶持青年编剧创作了以深圳为背影的电视连续剧《爱是双人舞》《有你真好》等。
“喜欢深圳的生气。喜欢那个时候的深南大道。喜欢它包容的精神,敢于试错的勇气。”杨争光毫不掩饰对深圳的感情,深圳的朋友们使他真切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体温。他说“我可能不会再调动了吧。如果不再调动,深圳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哪年开始写诗的?陕西师大推出您的诗集,是第一次单独出版吗?时间跨度有多久?可否具体谈谈?
杨争光:上世纪中期上大学前。在农村修水库,在山沟里,从沟底的小河里挑水到山沟的半坡,帮厨。有闲暇时间,就写了一首关于小溪的诗,受到了县文化馆老师的鼓励,就继续写。那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竟然写过几百行的长诗。真正开始学习写诗,是1978年上大学以后,写诗,天天写,直到1988年,就是我过去说过的曾经对诗产生过十多年的迷恋。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个诗人。1988年写了最后一组诗《交谈或自言自语》。这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写了这一组诗之后,就在小说和电影剧本写作之间来回折腾,不再写诗。曾经想给自己编辑一本诗集,甚至写了一篇序,但没有编成。到深圳之后,受一位朋友的怂恿,真的编辑了一本诗集,朋友请十位朋友每人写了一篇序,还有朋友给它起了个名字:《一个人的诗和一座城市的文字》,如果真能出版的话,大概会成为一本序文比正文还色彩斑斓的诗集。很遗憾,没有出版。2012年出版文集,其中有一本诗歌卷,因为是文集的组成部分,朋友们写的序文就没有收进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诗集《屋檐水》,是三本书中的一本,是从文集里边的诗歌卷里选出来的一部分,时间跨度十年。这本诗集也没有收进朋友们写的那些序文,是因为有了新的想法。从前年开始,我又恢复写诗了,都在笔记本里,没有公开发表。我想将来再出一本新的诗集,从旧有的和新写的里边挑一些能看得过眼的,自认为有些价值的,再把朋友们写的那些序文收进去,争取不辱没朋友们的文字。即使我的诗没有价值,但对我,至少是友情的典藏。
中华读书报:直到现在,大家谈起您的作品,《老旦是一棵树》《从两个蛋开始》等,还是津津乐道。能谈谈您早期的文学创作吗?经历了哪些阶段?
杨争光: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客串写过短篇小说,写的第一篇,就发表在《山东文学》第一期的头条,也得了奖。但那时候,是想当诗人的,并不热衷小说,虽然没有发表几首诗。后来还写过几个短篇,都发表了,依然是客串。也就因为这几篇小说的发表,有朋友以威逼为鼓励,怂恿我写小说。那时候是1986年,我作为陕西省扶贫工作队的一员,在陕北的一条稍沟里,一口气写了七个短篇小说,就拿着它们参加了那一年《中国》杂志在青岛举办的笔会,记得那一次笔会有许多青年名家,比如徐星,迟子建和后来的格非。《中国》杂志和青岛的《海鸥》分别发表了我的那七篇小说,就有了许多朋友的溢美与鼓励。《人民文学》组织1987年一二期合刊,负责编辑部工作的朱伟向我约稿,努力与期待让我感动。我写了三个短篇,竟然没有辜负他的期待与鼓励。从此,我就多写小说而少写诗了。1988年初,干脆停止了写诗。1980年代文学热,编辑家与作家都有着对写作艺术的激情与真诚,也能够拥有众多的读者。朱伟对我的鼓励,至今让我不能忘怀,也不会忘怀的。他确实是非常厉害的编辑,是那一个时代中国文学的亲历者。前段时间他写了一本书,写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的作家作品与文学事件。他对小说艺术的审美值得信赖,是许多浪得浮名的所谓小说艺术批评的名家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真正懂得小说艺术的像他这样的编辑家,在中国不能说是唯一,说寥若晨星应该不是过头话。由于他的热心鼓励与推荐,我把小说写作坚持了下来,后来就有了《黑风景》《老旦是一棵树》《棺材铺》等等。这个时候,我又开始写电影了。电影剧本的写作给我写作小说,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好处。有朋友担心,写剧本会“坏”了写小说的手,我也担心过,但似乎没有坏。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创作中,影视作品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双旗镇刀客》《五魁》,作为《水浒传》的编剧和《激情燃烧的岁月》总策划,您当年在影视界也是风云人物。可否谈谈这段生活?
杨争光:我肯定不是影视界的风云人物,但确实亲历了上个世纪末十年以及其后许多年中国电影电视的演变历程,也算是一个当事人吧。是当事人,也是局外人。在文学也是这样的,写诗写小说与文学有关,与文学界关系却不是很大,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都是我很敬重的作家。如果要用一句话说我这一段时间的写作生活,我愿意说我是一个把小说和电影电视写作真当一回事来做的散淡人。由于真当回事儿,就会认真,自己较劲,不管是小说写作,还是电影电视剧的写作,都一样的,有汗水也有心血,就和种庄稼的人把种庄稼真当一回事儿一样的,扯不到什么高尚,也扯不到比写作以外任何行业的人更辛苦。
中华读书报:在平衡写剧本、写小说、写诗之间的关系方面,您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小说也好,剧本也好,都得保持诗心,作品才有弹性。这种“弹性”,很难把握吧?
杨争光:说诗心与弹性,可能与我自己写故事有关,不见得就是什么真理。但我确实是比较注意弹性的,不管是一首诗,还是一篇小说,最好能像弹簧一样,具有好的弹性。要获得这种弹性,需要表达的技术,也需要对人物对事件的感受力。更需要立意。立意往往会决定作品的品质,然后才是表达。表达很好,立意不高,或者含混不清,是对才情的浪费。立意与理性判断有关,诗心与表达的弹性有关。
中华读书报:您的小说语言简洁凝炼,这和诗歌训练有关吧?您在语言方面有怎样的追求?
杨争光:也许有关吧。我希望我的作品,诗也罢小说也罢,哪怕是电影剧本,在表达上都能努力做到准确与简洁。准确的表达是首先的。准确的表达,也往往是简洁的表达。学术文章也许只有他这一套表达吧,我不懂。就文学的表达来说,我总觉得我们不如我们的古人,无论是文章还是诗词,精准,简洁,生动,诗意,弹性,白话文以来的作家作品,包括诗人诗作,少有能与我们的古人比肩的。也许,白话文与古文相比,还远未成熟,是我们比不过古人的一个原因吧。还没有成熟,多作践而少建设,在当代的作家作品中睁开眼就能看出,网络写作彻底摧毁了所谓作家诗人们的文坛,对汉语的作践也更甚,有自我作践,也有被迫作践,很悲哀的。
中华读书报:在文学界有一种误解,总认为严肃的作品才是“纯文学”,但是我觉得您的作品很好地融合了故事性、文学性。可否谈谈您的文学观?
杨争光:有人说,只有好的和不好的电影,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和通俗的电影。我基本同意这样的说法。就算存在纯粹和通俗的文学之分,也很正常,不同的作家各有所写,不同的读者各取所需。文学也是一种社会存在,丰富也庞杂,一律纯粹,会把文学纯粹到死的。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也很惨痛的。
中华读书报:2012年《杨争光文集》(海天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您的作品首次全面结集,被称为深圳出版史上的一次标志性大事件。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文集?
杨争光:我当然很感谢海天出版社。我一直不主张出文集的,因为在中国作家中,我实在不算什么。但出一套文集,对自己做一个检视,也许有益于继续的写作,所以也就编辑了这一套文集,竟然还有读者喜欢,听说已经买不到整套的了,这倒让我有一点欣慰,没给海天出版社丢人。
中华读书报:关于深圳,您似乎只写过一部舞剧?您还有意对深圳有继续的书写吗?
杨争光:是的,写过一台舞剧剧本,以深圳的从无到有为原型的,起了一个名字:《关于一座城市的舞蹈》,想法是整台舞剧,利用现代舞台声光电的技术,以国标舞为主要表现手段,兼容现代舞与街舞,拒绝芭蕾舞。当时主要的想法就是这个,写得也很顺利,也通过市文联在协会申请了文化基金,但后来听说,排演的不是我写的这个。我当然希望我能写和深圳有关的东西,也有过准备,但至今没有写。原因大约是,这座城市的光鲜与靓丽,睁眼就可以看见。但何以光鲜,何以靓丽?原因会多过满城的勒杜鹃,证据及其说服力也如莲花山和西丽湖一样确实。但这就是这座城市,从起始到庞大,从小水洼到音乐厅,从荒地到中心书城的全部真相么?与光鲜和靓丽相杂糅的,也有汗水与血泪,有牺牲,有戕害,有掠夺,其强悍与掠夺,是否残酷到丧失人性?其证据说服力是否也和它光鲜亮丽的证据说服力一样多,一样确实?人类建造城市,应该是要让人类有更好的生存,更美好的人性。文明的路径上,生长的不仅仅是光鲜与靓丽,应该也掩蔽着血腥与罪恶。如果我要写它,我该怎么写呢?我不知道。一座城市首先是一个人性的世界,人性的世界不会是单一存在。至今没有写,首先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对自己的审视与掂量,能不能书写?有没有足够的智慧?还是干脆承认了吧,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没有书写它的勇气和自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热爱这个城市,也许更意味着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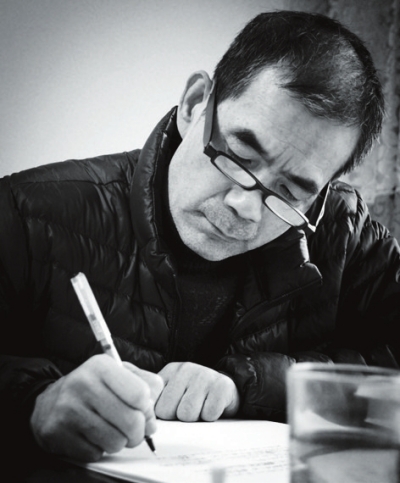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