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是一位抒情诗人。他在每首诗中都不断地提醒读者,一首诗是诗歌与诗意的空间,而非消息的传达者。因此,诗中包含的信息应始终是有旋律的,并需要词汇以旋律的方式获得聆听。当诗人们尚因不懂吟唱而限于叙述时,吉狄马加已开始歌咏,仿佛知道诗歌只能是这样:心旌摇曳时思想的乐音。吉狄马加想呈现的音效在哪里,他的箭就射向哪里。我们可以将吉狄马加归入以听觉为创作核心的现代诗歌潮流,在听觉的疆域里,“诗意”通过表达方式、声音的“意见”以及一种为了使自己被理解而开口讲话的音乐,扮演了为诗歌启幕的角色。
吉狄马加在他的诗歌中,将新颖或传统的旋律元素变化交织,避免了某种固化的、既定的东西赋诗歌以特权,施诗歌以限制。语言的这些细微举动分散了细节,挑战传统的所谓透视顺序、元诗、元叙事,以及将词语置于有规律的重复结构中的语言游戏;时而加速,时而骤停,周而复始。在吉狄马加的诗中,发声是为了被听见。历史声如洪钟;存在是听觉上的实在。
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有一种与“发现”相似的东西,这种发现胜过一切作品的开端,使一种根植于古老传统中的全新创作成为可能。诗歌的圆满成就于被旋律决定的那一刻,任由词汇去叙说,在适合独白之处独白:一个尚无语言涉足的地方。当词语在聆听中达到了目的,它们便存在。词语说话,动物也说;诗人将自己的主观如数奉上。无论是短诗或长诗,语言扩展着从独特视角去感知的可能性,使得某种目光有可能进入创作活动,保护这种目光的,是不依赖探测仪的、在最初的蓝图里并没有被考虑过的发现。
读者能感受到一种非凡的、极致的想象力近在咫尺,它的声音从常被忽略的不安与摸索中被硬生生地拔出,在响起的那一刻便成为一种确认:读者可以与这些诗歌建立联系,通过它赋予理解以更大的重要性。在1970年4月6日写给伊莲娜·希姆梅利(IlanaShmueli)的信中,保罗·策兰(PaulCelan)写道:“当我阅读我的诗歌,它们给予我短暂的生存可能,永存可能。”在吉狄马加的诗中,语言有了成为最即时模板的可能性,同时通报一种并不苛刻的措词的消息,这种措词与语言的本质对话,却不指明:唯其如此,它才得以表达。这样,诗歌担起了它基本的、毫不简单的使命:建造一种需要,通过它的内在密码与加密效能使这种需要得以存在;不对称、频繁、犹豫都在这种效能中交汇,但同样掺杂其中的,还有对于一种声音的需求,这种声音须得为了在被听到的同时听到自己而吟唱旋律。
这些诗歌的语言属于现在,它熟悉与可言说性相联系的感官,而这种可言说性是在思维准备好思考目光的一举一动时,从思维中生发的。诗歌(有萨满的声音)闯入了一个舞台,台上正被夹在实证与抽象间的视觉以间歇但连贯的方式粉墨登场,这种与理性冲突的行为先是佯装,再是遮掩。而目光,由于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变成了“表演者”(performer),在观看周遭的同时观看自己,它希望自己是被如此看待的(当它被看见的时候):它的愿望如同向心力般装饰了它的影响可及之地,而它在愿望的透明镜子里自我阅读。
从有着独特断句的口语化风格,以及紧接在混沌现实之后主观的曲折前行出发,目光在语法的偏航里,在实证对想象的不断皈依里观察着,比起描述不完整且坚决的事物的必要性,想尽可能地存在于“真实”的愿望对这种皈依具有更强的干扰:“我却能从不同的地方/远远地眺望到/那些星罗棋布的庄廓”(《圣地和乐土》)。
目光,作为世界聚合物的一部分,取得了优先地位。对事物的认知以及对一种非常规语言的运用,都由于目光,这一所有现象与被确认现实的源泉,而得以存在:“常常有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呆望着天空/而心灵却充盈着无限的自由”(《无题》);以及“谁看见过天堂的颜色?/这就是我看见的天堂的颜色!”(《雪的反光和天堂的颜色》)。但是,与如今在各种语言里都很常见的以色彩入诗的作品不同,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他的目光通过视角独特的虚构,集中在特定的事物上,而非出于对特定情感的身份直喻,这些情感最终都免不了雷同,与之相伴的,是一种对想见之物一无所知的观察方式,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如何表现它们了。
不同于所有对自己的行为方式的封圣,在吉狄马加的诗中,目光具有装饰的意义,同时也是私密性——目光的解体——诞生并退后的地方:为了观察,为了发现曾经未见的东西。观看即是言语,是予词汇以视力:“我说我的祖国的历史,是一部/完整的历史,那是因为我把这一切/都看成是我的祖国”(《致祖国》)。当看见并谈论所见之物时,目光执著地对自己叩问,问是否渴望知道所见之物,它质疑自己的行为,而它的媒介作用产生了不同的阅读,将事实变成次生现象。
这种包含着内在冲突的语言模式与单调性、可预见性背道而驰,主动的目光将语言从它所处的舒适区中拉扯出来,迫使它对诗歌逐词逐音节地阅读,诗歌就该被这样阅读,尤其是这样有旋律的,向读者承诺了震动、惊奇与回味的诗歌。这意味着需要不断对诠释过程中的飞跃进行阅读,以免诗句沦为其它诗句的翻版。与生活本身一样,目光的对象也在不停地改变着,因此,它在每首诗中,在未尽之言中,都加入了一些并不简单的偏差,对其它的成分造成影响。当目光自动转变为它本身的语境,它便作为文本的序言而出现,是针对新事物——一种从未有过之物——正在成熟的最初视角。诗歌是充满掠夺的森森丛林;是认知,但也是对于它本身出发点的确认:“我的灵魂,曾到过无数的地方/我看见他们,已经把这个地球——/糟蹋得失去了模样,而人类的非理性/迷途难返,现在还处于疯狂!”(《而我——又怎能不回到这里!》)
作为朦胧目光的终端,远远望去,吉狄马加的诗仿佛正在成型的框架,记录了正不断伸展到当下的过去,因为唯有如此,新事物才能永远崭新:不知如何,不知为何,并且绝不沉溺于书页间的唯我主义。每首诗都与其它诗相连,这种牢不可破的结合,作为吉狄马加诗歌的特征——由一种声音连缀在一起——赋予了他的诗歌一种所谓“追寻的魔力”。读者受邀继续用已有的目光观察,并看见诗人以文字记录下的东西。在摄人心魄的诗句里,潜藏着澎湃河流般的节奏,裹挟着读者,涌向一种并不回避目的论的语言,在至高点扎下阅读之根。这样的结果不可忽视,无从掩藏:诗歌成为诗学,或者说,诗学造就了诞生时就带着相似烙印的诗歌,那是一个集体的身份。因此,在改变对现实的接收方式时,我们目睹了一系列场景、沉默与精神状态令人惊叹的延续,它们集合在一起,成为被拯救出现实的“诗的时刻”。
吉狄马加的诗歌是多声部的创作,正如作品中所突出的那样,它们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整体。它们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十分清楚自己想讲些什么、如何去讲),每当其内部的更迭得到外化,这些作品便更新自己的源泉。在朝着流动命运的迁徙中,诗歌留下的足迹与那些早已被预见并且已被收进某部作品中的足迹重合,这部作品在每一组成部分的独特性中(它并不处于这些部分中,也不在它们之外),在朝着不同方向、以不同形式伸展的口头协定里,成就了自己。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除了对中国历史顺理成章的总结,最明显的便是一种由词语自发创造的语言节奏,透过这些词语,可以对世界展开超越时间的诠释与思考。这种语言在冲突中,将自己经过了想象核验的记忆注入传统。每一首诗都将读者引向由语言的措词与意识带来的节奏的核心区域,这是语言得以表达的唯一途径。
为了突出其活动的持续性,无论是在这本书的诗中,还是在其它诗集里,吉狄马加都常常使用与用双眼认识事物有关的动词:观察,眺望,注视,静观,看见,凝视,而为了描写一种“半看”的状态,即似看非看的眼神:微闭。目光牵引着诗学,触摸它,刮蹭它,周而复始,永不停止。这是一种不断在新事物里自我更新的方法。它要求诗歌根据以它为中轴、为路口的不断变化的情势与引力,为句法的特质划定准则。所言之物必须以无法复制的方式被言说。为此,语言不再依赖于它本应该说的内容,而去关注藏在仍未部分或完全成形的东西之后的,究竟是什么。写作,这一在眼神消解前,使其中的征兆现形的劳动,提出要对某种被鼓励,甚至被强调到极限的不可能性保持警惕。这样的话,当语言进入了回声之隧道,每个句子都会发现自己是非语言的原创者,认识到自己在遗迹中的可变地位。
显然,无后果的模拟行为,其危机状态扩大了象征性语言的不必要边界,使得语言,一旦不再需要包藏含义,一旦被野化,则变成不可模仿的事实,状态取决于其厚度,回音取决于目光在语法上的最初声音。诗句立足于没有目的地的流徙,短暂而犹疑,这并非没有意义:“灰色是如此的遥远/看不见鸽子,天空没有飞的欲望”(《重新诞生的莱茵河》);“只有群山才是永久的灵床”(《巨石上的痕迹》)。为了强调犹疑的情绪,在尚能眺望之处,本会使诗句更为迟回的停顿被省略了。语言与它的动机同样迅速,失去了确切的方向(因为目光也没有方向),语言在死胡同里踩下油门。后视镜里的风景向前移动。
吉狄马加的诗是所有感官中的冷漠物种,像约翰·凯奇(JohnCage)的音乐,承载着沉默的状态,因为此处,沉默是预言之声,预言从目光里获取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的晨曦。诗句通常很短,几乎快要消失,停顿呼之欲出,表现出一种思想即将洞察的安静瞬间,因为它们会在最沉默的时候对一门有关克制的学问的持续行为进行描述。这一叩问欲望的复杂方法的意义并非显而易见,因为它只是为了在同期事件令人迷惑的焦虑中自我展示,在这些事件中,存在着大量的歧义,而如何消减掉它们,无从得知。
因此,诗歌是超凡的,诗行间的果敢一字千面,将诗中谜团的暂时胜利神秘化。这一点的基础是——它也由此深化——回顾中预感的悖论,这一悖论认可自己的反射与意义的有效性,即使它们属于一种尚未得到验证的语言。不属于现在的东西,诗歌都把它们留给以后。它使表达方式周期化,这种表达是与那些明显的但又常被忽视的东西调和的。当欲望变成了问题,诗歌就成为了知识,充分显示出内在的崎岖。这让吉狄马加融入中国善于幻想的伟大诗人们的传统,他们不畏凝视,也就不惧怕目光会在视野之外幻化出情景。
诗歌让它的不同源泉彼此对立。正是通过那种与其本质对抗的力量,语言才得以自我批评,成为由概念构成的短歌故事,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叙述不存在故事的目光的概念,当诗歌在最紧要的关头,对暗示的废墟进行预言时,这种目光同时也是一种衰败的可能。这样的诗歌,正如诸多诗作所突出的那样,面对完成认知行为的无能为力,是知识上的不安之诗。写诗是为了了解尚不被了解的,因为懵懂无知的诗歌致力于最动人的惊异,使它免于堕入服务于单一目的的简单定义。
诗歌会回到自己一连串脚印的起点,它具有自指性,不让期望成形、变形或化为虚空,而是对期望进行剪辑,赋予某些以视觉或其他形式证实了真相的镜头以特权。诗歌存在的地方,或计划抵达的地方,是多样的。吞吐在闪光,话已说出,但最好沉默;这正是这些诗歌主要的成就之一。语言从不提醒“我去那儿了”,而是突然改变路线,换掉了出发时定下的目的地。它与欲望本身一样,在所有方向上都自得其乐而游刃有余,这是一种只能在影射中,在受策略限制的氛围中被发现的乐趣,这些策略一旦被重复,便造出一种眩晕,是了解它自己的又一种方法:“你曾看见过垂直的天空上/阿什拉则金黄的铜铃/那自然的法则,灼烫的词根/只有群山才是永久的灵床”(《巨石上的痕迹》)
吉狄马加的诗希望以一己之力动摇已有的积欠,使它们成为某种声音的宠儿,乍听之下,便知这声音曾幻化的无数面目。与这一诗学的发现毗邻而居的,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先锋派,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这样的诗歌,在语调的审慎改变后,保留下完整的面貌,这也是对所见事物保持警惕的方法之一:“但那扇大门,看见了吧/却始终开着”(《拉姆措湖的反光》)。因此,思考以一种似乎别无选择的痉挛方式进行着,忍受着某些几乎无可避免的听觉表象的牵扯,在那些表象里,欲望根据自己的声学,以一种词语自行建立的节奏演变着,此外,一种预言感,一种先于韵律成形的人造性也为诗歌增光添彩。从不会有对真实的确认。诗的效果是时间里遥远的影像,却可以持续到它不断的外在发生行将落幕时,与惯例相距甚远。
所有的新都会消失在更为崭新的事物中,保罗·瓦雷里(PaulValery)如是说。在吉狄马加的诗中,那种富有原创性的幻想,是目光在感到自己正在看“似乎”是初见的东西时,获得滋养的源泉,它又反过来从激荡的、使语法自我揶揄的多声部旋律中汲取养分,因为这样,幻想得以迁移,这首先让被诗人献祭的东西神秘化,并以此形象长存——如果存在目的的话,这便是主要的目的,属于对看见并认识的渴望——这样,它的永续性也得以保证,它自然的焦虑状态:避免开口,以防有人彻底禁止它发声。
在诗歌的活动中,过去与现在同时进行,在它颤动着的非时间性中,诗歌将日期不明的联合视为己任,这些联合延伸了思考的边界,直到极限,正如吉狄马加在《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谈》这篇具有自传色彩的早期作品中所写的:“我写诗,是因为我无法解释自己”;“我写诗,是因为对人类的理解不是一句空洞无物的话”;“我写诗,是因为我在意大利的罗马,看见一个人的眼里充满了绝望,于是我相信人在这个世界的痛苦并没有什么两样”。
属于现在的短暂确定性——如果说存在确定性的话——已被所有由来已久的东西摧毁,也就是对确定性的更不明显的幻想,它攫取了一切。而为了得以存在于时间内外,诗歌将紊乱作为核心目标来执行,或者说,通过紊乱,诗歌得以远离显而易见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避免它们,而是让它们不要与特定观点太过相似。在时间与目光间构建的空间难以辨认,但是无法躲闪。《史诗和人》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首诗在确实可见与似乎可见之间流逝;认知受制于我们能看见的东西以及那些一旦被看见,就产生出一种极富诱惑性的认知的东西;目光是一种有待确认的确定性的原则,想象是它的决定性力量,拥有明显的确定性,在创造力方面甚至高于记忆:“不是词在构筑第四个空间/仍然是想象,在他干枯的眼底/浮现出一片黄金般的沙漠”(《盲人》)。
诗人写作,随后观察,接着思考。正是在剧烈语言的洞穴中,言语将它的唯我论演变成一种确凿的神学,追随它,与它对话。没有一种感觉是自相矛盾或与语言冲突的,一旦它处于困境,就释放出边缘的理性,为了扩展现实中的场景而去接近它们,因为“不可言说”的持续性便是建造这种诗学及其特有的郑重决定的唯一方法。这些想法属于一切,除去那类似现实的东西,或者说生活本身(从不存在生活本身),除去那些同为声响,同为决定,同为习得之无知的东西,什么都不必一致。
不必以某物作结,或以一切作结,因为在这里,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对保罗·瓦雷里的作品的评价中所说,想法“如岛屿浮现于声之海洋”,诗歌发声,在被一种反省写作所承认的空间里,其声音强调着一种割裂时间的渴望,通过反省写作实现某些只有在按其本性行事时才会依靠句法的使命。在这一点上,诗歌遵守严格的要求,即成为一种“完全”的“智力”,它与自身内容沟通的方式堪称典范。通过一项有条理的工作,诗歌建立起一种内在位置的认识论,这些位置在真实的外部找到了自己的实质。诗歌是一种尚处于观察期的信念的证据,是目前以及将临之物的证据:“我总是靠近死亡,但也凝视未来”(《我,雪豹……》)。
作为对并未被要求的目光与思考的(再)认识,吉狄马加的诗歌不再对自发性负有义务。它兀自存在着,以承担起自身特质的同时性,这些特质被公认代表了一种永不休止的开始,一场目的地未定的旅行,与对可决定的目标作出回应的必要性无涉。诗歌是过程,如此地朝着一种尚在被孕育的架构运行,直到成为——或似乎成为——一种甚至领先于欲言之物的精确系统。结果显而易见,再明确不过。在时间中,目光随心所欲——它的阿多尼斯之声——成为了结果,又因此成为自身的解决方法,因此诗歌的效果——它的效力——也来自于它的明确与精准。
吉狄马加出生于四川省西部大凉山山区,其家族在当地享有声望。他是当代中国最具原创性及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文化活动家。他曾在中国各地组织举办国际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将当代世界的诗歌带到他的祖国最偏远的边境。
吉狄马加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4岁时,吉狄马加便获得了国家级的最高荣誉,这在同龄的作家中是很少见的。他很快成为受到国内外认可的作家。
吉狄马加的作品具有极强的抒情性与极高的精神高度,他曾出版四十余部诗集、散文集,作品被翻译成二十余种语言。这不仅使吉狄马加成为彝族乃至中国所有民族的文化象征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还使他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中享有国际声誉的重要诗人之一。
(爱德华多·埃斯皮纳,当代拉丁美洲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诗人之一,本文是他为其翻译并在古巴出版的吉狄马加诗歌《我,雪豹——吉狄马加诗选》西语版所作序言)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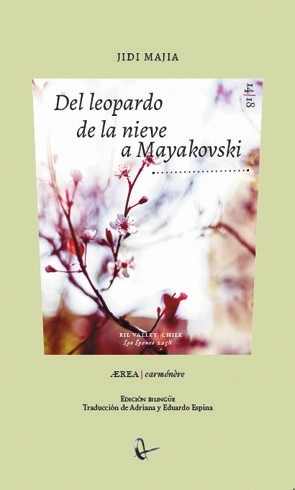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