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至1885年间的中法战争长期以清政府“不败而败”的形象示人。这场战争切断了清越之间的传统宗藩关系,加剧了清帝国西南边疆危机。清廷对法政策在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不同派系的权力之争引发甲申易枢,对晚清枢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不过,与近二十多年学界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领域取得的突破相比,中法战争研究声光暗淡。就史料积累方面而言,除当事人的奏折、公牍和年谱外,前辈学人编纂整理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中法越南交涉档》《中法战争文献汇编》和《中国海关和中法战争》等资料集对推动相关研究,皆有一时之功。除此之外,法文史料的价值自不待言。邵循正先生1935年出版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就因广泛援引法国外交文书而被奉为中法战争研究的经典之作。台湾学者龙章同样参阅了大批法文史料写成的《越南与中法战争》一书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过,目前已有资料集以中文史料为主,多从清政府的视角展现中法冲突的酝酿与演变。法国本土档案馆馆藏资料的整理、翻译和利用严重滞后,制约了中法战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1999年至2006年,张振鹍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三、四、五册开始辑入法国外交部和海军部档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法战争研究中法文史料的不足。时隔十一年,中华书局于2017年出版了最新一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六册(以下简称《中法战争续编》[六]),为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有利于研究者从法方的视角考察中法战争相关史事。
《中法战争续编》(六)以时间为序,收录了法国海军部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共831件,时间跨度从1884年5月1日至12月31日。军事类档案包括法军在越南东京、福建马尾、台湾基隆和淡水的作战报告、兵力配备、物资补给等情况。外交类档案包括法方代表与李鸿章、曾国荃的谈判经过、法国众议院的相关决议、法国政府对美英两国调停活动的反应、中国沿海和内地省份的反教活动等。编译者采取原文照录的方式,对已刊《中法战争》中省略过多、零碎不全的部分史料进行补全。除此之外,本书中绝大部分资料均系首次披露。这批珍贵史料不仅有助于学界对中法战争期间诸多问题的考辩,而且能够从中探索新的论域,试举几例如下。
一、《李福协定》签字后的“撤兵节略”问题
1880年之前中法围绕越南控制权的争夺便已现端倪。学界一般以1883年12月14日法军进攻屯驻越南北部山西地区的清军和黑旗军作为中法战争的开端,以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和李鸿章于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草拟《李福协定》(亦称《中法天津简明条约》)作为战争第一阶段结束的标志。《李福协定》签署后,由于中法对撤军时间的理解不同,双方在越南北圻观音桥一带爆发军事冲突,中法谈判失败,战端再起。因此《李福协定》及其背后中法之间的分歧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李福协定》第五款法文本规定,自签字之日起,“三个月内”双方各派全权大臣详定正式条约,商定通商、划界和撤军事宜。而中文本将“三个月内”误译为“三个月后”。1884年6月,法军试图接管谅山地区的清军阵地时,双方在观音桥发生激战,法军强攻无果。事后双方均指责对方破坏《李福协定》。法方强调,签字完毕时,福禄诺曾交给李鸿章一纸“撤兵节略”,规定6月6日法军开始接管清军控制下的谅山、高平等地,清军最迟应于6月26日前撤回广西。李鸿章当时并未反对。总理衙门就此事质询李鸿章,李鸿章坚称未曾应允所谓的“撤兵节略”。总理衙门也表示《李福协定》并无附件,撤军问题本应在中法双方签订正式条约之时才能确定。至此,中法双方关系破裂,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尽管总理衙门在观音桥之战后承认《李福协定》中文本存在误译,但是“撤兵节略”仍是中法战争期间的一则悬案。论者或认为法人诡诈蛮横蓄意制造事端,或指出李鸿章畏惧言官弹劾隐瞒节略不报。近年有研究者提及一则直接证据,即1921年福禄诺在法国某杂志(Revue Des DeuxMondes)上刊出的一则回忆,自称节略上原已注明撤军日期,只不过交给李鸿章之时,被他本人用铅笔涂抹。巧合的是,2017年第4期《近代史研究》刊发张振鹍先生的一篇札记《福禄诺节略与中法战争两个阶段的转变——从〈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说起》,考订节略风波系李鸿章将撤兵日期涂抹,反诬是福禄诺所为,并有意向《泰晤士报》记者透露此事,以制造舆论逃避责任。关于节略被篡改一事已有截然对立的观点。《中法战争续编》(六)收录几则披露了“撤兵节略”细节的新史料值得关注。
《李福协定》仅规定清政府“立即”(中文本译为“即行”)从越南北部撤军,但并未开列具体时间表。值得注意的是,5月11日中法代表签署《李福协定》之前,福禄诺致海军和外交部的电文中从未提及“撤兵节略”之事,也未曾提及在《李福协定》之外另拟“撤兵节略”的谈判策略。直到5月18日,福禄诺才首次在致海军及殖民地部长的电文中提到他于5月17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撤军节略”,并附上全部内容(参见第59页)。具体情景存在两个版本。其一,在6月1日致海军及殖民地部长裴龙的电报中,福禄诺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与李鸿章之间的对话。李鸿章不同意“撤兵节略”,认为其中规定的撤兵期限太短,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有伤朝廷体面。而福禄诺自称未作让步,最后“李鸿章向我肯定他保证把命令传达下去”(参见第137页)。其二,中法重燃战火后,在7月21日致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乐的信中,福禄诺回忆中法交涉退兵一事的更多细节。双方对话如下:“‘这么说,阁下接受了我在公函中确定的日期,并由您承担责任,负责以适当的办法使北京同意在这些期限内把中国军队撤退完毕啰?’‘是的。’总督坚定地答道”(参见第343页)。对话结束后,福禄诺故意通过天津电报局以明码的方式将此信息发给法国海军的米乐将军,“一刻钟之后,李鸿章就拿到这一电报,亲眼证实该电报与我交给他的那份公函的内容完全相符”(参见第343页)。上述内容皆与1921年福禄诺的回忆存在不小的出入,个中细节需要与其他资料作进一步比勘。如果1921年的回忆为真,那么福禄诺事后提交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为何隐瞒涂改日期一事?从福禄诺发给茹费理的电报来看,福禄诺并非好战派,而且对顺利签署《李福协定》结束战争颇为得意,他的种种邀功之举甚至引来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的嫉妒。目前尚无法看出福禄诺破坏中法和谈究竟能给他自身带来何种益处。如果福禄诺1921年的回忆不实,那么李鸿章为何在签署《李福协定》之后,先接受“撤兵节略”,以致中法矛盾不可收拾,遂又制造和散布福禄诺涂抹节略一事为自己开脱?有研究者提到,李鸿章一则无权命令驻越清军后撤,只得私下向前线淮军旧部暗示准备撤退,二则不敢上奏清廷降旨撤兵,因为清政府刚刚下令军队“扼扎原处”。不过,此说未触及李鸿章欺上瞒下的真正顾虑。因此仍有必要继续检讨李鸿章在中法谈判中的责任问题,尤其是甲申易枢前后清廷的权力格局对李鸿章外交决策的不同影响。
此外,中法谈判过程中的翻译问题也值得关注。福禄诺递交撤兵节略时在场的人物除他本人外,只有李鸿章、李的法语翻译马建忠和李的英文秘书罗丰禄(参见第1019页《巴德诺致茹费理》)。其中,马建忠的翻译水平不宜高估。例如福禄诺和李鸿章起草《李福协定》时,二人的交流依赖马建忠居间翻译,福禄诺当时认为,“马建忠先生精通我们的语言,但讲得并不准确”(参见第109页)。《李福协定》中文本将“三个月内”误译为“三个月后”已属大错,折射出清廷法语翻译人才的匮乏。所以,福禄诺递交节略之时,口译的准确性是否影响了李鸿章的判断,则是另一则悬案。
二、孤拔舰队的军事行动
法国认为李鸿章背信弃义,清政府违背节略,应为观音桥之战负责。法方要求清政府不仅执行《李福协定》及其节略,并赔偿法军军费和相应战争损失。总理衙门则表示拒绝赔款,并将观音桥之战归咎于法方。于是法方展开报复行动。为迫使清政府就范,法国海军拟占领港口为质,此后便有了法军攻陷基隆,甚至短暂封锁台湾岛之举。那么法军为何选取基隆作为目标?在法军海上作战计划中具有怎样的意义?近年随着科技史和军事史研究者的加入,晚清中外战争中的兵力、军事技术和战术受到更多关注,在传统外交史研究之外,为探讨中外交涉中的各方决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既有研究多认为法军觊觎基隆港口的自然条件和周边丰富的煤炭资源,视之为优良的军港和燃料补给站。《中法战争续编》(六)收录孤拔与法国外交部、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之间的大量通信,还原了法国海军行动背后的考量,有别于一般认知。1884年5月28日,法方从北京公使团处获悉《李福协定》可能无效时,便制定了“占领基隆煤矿和台湾北部”作为抵押品的对策(参见第96页)。没有选取福州、广州和上海的原因,主要考虑到这些口岸外侨较多,一旦开战难免引发列强干涉(参见第339页)。7月13日,茹费理令孤拔舰队攻占基隆作为抵押品,表示“我们不打算在李鸿章管辖下的渤海湾攫取抵押品”(参见第291页),反映了法国政府仍然对李鸿章出面主持和谈抱有幻想。不过,由于清廷枢臣更替,加之总理衙门追究李鸿章在《李福协定》及其节略中的责任,李鸿章已经无力左右谈判的进程。从1884年8月直至12月,中法之间打打停停,双方代表在上海、天津两地频繁接触,以期达成新的协议。此期间孤拔反复要求北上。他数次向茹费理展示他的作战计划,即首先占领芝罘(今属烟台),作为北进的基地,进而占领威海卫和旅顺港,最终达到封锁渤海湾的目的。撤兵节略风波之后,清政府委任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荃在上海负责对法谈判。李鸿章在天津多次和法国领事接触,试探取消战争赔款的可能性,但都无功而返。从现有通信来看,孤拔对清廷权力变动和李鸿章的处境并无清晰的了解,将清政府拒绝赔款而又拖延谈判视作为战备争取时间,故而一方面不断要求法国政府增兵,另一方面搜集渤海湾的情报,甚至提出水陆并进攻占旅顺的计划。孤拔的方案还得到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的鼎力支持,两人频繁向法国外交部、海军及殖民地部索要军事援助。孤拔舰队北进计划最终流产,其外部原因在于,一方面法国政府将主力军队置于越南,无力支援孤拔舰队;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并未试图扩大海战的规模,茹费理和海军及殖民地部不断勒令孤拔不得开展登陆作战,军事行动应仅限于基隆港附近。至于舰队内部原因,首先,孤拔舰队占领基隆港后发现,基隆港港口狭窄,难以停泊大型军舰,并非预想中的良港;其次,清军在撤退前捣毁基隆煤矿坑道,恢复生产实属不易。而且该矿煤质低劣,无法满足海军的需要。法国海军不得不依赖香港、新加坡和长崎的煤炭供应,补给线被迫拉长,限制了法军的行动。随着法国海军封锁台湾岛期间扣押英国船只引发的法英外交纠纷,香港和新加坡的煤炭供应随时都有中断的风险,这也为法军北进增加了不确定性。最后,法国海军士兵占领基隆后出现水土不服、伤寒和霍乱,非战斗减员增加,孤拔的北进显得力不从心。北进计划未能实现,客观上缓解了清政府在海上的军事压力和被动局面。孤拔攻占基隆期间,清军加强了威海卫和旅顺的防御力量,并不断用悬挂英美国旗的船只运送士兵和物资支援台湾守军。孤拔进退失据,多次向政府抱怨,若早日执行封锁渤海湾的计划,清政府恐怕早已就范。由于中法双方在战争中后期都执行以战求和的策略,因此,双方的军事决策与战场胜败直接影响和谈的走向。本册中所收录的法国海军档案无疑为研究中法停战谈判提供了关键的背景信息。
三、列强对中法战争的态度
学界对中法战争时期的国际局势已有所关注,如德国政府纵容法国侵略越南以期转移普法战争后法国国内的复仇情绪,又如曾纪泽游说英国参与调停、美国公使杨约翰在北京和天津的斡旋、日法联合夹击清政府的密谋等,但仍有未尽之意。《李福协定》签署前夕,英国公使巴夏礼正忙于交涉朝鲜事务,闻言中法即将停战缔约,匆忙从朝鲜回到北京。福禄诺认为,英国人乐于看到法国人深陷东亚海战的泥潭,以便“钳制我们在马达加斯加和埃及的行动”(参见第120页)。法方拒绝美国公使杨约翰的调停方案,也与美国谋求在华利益偏袒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不无关系(参见第391、405页)。彼时正值殖民主义狂飙的时代,远在东亚的中法之战并非一起孤立的地区冲突。列强各有所图,它们对中法冲突的关注超越了维护在华利益的基本诉求,而是杂糅了国际战略考量。福禄诺在签订《李福协定》后,邀请各国驻天津领事共进晚餐宣布此事。他在报告中写到,受邀的客人听闻中法秘密缔结了一个外交协议,既感到吃惊又难掩懊恼和悔恨,“因为他们这样被人玩弄却又被邀请来庆祝法国和中国瞒着他们突然达成的和解,而他们本来要不择手段加以阻挠的”(参见第131页)。已有论者指出,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之后,列强一致侵华的局面不复存在,彼此间的冲突往往大于合作。本册中的各类报告和通信显示,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欧洲列强对巴尔干半岛的争夺,逐渐催生以法俄同盟和德奥同盟为代表的不同阵营,列强间的合作与竞争延伸到了东亚地区。德国政府极力鼓动法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并未料想中法战争会草草结束。1884年中法在天津商定《李福协定》之时,德国公使巴兰德往来于京津之间,福禄诺担心德国人在策划什么阴谋,因为这位公使自中法开战以来便是“协助中国政府制定反对我们的政策的主谋”(参见第120、218页)。1884年8月26日清政府对法宣战后,法国委托俄国领事代管各地的法国商人和传教士。俄国驻烟台副领事法格圣不断向孤拔舰队提供旅顺港的地形、炮位、兵力、德国教官、舰船吨位等信息(参见第624、628—633、979—980页),助长了法国海军北进的信心。《李福协定》签订后,福禄诺提交多份报告描述战争期间各方驻华代表的反应,虽不乏向茹费理邀功的意图,但从近年来不断升温的全球史观出发,欧洲列强的国际关系网络,实则构成影响中法战与和的因素。中法战争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有赖于研究者对多语种史料的解读。此外,尤其不应忽视的是,中法战争是19世纪70年代越法冲突的延续,已有中法战争史的相关著述中,越南虽是最重要的相关第三方,却始终处于失语的状态。除《大南实录》《往津日记》和部分燕行录外,研究者如能挖掘更多越南官方档案,则可一窥越南政府在1880年前后对宗藩体制的期待和对西方条约体制的迎拒。越南一方如何衡量自身利益,在中法之间周旋取舍,不仅有助于还原中法战争在酝酿阶段的诸多史实,更可从藩属国的视角揭示近代以清帝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制所面临的西方挑战和内部困境。
《中法战争续编》(六)共两册近1200页之巨,上述浮光掠影式的描述尚不足以凸显它对沉寂多时的中法战争史研究的史料价值。需要指出,中法战争资料续编原定共七册,第七册内容拟包含1885年1月至6月9日中法和约签订期间的法文档案资料,以及从越南、英、美等国档案中选取有关中法战争的资料。从本书编译者的后记来看,由于出版计划的变更,第七册被取消,实为学界憾事,同时也昭示了仍有大量外文资料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不失为后来者汲取灵感的来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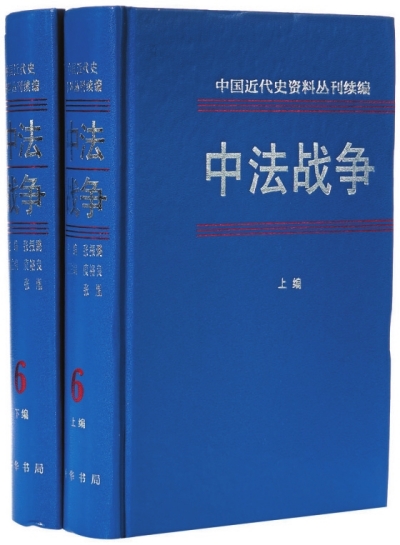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