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99年10月到威海参加李文放女士召集的复建秦刻石论证会上,头一次见到赵平安教授的,那时他还只有三十多岁,却已经是教授了。记得当时他签名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说文〉小篆研究》,拜读之后,受益匪浅。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后来见面的机会不多。只是他调到清华大学工作后,我不时到清华参加学术活动,见面次数才多了一些。
这次他要出一个自选集,竟找我要写一个序。其实,我虽因个人经历,先钻研东北考古和历史,又攻读甲骨金文,由甲骨金文而又从事古史研究,后来因工作需要又时而搞考古,时而搞古文字,杂七杂八,面铺得挺广。然而赵平安教授最初出版的专著都着重在汉代的隶书和小篆,后来研究的又集中在战国的简帛,都非我所长。只是赵教授盛情难却,又正好有机会集中拜读赵教授学术研究的精华之作,便斗胆以一半是门外汉的身份,谈几点读后感吧。
头一点感触,便是要正确识读古文字,必须对汉字从甲骨文直到汉代的小篆和隶书的字形有一个通盘的了解。吾师于省吾先生早就说过,商周古文字是“本”,小篆是“末”,研究文字“须本末兼晐。本固重矣,而其所以演变以至于末者,迹必相衔,方可徵信”。不过,像我这一代的古文字研究者们,大都是从金文、甲骨文入手,当时战国简牍出土无多,汉代篆隶也尚无专门的研究。所以在研究“迹必相衔”时,难免头重脚轻。赵平安则不然,从攻读博士时便研究“隶变”这一汉字演进史上的重要关键变化,博士后又专门研究汉代小篆的实际字形,从汉字演进序列的观点来考察小篆字形的讹误和篡改,使他在“末”这一头有了坚实的基础。而又在不断新出土的战国简牍文字上有很扎实的功夫。所以反过来考察金文、甲骨文,便会有不同于前人的创见。例如,他发现了甲骨文中的 ,从字形演变的规律可以和战国文字的 所从的 联系起来,从而把这个甲骨文释为逸失的失,现在已经得到甲骨学界一致的认可。这种用不断新出土的战国文字为出发点去释读过去聚讼纷纭的甲骨文的办法,赵平安是先行者之一,现在已经蔚然成风了。又如,他注意到秦隶中的鞫字有由 变 的现象,从而认定甲骨文中的 、就是隶书中偏旁 的原始象形字。并就字形推定有“械系”“拘禁”,引申为“审讯定罪”之义,是很有说服力的。这种用古隶为出发点识读先秦古文字的研究方法,应该还有潜力,是应该继续发扬的。
第二个感触,是研究战国简帛材料,不但要有文字学的修养,一定要熟读古书。例如郭店简《穷达以时》第九号简上的“初 酭,后名扬,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后一句裘锡圭引《韩诗外传》卷七:“伍子胥前功多,后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阖闾,后遇夫差也。”说明是指伍子胥。但前一句一直不得其解,池田知久以为是指向楚庄王举荐叔孙敖为相的虞丘,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句话。赵平安首先从正确识字着手,把“酭”前一字改释为,又按孙诒让《周礼正义》把“醓酭”解释为用牲肉做成的肉酱。然后从《楚辞·九章·涉江》有“比干菹醢”,再推定前一句的主语应该是比干。为了论证是比干,又引了《荀子》的《宥坐》《臣道》《大略》,《鹖冠子》的《备知》,《吕氏春秋》的《不苟》,《盐铁论》的《非鞅》《散不足》,《韩诗外传》卷一,《论衡》的《死伪》,《新序》的《杂事》《节士》,《中论》的《夭寿》等十多种文献,证明战国秦汉时多将比干和伍子胥并提。所以就相当有说服力。一般说来,像我这样1949年后还在读小学的人,古书底子都是差的。赵平安比我还要小很多,能有这样的古书功底,我是很佩服的。实际上,现在很多更年轻的战国简牍研究者,都认识到要正确识读战国简牍文字,必不可少的一门功夫是要熟知古书,能找到简牍文句和传世古籍的对应关系,这在正确释读文句中的关键文字时,有时能起很大的帮助。赵平安在这方面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第三个感触,赵平安并不是单纯的古文字学家。因为,他在河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苦读三年,写出的硕士论文《汉字形体结构围绕字音字义的表现而进行的改造》一文,就是纵观整个汉字发展史,从甲金篆隶及近世俗字材料中归纳出历代汉字在表音和表义两个方面的改造法,是在汉字发展史上很有创新意义的力作。所以,他早已立志于以汉字发展史为己任。他也不是单纯的出土文献专家,因为,他在综合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文字资料中还不时对所涉时代的经济、政治、思想等历史问题有崭新的认识,所以,他也是研究先秦乃至秦汉时代的历史学家。
总之,匆匆读完赵平安教授的自选集,虽然未必每一篇都能深入思索,但对他治学的全貌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便深深感到我们俩虽然年龄相差约四分之一个世纪,在学术取向上是志同道合的。我一向认为,中华文化能传承几千年不断,汉字是一大功臣。古文字研究者理应以研究整个汉字发展史为更高的目标。出土文献的研究,应为所涉年代的历史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新资料,不断为验证和更新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而服务。因此,我欣喜地愿以步入暮年之躯同正当壮年的赵平安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继续努力多作新的贡献。也希望研究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的队伍中,出现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一起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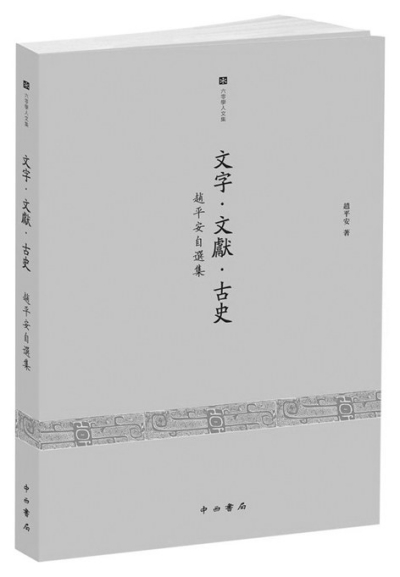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