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对各种美食不加挑剔的热爱,且热衷搜寻平民美食,陈晓卿被朋友们戏称为“扫街嘴”。十余年来他不光领衔制作了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系列,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诸多美食文章,《至味在人间》即是对此前文章的首度精选结集。
每一个人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窗外的晨雾中,浅绿的麦田、淡青的屋舍以及裹挟着细雨的淮北平原飞驰而来……广播里的声音在说,列车前方停靠的是:宿州车站。
整一宿,上铺的老兄电话短信一直没有间断,听口气,电话那端显然是不同的女人,尽管他已经努力压低了声音,但关键的话永远要到走道里说,下铺上铺开门关门顺带给保温杯里续水,一刻都没消停,身体真好啊!等他终于清静下来安然入眠,我已经离目的地不到一小时了……下到站台,父母照例在那里等着,看到我一脸的疲倦,我爹忙叮嘱说:“赶紧回去,再睡一会吧。”想了想,我还是建议先吃早饭。
于是扛着行李打上车,穿过刚刚开始苏醒的街道和毛毛雨中的小巷,到了一家羊肉汤馆,五元钱一大碗的羊汤庄严地摆放在面前,把羊油辣子和香醋调匀,深深一口下去……哎呀!喉结蠕动的同时,阻滞的气血开始融化、流动。我不由将四肢伸展开来,以便让口腔的愉悦尽快蔓延到整个身体的每一个末梢——现在,才算是真的到家了。
皖北地区的羊汤大多冠以萧县羊肉汤的名号。萧县归宿州市管辖,该县丁里镇多回民聚居,因此羊汤做得格外出名。中医说羊肉性温,多食上火。但萧县的风俗是,越到夏天越要吃,尤其是三伏天的羊肉比其他季节的都要细腻味甘,故此亦称“伏羊”,据说江苏徐州正和萧县为了“伏羊”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情,掰扯得不可开交。十年前最热的季节,长途车去萧县的路非常烂,但我仍然慕名去了丁里,找到那家“青春羊肉馆”,挥汗大嚼,如果说味道有多特别,我还真说不上来,但足以让我回到北京想得涎水连连。
据说北京这座城市有三种人:外国人、外地人和北京人,我显然属于第二类。尽管我已经居住了二十八年,但一直找不到味觉上的归属感。“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一段时间不吃老家的东西会有些想。”坐在清华东路的一家韩餐馆子里,青年作家罗永浩老师幽幽地问我。“当然。”我的注意力都在那盘菜包肉(清水煮的猪肉,蘸豆酱,和着新鲜的不太咸的泡菜一起吃)上面,根本没工夫答话。他接着问我去过韩国没有,我摇摇头。“那就好办了。”他拍了下大腿,开始介绍这里的正宗韩国农家菜,“朝鲜的农家菜铆足劲就做三样:脊骨土豆汤、菜包肉、煎饼。最有特点的是这家的泡菜,北京很少有人做得比这儿正宗,太朝鲜太韩国了……”
罗老师出生在东北,朝鲜族。和很多革命先烈一样,老罗年轻时曾经远赴海外勤工俭学,地点在首尔。在考察工人运动现状的过程中,他的肠胃也被韩国料理所征服。“同样是农家菜,韩国的还是比我老家更精致一些。”据老罗说,这家韩国人开的“故乡福星”很像在韩国的口感,也正是老三样吸引了他,所以隔些日子就要来一次,每次吃完心情都会大好。说完,罗老师舀起一瓢脊骨汤,慢慢喝了下去,镜片后面的眼睛也随之眯了起来,特文学,不由地让人联想到那“一湾浅浅的海峡”般的乡愁。
青少年时代的顽固味觉记忆,势必影响人一生的食物选择。远的,像珍珠翡翠白玉汤,传说,不提也罢。1974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当时国家发给的出国补贴是二十美元,回国之前,大家都在计划买点什么纪念品,只有邓副总理按兵不动,直到去巴黎转机的时候,他才把钱掏出来,找了一家面包店,全部买了baguette(一说买的是croissant),当做礼物送给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学生会干部周恩来,在北京接机的周学长当场被感动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博得领导的心,首先要摸清他的胃。
和老罗不同的是,猪脊骨土豆汤虽然也不错,但怎奈我的珍珠翡翠白玉汤是伏羊汤,敢情每一个在北京的外地人,都有专属于自己汤的味觉记忆。
十六岁之前,我从没有正式下过“馆子”。那年暑假,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下松弛得无所事事,于是跟我爹到宿州(当时还叫宿县)开会。可能因为伙食太差,有天中午,我爹带着我出来,径直到了南关电影院门口,进了一家现在记不得名字的饭馆。我爹让我找座位,自己则去开票。一会儿,一屉包子和两碗汤便上了桌。我爸从一只小碗里擓了一勺羊油辣子,放在我的碗里,橘红色的固体物在滚汤里慢慢融化扩散……肉是顺着动物肌理切的,一小片一小片薄如蝉翼,半透明地散落在汤的表层。我很小心地吃了一片,很有嚼劲,香,而且回甜。进而再喝汤,浓得像奶一样,非常鲜!苍天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那碗汤和那个赤日炎炎的夏天以及我上颚烫出的水泡,就这样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和韩餐遍地开花不同,在北京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找到一家萧县羊肉汤。我常去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闹市口宿州驻京办,不对外营业,要预定;另一个在中关村皇冠假日,五星级酒店,但我知道业主专门请了萧县的厨子。每次去,不看菜单,只点一碗羊肉汤,两个油酥馍。ok了。服务员僵在那里,拼命推荐其他菜——这样次数一多,脸皮薄,也不好意思再去。这不,只好坐火车回家。
2010年4月5日
周瑜小馆黄盖客
每次去翠清吃饭,看着正在等座的绝望食客们,我都会想到一位我曾经的女同事。
三四年前的一个冬天,因为加班,办公室集体去吃拉面,我这位同事拒绝前往:“咱们去吃翠清吧,湖南菜,超级好吃。”我刚有些迟疑,她又加了一句:“不过,菜是好吃,但要排一小会会儿队哦。”我呸,哪有时间等座儿!全体上车,只剩下她瘦骨嶙峋的身影。
那顿饭是这样的,吃面归来,收到那位姑娘的短信:“还在排队,不要嘛,该死的。”半小时后,“前面还有两桌,不想活了讨厌。”再二十分钟,“天杀的,终于坐下了。”又约四十分钟后她又发来短信,只两字:“真好。”如果把几条短信编辑一下,是否能够得到如下的答案,“该死的,不要嘛,天杀的,我不想活了……你真好。”这简直就是一个怨妇突然见到丈夫归来的心路历程。也正是因为这位先驱者那次令人发指的等待,让我对这家叫翠清的小店青眼有加,并迅速成为它的常客。
颐源居西门,扎堆儿着一大片小馆子,但要说最火爆的非翠清莫属。我的朋友老六就曾经站在翠微路的暮色里思考人生:“你看,这家叫翠清的一点都不冷清,而对面那家叫翠满楼的却总坐不满人,这是为什么呢?”确实,翠清的门脸儿不大,但每天饭点儿,沿街排队等座的人却相当扎眼。
其实,翠清的菜单不过一页纸,难得的是,几乎每个客人都能从里面找到自己的最爱。老六的饭局常设在这里后,最经常看到的景象是这样的:人刚刚到齐,服务员过来,我还没来得及拿起菜单,旁边就一人一嘴嚷嚷开了——酱椒鱼头、小炒肉、萝卜丝煮河虾、干锅鱼杂……七嘴八舌一通嘈杂过后,陈晓楠同学还用商量的口吻说:“哥,我能点两份小炒猪肝么?我保证吃完。”话音未落,喜欢终极思考的老六立即说:“按此理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要两份鱼头呢?”……等我颤巍巍把自己喜欢的砂锅粉丝添加上去之后,“你们已经点了十七个菜了!”服务员面无表情地说。
翠清的服务员是我见过的最有“气节”的服务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那种。打电话订座,她们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包间只留到六点半,人数不够按最低消费收费”,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如果你想上个拍黄瓜或者花生米下酒,得到的回答永远是不卑不亢的“我们不做凉菜”:上菜时,她们也会大声命令你“把转盘转一下”,十分威严,不容置疑……
没办法,有什么样的饭馆就有什么样的客人,如果翠清是周瑜,我们就是黄盖——谁让我们爱吃这一口呢?尤其是喜欢思考人生的老六,只要到了翠清,人性里最温顺的一面总会被激发到极致。“姑娘,”老六撒娇道,“能帮我们催一催菜么?我的唾液在玩着命地分泌呢。”服务员看了他一眼,甩下一句“现在人多”旋即给了一个骄傲的背影……老六这边一点都没失落,抚着胸对着空气嗔道:“我还就喜欢你这个简单粗暴劲儿……”
经验告诉我,要求一个苍蝇小馆的服务态度,无疑会增加你享用菜品质量的风险。好在和服务员的强硬相匹配,翠清的饭菜一样霸道无比——几乎是我在北京吃到的最顶尖的“口味菜”。更难得的是,这些年,他们家的品质一直没有任何改变。去年给“餐厅大赏”做评委,我极力推荐了本来不在候选名单上的翠清。究其原因,不仅因为这家湘菜小馆精心烹制的饭菜个性十足,口碑甚好;更因为它是我这几年剃头挑子一头热追求的民间美食典型。有这么可口的美食,嗨!态度粗暴就粗暴点儿嘛。
我把这个道理说给老六听,他立即展开终极思考:“按此理论,难不成最好吃的饭馆……得是城管开的吧?”
2009年3月18日
螺蛳壳里的道场
南京里下河土菜馆,盱眙小龙虾号称已经上市,将近二十人的大桌,东道主好客地摆满了碗碟。烧麻鸭、河虾煮千张、昂刺鱼炖豆腐……吃得非常尽兴。然而,我还是忍不住弱弱地说出了“螺蛳”两个字。吃螺蛳最好的季节是清明节前的那几天,这是螺肉最肥美的时候。之前的偏瘦且没有膏黄,清明过后,螺蛳便到了甩籽(就是产卵)的季节,尾部充斥着密密麻麻的小硬壳。因此,清明时节雨纷纷,想到螺蛳欲断魂……赶在清明前去江南出差,螺蛳自然是不能缺少的。
主人丝毫没有怠慢,立刻伸出了沾满小龙虾汤汁的手掌呼喊服务员:“加两盘螺蛳,不,四盘!”待螺蛳上桌,个个晶莹饱满,拈一只轻轻一吸,一团肉早就端放在舌尖之上,随肉奉送的还有一汪鲜美的汁水……感动!整个童年时代,我很少吃到螺蛳。就像炸酱面一样,螺蛳当然是家里做的最好吃——买回来的新鲜螺蛳放在水里,滴两滴香油,两天过后,去尽泥沙,加姜葱豆豉辣椒旺火爆炒后,加骨头汤焖一下,如果有紫苏的话,放几片味道更美。可当年我的父母总是强调说,那东西吃了会得血吸虫病,今天想来,这不过是他们怕麻烦的借口罢了。
老家的螺蛳在下锅前,首先要用刷子刷过,再逐一将尾部剪掉。剪螺蛳是一道非常细致繁琐的工作,一般从尾数第二节下钳,为的是去除余下的一点点泥沙,同时也让螺蛳在烹炒时更加入味。螺蛳在我老家称作“屋牛”,有句歇后语就叫“鸭子吃屋牛——食而不知其味”,确实,如果不把螺蛳坚硬的壳事先剪出突破口,很难想象作料的主力部队如何能攻破它固若金汤的城池。
北京夜市的排档也常有螺蛳售卖,或淘洗未净,糟污拖泥带水,碜牙;或火候太过,螺肉坚硬如铁,硌牙。最关键的,北人粗犷,炒制螺蛳时无一例外忽略了去尾的这道工序,因此炒出的螺蛳味道很难进入膏黄部分,而且为了让螺肉与螺壳分离,必须搭配使用牙签。所以在北京,除非自己家里,我极少点螺蛳上桌。偶尔摆上此物,吃两颗,除了有变成鸭子的幻觉,内心更加怀念南方。这种味觉上的冥顽不化,颇有些类似鲁迅在北京看到下雪时的心境,在他的笔下,“朔方的雪”在纷飞之后,永远如粉如沙,决不粘连…而“江南的雪”则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我常常想,其实这里把雪代换成螺蛳,显然也是成立的。
螺蛳美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正像我们这桌几位食指大动的客人,耐不住性子高喊:“服务员,拿牙签来!”举目望去,果然是几个北方汉子。于是,同桌一位当地的女性同行,在流露无限同情之后,便开始用记录速度示范螺蛳品尝教程:伸出纤纤玉手,用前三个指头拈住一颗螺蛳,轻轻靠近唇边,两颊微微一颤,指尖便只剩下一只空壳……整个过程就像打了一个飞吻,轻佻又不失优雅,加上眼波流转,直看得糙汉们食欲难填,纷纷仿效,抓过几只,笨拙地吮吸着,弄得一屋子山响。
吸螺蛳确有技巧存在,嘬的那一刹那像极了婴儿吮奶,只需要口腔前部动作。如果用力过猛,往往会呛到气管。一位北京同事被呛得歪头猛咳,进而抱怨说:“这劳什子,干嘛不索性把壳儿去掉,只烧螺肉岂不痛快?”但吃螺蛳正如吃瓜子,许多乐趣正在一个“嗑”字上,这是直接食用瓜子仁所不能享受得到的曼妙过程,如果这个过程也省略了的话,以后人类进食不妨采用注射了事。吃瓜子的劈劈剥剥和吃螺蛳的啵啵动效,何尝不是味觉器官与食物的友好交谈呢?多么亲切友好的气氛!
从南京离开,沿着皖南的高速公路又到安庆。一路上,油菜花盛开,徽式建筑婉约地置身在黄色的画卷中。路上再次遇到一群北京的文学中年,伊们是为了悼念安徽的一位诗人而来。晚上一起宵夜,他们在不停地谈诗谈文学,我则端坐一边尽心尽力地吮着美味的田螺,各不相扰。有一刻,吃得眼睛濡湿,望着窗外阑珊的灯火,耳边忽听一位诗人缓缓吟道: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吃螺蛳……
2009年4月8日
除了蛋,我们来认识一下母鸡
前一阵,沈宏非老师在南京,问我愿不愿去,我一点没犹豫就答应了。见沈爷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南京有一位我熟识的帅哥厨师,叫侯新庆。我和侯师傅四年前相识,再次吃到他做的菜,亲切中有了些变化。其中两道,现在想起还会舔舔上唇。一道是自制年糕烧黄鱼,糯米粉和蛋清、猪油、盐同蒸,趁热搓条。新鲜黄鱼煎到两面金黄,加炸好的蒜子和高汤,烧熟后撒进年糕,淋上葱油,质地绵密的年糕浸饱了鱼汁……
另一道砂锅神仙蛋煮素鸡,味道更加独特。从已经略微呈胶状的汤汁里舀出一只虎皮蛋,一入口先是汤的浓香,牙齿依次穿过已经软帖的焦皮,富有弹性的蛋白,里面竟然是鲜嫩的肉圆!据说这是扬州的民间做法,鸡蛋略煮成型,趁热用吸管吸出蛋黄再填进调好味的五花肉糜。吃着蛋,脑补着侯大师温文尔雅吸蛋黄的样子,直有种想冲进后厨握住“母鸡”双手的冲动。
钱锺书说吃鸡蛋就好,何必认识母鸡。但有时候认识了母鸡,鸡蛋的味道会发生很大变化。当初,侯老师还在北京,《舌尖1》里的淮扬菜、汤包段落拍的都是他。拍摄回来,摄影师闫大众跟我说,在小侯那里,终于见到了国内“最整洁、看不到一滴水”的厨房。因为是国际餐饮集团管理,小侯所在的中国大饭店后厨不能进“活物”。于是,每天早上都能看见这样的情景,侯师傅坐在前厅,手边放着一盒活虾,一个一个慢慢地剥。这以后,再吃到龙井虾仁的时候,确实有种不一样的味道。
对餐饮经营者来说,厨师是一个餐厅的核心。对于成功的餐厅,厨师甚至是一道风景。想想侯师傅坐在门口剥虾的样子,确实像一幅画。
不过,常年和厨师们打交道的最大收获,是能够了解他们对食物的感受,这是一群离美食最近的人。日餐厨师程世儒,在神户从业十年后,回北京开了家居酒屋。小店只有一个操作台,加三张桌子,并且每天只有晚上营业,星期天休息——这是日本的习惯。第一次朋友带着,我当场被面前特别新鲜的食材感动了。小程每天早晨都在附近的新源里菜场逡巡,这会占用他整整半天的时间。之后,他会根据食材设计当天写在黑板上的菜单。
经常去他店里,他会说,“可巧,我今天买了金目鲷。”“可巧,今天进了籽蟹。”“可巧,今天有从日本来的,可以刺身的青花。”再后来,我会直接告诉他,你索性先给我来一份“可巧”吧。小程是我感知季节的一个探头,他总能用最新鲜的食材折射出对节令最敏感的体悟。
因为职业原因,和很多厨师成了朋友,也对厨师这个行当有了不少新的认识。我写过这样的解说词:“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昆曲、京剧,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从这个角度来说,厨师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文明的伟大书写者。”这不是奉承,是真心话。
大董餐厅是北京餐饮界的翘楚。去年有几个内蒙古学员在大董学习,大师傅董振祥在这些学员心目里,往好了说就是大神,最不济也是头条界的汪峰,有半壁江山的气场。实习结束,大董本人照例要请学员吃饭,面对餐桌上铺天盖地的崇拜,大董没说话,带着大家出门找了个煎饼摊,大师傅让卖煎饼果子的靠边,他要给大家露一手。然而,连续三张煎饼都不是很完美,有的甚至破了洞,大师傅停了下来,对大家说:“在你们看来,我已经是非常好的厨师,但你们看到了,我连煎饼都摊不好。餐饮这一行,太博大精深,只要你专注一门技艺,就能有自己的饭碗。”
我理解大董说的“饭碗”里埋藏的朴素道理,做厨师这一行只要用心,只要专注,就一定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假以时日,就有机会成为大神,成为季节的使者,成为餐厅的风景……
2015年8月30日
那条愤世嫉俗的鱼
一条腌制过的鳜鱼,汁紧芡亮,身披着红椒、白蒜、青葱,出现在餐桌上,远远看去像一个裹着国旗的意大利球迷,鲜艳动人。刚要动筷子,却有一股怪味传来——这便是闻名于世的徽州腌鲜鳜鱼,也就是臭鳜鱼了。
最近出去吃饭,不管是湖南馆子还是四川馆子,几乎都多了臭鳜鱼这道新菜,大有一条鱼臭遍天下之势。据说臭鳜鱼最早出现在乾隆初年。但资料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却几乎都是“民间传说”,说是某挑夫暑天运送鳜鱼,发现桶中的鲜鱼已经不新鲜甚至有些变味,于是逐条抹上盐巴……这个听上去更像风景名胜点三流导游的解说,我一直存疑。如果说是乾隆年间的事情,我们不妨看一下同时代的《扬州画舫录》,里面不仅有大量的饮馔食事记载,还记录了大量名人雅士的生活。当时的扬州相当于现在的上海、广州,是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心。扬州最著名最有钱的是盐商,相当于现在的煤老板,他们在这座城市中到处买房子置地建园林,因为政治诉求无法实现,同时又掌握了富可敌国的资金,这使得他们把更多的爱好投入到建筑和美食上。
《扬州画舫录》对这些上流社会
人士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状态多有辑录,出于与官府交际及商务应酬的需要,加之炫耀露富和及时行乐的心理,一些盐商“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比如有人用参、术、耆、枣研末饲养母鸡,食用这鸡所生之蛋,每枚价值白银一两。还有盐商精于烹饪,如吴楷就善于制作“蛼螯糊涂饼”(玉练槌)……要知道,当时最著名的几十位盐商中,有一多半是徽州籍人士,但却找不到臭鳜鱼的只言片语。相反,在同时代的《调鼎集》中(作者据说也是位盐商),却信誓旦旦称鳜鱼“不可糟亦不可腌”。所以,我同意臭鳜鱼来源于民间,但究竟出现于何时?待考。
从前文人雅士多有闲心,喜欢鼓捣点儿厨艺。李渔的《闲情偶寄》和袁枚的《随园食单》都有大量河鲜料理的方式方法,不过这两位爷基本属于光说不练的主儿。倒是后来,安徽籍的胡适博士,偶尔喜欢“洗手作羹汤”,上世纪30年代,在老北大旁边的王府井承华园,胡先生亲自发明了“胡博士鱼”,其法为鱼脔切丁,加三鲜细料熬成鱼羹。在当时,这道菜与马叙伦先生的“马先生汤”,张竞生先生的“张先生豆腐”比肩,成为京华一时名馔。
不过胡博士的鱼羹用料是鲤鱼,档次上没有办法与鳜鱼相提并论。鳜鱼在河鲜中仅次于鲥鱼和刀鱼,刺少肉滑,比日常所见的鲫鲤鳙鲢高贵许多,是各类食单菜谱中不可或缺的一味。张志和有“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诗句,但鱖鱼不仅见于诗词,更是画家笔下的常客。李复堂、齐白石尤其八大山人,那条孤独的鳜鱼翻转着赵薇李承鹏式的大眼,一副离世脱俗之相,人见尤怜。鳜鱼的食法极多,有烧、炒、蒸、烩、瓤、煎、酥焖、醋熘等多种方法,淮扬菜系中,最知名的要算“醋熘鳜鱼”与“松鼠鳜鱼”,但徽菜中的臭鳜鱼却是独树一帜。
今天的北京,在为数不多的徽菜馆可以品尝到制作水平参差不齐的腌鲜鳜鱼,以比较正宗的为例,腌鲜鳜鱼的做法应该是,鳜鱼宰杀、净膛、洗净沥干。在鳜鱼的膛内和外部均匀地涂抹上盐,葱切段,姜切片,将抹好盐的鳜鱼放于大盆内,一层鳜鱼一层葱、姜,层层码放。腌制八小时后进行翻倒,上部的翻到下面,下面的翻到上面(鳜鱼腌制发酵时间,夏季一般腌制三至四天,冬季腌制八至十二天,每隔八小时翻一次。腌制鳜鱼时的气温温度以二十八摄氏度为宜)。这样的腌鳜鱼,一方面是盐水渍入,另一方面鱼肉会自然发酵。
而前面说的其他菜系餐厅的臭鳜鱼,吃起来不像徽式的那样咸得齁人,鲜香的气味甚至更加外在,更加适合“现代人饮食习惯”。但功夫和差异还是看得出来的,只因为他们使用的不是腌制的方法,更多是调和好卤水,只浸泡一天便送去烹调。和一位徽菜特级大师交流,他无法理解,“臭水泡出来的,这不是毁了徽菜吗?”他教我区分两者差异:传统的做法应该是异香扑鼻,鱼肉粉润,肉质不粉,呈蒜瓣状,咸鲜适口。而“新式”的做法,尽管味道更加亲和,肉质也能维持蒜瓣状,但入口却失于松散,尤其颜色,绝对无法和传统做法相提并论。
想到自己平生吃到的记忆最深刻的一条腌鲜鳜鱼,是在皖南,厨师长亲自料理的。那是去年桃花刚刚开完的季节,新鲜的鳜鱼腌制之后,切块干烧,芳香扑鼻,肉质极其细嫩。举箸夹在眼前,鱼肉如鲜百合一样,层层散开。这时候,能看到鱼肉的横断面中心雪白,往边上渐渐上色,到最边缘,居然艳若桃花一般了。
2010年2月12日
(本文摘自《至味在人间》,陈晓卿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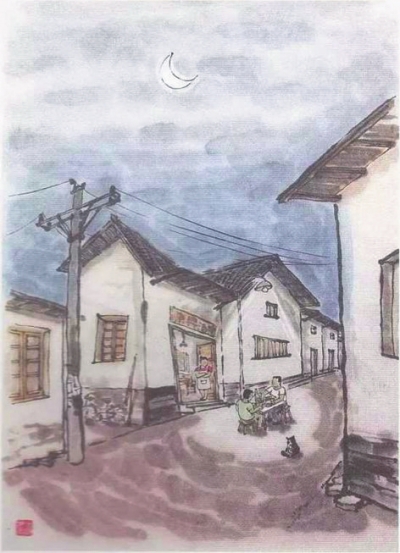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