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话不是一味灌输或迎合,而更像是一位坐在孩子们中间的父亲或者游戏组织者,殷勤而兴奋地为他们打开一个个精彩的书中世界。
“青灯有味似儿时”,如果童年时代的阅读记忆能够伴随着愉悦和情致,那么培育的阅读兴味将会影响久远,甚至伴随终身。假使这种记忆是以场景化的形式织入生命的底色,那么这种在场的阅读记忆尤会稳固和鲜活:伴随着更丰富、立体的信息关联,即使逼近老境,独对青灯夜读,依旧会勾起彼时彼人、彼情彼景的盎然意味。
在我看来,本土新锐图画书作家杨思帆的三部近作《呀!》《错了?》及《奇妙的书》正是具有上述“在场阅读”特征的作品。在这三部作品中,杨思帆以“在场创作”实现“在场阅读”——他以现代儿童观、艺术观以及个性化的艺术表达,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作者与读者共存的阅读场,在这样的创作和阅读场景中,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微妙而平衡的,作家弱化了对读者控制的权力,转而寻求一种新的相处之道,那便是“对话”。
这首先体现在这几部作品的语言上。无论是有字图画书《呀!》《错了?》还是无字书《奇妙的书》,其语言表达都极为节制、自然,充满童趣,具有强烈的亲和力。尤其是《错了?》中使用问答句的形式,重复的句型与交替的画面节奏相配合,打破了常规的言说姿态。每一次“错了?”,都是作者向读者发出的共读邀请:“你觉得错了吗?”“你猜到我的想法了吗?”“猜对/错啦!要不要继续挑战?”“你有什么更好的想法?”这是类似《别让鸽子开巴士》那样须要读者接受邀请才能完成的作品,这是如同《一起玩形状游戏!》那样作者和读者共同玩得不亦乐乎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错了?》是一处作者和读者共同搭建的阅读场,在交互的阅读游戏中,读者亦拥有对文本的解读权和建构权,从而获得专属于自己的阅读意义。
在这样的语言方式和阅读挑战中,作者和读者产生了对话。这种对话不是一味灌输或迎合,而更像是一位坐在孩子们中间的父亲或者游戏组织者,殷勤而兴奋地为他们打开一个个精彩的书中世界。又像是一个以孩子的笑声为唯一报酬的魔术师,搭好舞台、设置机关,从容而狡黠地开始挥动魔杖,在一次次“错了?”“呀!”的猜测和惊喜中,为孩子们演绎出精彩纷呈的“纸面魔术”。如同杰出的图画书作家伊娃娜·奇米勒斯卡所说:“一本好书就像一位亲切的主人,它热情地迎接读者,用美味的饭菜招待他们,而不是自己一味地讲话,装作无所不知的样子。一本好书是和读者谈论有趣的话题。”在这里,成人和儿童构成了一种平衡的关系,不是训导、计算、控制与反控制,而是大家开开心心地围坐在一起玩游戏、听故事、看魔术、聊话题。作为一位常常给自己孩子读书的父亲,我想杨思帆能够设计出这样的在场感并不是偶然的。
“纸面魔术师”杨思帆非常明了孩子的心理,他选取的物象是儿童所熟悉的生活物品、常见动物,特别是各种美食——食欲得到满足本身就是儿童快感来源之一。在美食的诱惑下,孩子们很轻松地被魔术师引入到阅读场中。杨思帆很好地利用了相似联想,将这些物象用在本不该存在的地方,或者天马行空地改变其原有用途,造成强烈的陌生感和滑稽感。尤其是《呀!》中那些食品和动物身体部位的代换,为读者营造了非同一般的奇趣感和阅读的戏剧性。伊格尔顿指出:“文学文本最重要的意图并不是提供事实。相反,它邀请读者‘想象’事实,即用事实建构一个想象的世界。”在《呀!》《奇妙的书》这些作品中,杨思帆拆解和割断了物与功能、物与意义之间关联的必然性,于思维惯性的破坏中重建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邀请读者从此岸的事实出发去想象彼岸世界的无限可能。
杨思帆这样一位本土新锐创作者的出现并非偶然,乃是二十余年来,在优质外版图画书的大量引进,无数本土创作者、出版者、研究者、阅读推广人的深耕,中国原创图画书界已经有了较为开阔的艺术眼光、相当的创作经验积累和对图画书艺术及其创作机理更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其个人的创作发展轨迹和本土原创图画书的发展几乎同步,他的创作走向也成为一个表征:个体的成功与失败、得意与缺憾,乃至主题与表达方式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来路与当下状态的缩影和象征,这恰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在场”——见证与参与当代本土图画书的发展进程。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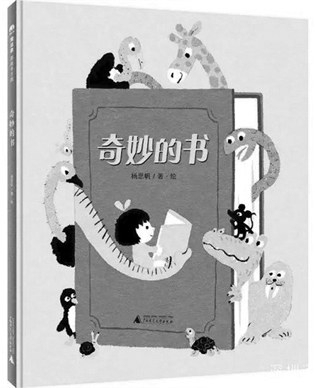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