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作为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股被遮蔽于主流之外的古典主义,迟迟未能得到深层阐发与主导性的梳理。所幸,曹氏兄妹以坚定的美学坚持和持续的作品实践,在儿童文学领域竖起了一面古典美学的旗帜。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要为我的童年时代所经受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的文学归宿”。每一位优秀甚至伟大的作家,心里都有一座永恒的故乡。比如,马尔克斯与他的马贡多,马克吐温与密西西比河,威廉·福克纳与他的南方小镇,大江健三郎在小说里反复回忆森林与自己的关系,湘西之于沈从文,当然,包括水乡之于作家曹文轩、曹文芳兄妹。
“‘我家住在一条大河边上。’这是我最喜欢的情景,我竟然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写过这个迷人的句子。那时,我就进入了水的世界。一条大河,一条烟雨濛濛的大河,在飘动着。流水汩汩,我的笔下也在流水汩汩。”曹文轩曾在《十年回首:〈草房子〉创作札记》(《中华读书报》2007年9月19日“成长”版)一文中深情回忆。
故乡,或说水乡,这种典型的中国古典主义的环境、意境,深刻影响了曹文轩包括曹文芳兄妹的精神层面、情感性格,包括创作和美学观。不管是曹文轩,还是曹文芳,都是文质彬彬、端庄典雅,似春风,如流水;而在创作和美学观层面,不管潮流和风向如何多变,曹氏兄妹均没有追新逐热,而是独树一帜地坚持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和叙事风格,承继由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开启的现代文学一脉相承的古典美学的小说空间。
作为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股被遮蔽于主流之外的古典主义,我以为一度被学界有意无意地低视,迟迟未能得到深层阐发与主导性的梳理。实质上,古典主义无论是作为一股文艺思潮抑或是一种审美理想,它在20世纪乃至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中始终占有至为重要的一席之地,更是中国文学文化史的始终未曾中断的精神命脉,亟待当下学界展开多元视阈维度的综观、廓清、勾勒及更高视点的解读。所幸,曹氏兄妹以坚定的美学坚持和持续的作品实践,在儿童文学领域领域竖起了一面古典美学的旗帜。
总而言之,童年的经验和记忆是曹文芳文学作品取之不尽的源泉,古典而唯美的风格、轻盈俏皮而灵动的语言,犹如一泓清泉,把人们从现实的残酷与苦闷的泥潭深处带到一片充满爱与美的诗意天空。其实,作为著名作家曹文轩的妹妹,曹文芳的创作特色和价值一度是被曹文轩的光芒有所遮蔽的。
人性的坚守和美好人性的描绘,是曹文芳作品古典美的主要特色之一。在她笔下的糖河镇、西溪镇,无不充盈着邻里互助守望的温暖,紫苏、红婷,“我”和小鸭子,孩子之间真挚朴实的友情,还有浓浓的亲情、乡情,处处闪耀着人情人性的美好光芒。这是一种古典温情的写作姿态。
如果说,曹文轩的语言风格是诗意流淌,呈现丰富而优美的意象,曹文芳的作品则真情至性,纯真流露,“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自然、本色、纯真。比如《石榴灯》里的这一段,“外公背着手在屋里走动,一下找到了当年做私塾先生的感觉,不时问孩子们,‘有没有不会写的字,如果有,可以问外公,外公乐意教你们写’。”深得明清小品的个中三味,“趣”需与“真”联系,需具童心,作品才纯真自然。此外,曹文芳作品秉持的是一种节制而克制的古典主义写作姿态,即“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其实,肆意渲染的苦难,过分夸大的悲伤,反而会使作品陷入浅薄和轻浮。有节制的写作,文本的留白,反而给作品留下了充盈的思考空间和想象空间。比如,《紫糖河》中的红婷,竭尽全力也无法敲准鼓点,最后被迫退出腰鼓队。退出一场盛大的演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无异于世界一角的崩塌,文本是这样呈现的,“红婷很难过,但一句话也没有说”,“天色已晚,同学们还能看见红婷孤单单坐在操场边的身影”。余意无穷。
古典主义的风格在曹文芳作品文本中的呈现,还包括音乐性的语言、美的意象、浪漫色彩的大自然景象,包括不温不火、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和细节。
在曹文轩的作品中,虽然秉持的也是古典而唯美的风格,但我们往往能看到的是,文本让人性当中最有力量的点引发爆炸,让人与命运抗争当中或残酷,或高尚的东西闪烁,绽放美丽的生命之花。读者可以从阅读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人性的伟大力量,一种崇高的悲悯情怀。
而曹文芳的作品虽然也写人生之无常,生活之艰难,但风格更为平和柔顺、天真俏皮,不把主人公和读者逼至绝境,让我们更多体验的是作家的温情与关怀。
或者,这就是男作家和女作家的区别。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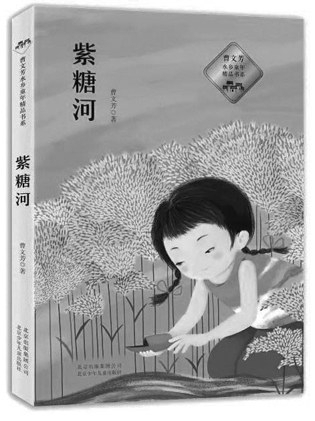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