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9月7日,23岁的英国小伙子威廉·麦吉利夫雷怀揣10英镑,带着极其简单的行李从家乡亚伯丁出发,开始长达800英里的行走。为了便于田野调查,他特意选择了一条曲折的路线,最终于10月20日抵达终点伦敦。这个距离比北京至上海的距离更远,算下来平均每天要走30多公里,为此威廉每天四点半得起床,辛苦至极。
同时代,像威廉这样钟情博物学而精力旺盛者绝非凤毛麟角。为了从事博物学研究,有人从不知疲惫,有人从不休假,有人经常忘记是否吃过饭……当时的博物学家普遍认为,时代使“他们对懒散有一种负罪和厌恶感,娱乐从来不能令他们放松”。
博物学家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本书作者大卫·埃利斯顿·艾伦则认为,这一群体的表现不过是19世纪田野俱乐部蔚为风潮的时代症候——1873年,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169家地方科学协会中多达104家是明确的田野俱乐部。
1962年春,大卫·埃利斯顿·艾伦在为不列颠群岛植物学协会会议策划一个小展览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实——广泛的全国性潮流忠实而明确地反映在了这个微缩世界之中”,博物学发展无异于社会史的一张晴雨表:透过博物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碎到系统、从业余到专业等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期社会潮流与博物学之间的相互影响。
历史上英国是博物学最为发达的国家,知名博物学家比比皆是,如约翰·雷、吉尔伯特·怀特、林奈、达尔文、赫胥黎、赖尔等。艾伦写作此书,并不是为了给这些知名人物树碑立传,而是从社会史角度,追溯博物学家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发展历程,讲述学徒药剂师们的“植物采集活动”、国家保护区和跨国协会的建立,也讲述博物学作为一门组织化学科的诞生过程(包括植物、地质、鸟类、昆虫、海洋生物、生态等学科领域)。
从可查寻的记录看,英国的博物学协会肇始于17世纪的药剂师协会。因为工作关系,药剂师们必须正确鉴别药用植物,这与我国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的研究异曲同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不仅介绍了大量药方,描述植物也多达1195种。之所以200多年后,英国能够在博物学研究方面比中国走得更远,重要因素之一或是公众的广泛参与。比如许多英国家庭曾流行在客厅摆放蕨类植物,后来又时兴摆放动物标本,再后来又热衷摆放装有海洋生物的水箱——英国人觉得把玩自然“就像把玩一件新买的玩具”。公众对自然的推崇,不知不觉中会推动博物学向前发展。
艾伦指出,英国博物学的诞生源于职业原因,甚至商业原因,而非纯粹的科学原因。并不否认,功利因素会给博物学研究带来诸多弊端,如大量挖掘矿石和植物,肆意捕捉昆虫和鸟类,超量捕猎海洋生物,但利益驱动的结果是多方面的,也会促进博物学研究装备的进步,比如地质锤、捕蝶网、水族箱的发明;比如田野调查衣着和博物箱的标准化;比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大量应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大大降低了成本,从而也大大降低了博物学研究门槛。
正如前面所述,博物学与社会的影响是相互的。博物学家最初开展田野调查全凭一副铁脚板,像麦吉利夫雷那样能行走800英里的毕竟屈指可数,更多人只能在生活周边开展研究。随着火车、汽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博物学家的脚步越走越远,协会活动也不再局限于城镇和晚上。最有意思的是,曾有段时期,受人们书写潮流影响,“一切博物学书籍或文章中都要加入一段华兹华斯的文字,这成了一项必需的义务”。至于历史上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对博物学发展的影响毋庸赘言。
当然,社会的发展进步也会给博物学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革命对矿石需求量越来越大,而“大工业扩张所推动的大规模挖掘,带来了诱人的采集化石和研究地层的机会”。及至1886年,“单是英国已知的化石物种就不下19000种”。“17世纪晚期,随着海水浴的风靡,海洋博物学似乎也变得越来越热门。”
博物学家虽不乏闪光的一面,但有时也难避世俗的侵扰。一些协会为聚拢人气,不得不以名誉领袖礼邀名人入会,有的倚靠豪门家族以扩大影响。也有一些博物学家被生计搅得心神俱疲,如19世纪30年代,由于薪资实在太低,许多博物学教授不得不靠频繁著书来安身立命。而史密斯接手林奈学会后,也曾“计划撰写一本关于地层的专著。他认为自己的数据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因而把它们当成了一个大秘密”。爱丁堡植物学会一开始就设立了一个主要目标,即“成为一个组织化的全国标本交易中心”。有些采集者则是“通过销售采集到的标本为生”。这里特别有必要提一下罗伯特·福钧,著名的植物大盗,当年正是他从中国盗走了茶叶树种。
虽然艾伦对博物学发展过程中的“商业化泛滥”不无批评,但他对博物学的社会属性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也许在他看来,博物学根本不可能置身于社会之外,当前人们唯一能做的是将学术与商业细分,让专业人做专业事,而不是像历史上那样一次次随波逐流。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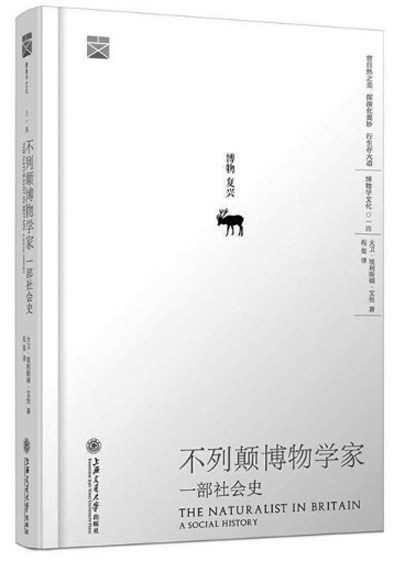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