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访谈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用这样细致的方式写京都,那就一次写足吧。写作的过程绝对很愉悦,好像神游。外面的时代变化这么急促,可是写作的时候还是要有文学该有的生长期,还是得耐下心来一字一字写出来,像在一火场里绣花。
1979年5月,从未离开过台湾的作家朱天心同姐姐朱天文和好友仙枝到京都拜访她们的老师胡兰成。虽然错过那一年的樱花季,见闻这座千年古都的风物胜迹与市井民俗,与师长朝夕相处,还是给彼时二十一岁的朱天心留下深刻印象。以此为起点,随后三十多年里她一次次重访京都。京都对她来说已超越一座异国古城、旅行故地的意义,承载着她半生的生活、写作、情感记忆乃至更深层面的精神蜕变。
从《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出版至今,朱天心已七年未有长篇小说问世。她有写作计划,始终找不到感觉,写了几万字推翻重来,关于京都的记忆却不期而至,就这样完成了《三十三年梦》。这是从叙事形式到文字内涵都个人化得近乎随性的文本,但作者所经历的时代是台湾社会发生剧变、文学艺术蓬勃纷繁的时期,加之她少年成名后成为华语文坛的重要作家,处在文学之气氤氲三代的家庭,她的书写某种程度上也是集体回忆的浓缩。三十三年梦,多少大时代下的事件发生,多少华语艺文界的重量级人物穿梭其间。
前不久,好几年没回内地的朱天心和同为作家亦是书中共游京都主要人物的爱人唐诺来到北京,在“八十年代,我们的文学回忆——《三十三年梦》北京沙龙”上与作家阿城、李锐、蒋韵老友重逢,讲述各自心中的八十年代,畅叙彼此的人生、文学交集。沙龙举行之前的那个上午,朱天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中华读书报:此前看到您接受媒体采访提到有个长篇计划,在您这样的年纪,未来可能还会不断去京都吧,是什么因由觉得是时候写下这些回忆了?
朱天心:这有个大的背景,就是你刚刚说起的,我很想写一部长篇小说。题目还没那么具体,主题大概是写“我在场的台湾五十年”,从我小时候在客家庄外公家,认识世界、有自己的意见、有话要说,到从事写作,写这五十年的情景。试着写了两个大章节,失败了。犯了初学写作者才会犯的毛病,好比开始写,人物才登场,就把自己的话“塞到”他嘴里,他变成傀儡,变成一个木偶。
我就想,何不把自己在京都、台湾几十年看到、想到、记得的一肚子话先写下来?就像打个包存放在寄物柜里,然后我才可以轻装简便地背着行囊,一瓶水、一支笔地开始写长篇。那样我就不急了,有些想说的话在这里都写出来了。除了写一次次去京都的经历,也难免写到这次去京都和那次去京都之间发生的或者自己在台北经历的事情。京都像是个舞台,我和同行的亲友在那里扮演我们的戏,可我对台下也有兴趣。
中华读书报:这么多年一次次去京都,京都是您除了台北以外最熟悉的地方,这应该有胡兰成曾在那里的缘故,但也不止如此吧?
朱天心:去了这么多次,不光因为那里是京都。我其实更喜欢伦敦,要是伦敦像京都那样离台北近,飞过去只要两小时,机票又便宜,也许这本书里写的就是伦敦了(笑)。记得去京都跟胡老师看到那么多寺庙、山门,想着日本的屏风美学大概由此而来。看到黑色山门旁开满樱花,心里就在说,等到枫树红了要再来看看什么样子,下雪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样。就这样一去再去,会觉得京都简直“鬼影重重”,像是记忆的化石层。我后来去,会像见鬼了一样看到坐在婴儿车里的盟盟(记者注:朱天心的女儿谢海盟),低头哄她的唐诺,盛年时被我“拐去”那里旅行的父母,胡兰成老师穿着长袍的身影,还有我那时的朋友们。我的很多记忆存放在那个地方,每次去就像是重温记忆现场,回忆同时涌现。
中华读书报:《三十三年梦》中对于那些京都之行的记述,很多细节、对话都具体而生动,甚至细化到出游的线路、交通工具的更换、一餐饭的食谱,您有写日记、记笔记的习惯吗?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会向其他同行的当事人求证吗?
朱天心:以前会写日记,如今连日记放在哪里都想不起来了。近十年的有些日记是找得到的,只记事情不记心情。我在写的时候,会刻意地避免去看那些日记,很任性地“迷信”——够重要的往事一定会记得,记不得的一定不重要。我放纵自己把这样的迷信当成一个回忆的过滤器。
我没有在朋友们那里求得什么记忆,他们几位都号称白痴旅行法,尤其是大春(记者注:台湾作家张大春),去了两三次都是抱着孩子,方向都搞不清,还要我们带路。有一年,我们年初去京都看樱花,年底去东京看枫红,结果被他混得一塌糊涂。
中华读书报:作家杨照在《说吧,追求“自由”的记忆!》一文中,针对您在这本书中的记忆书写,感慨记忆并非受人主观控制,“要记得虽难,要遗忘其实更难”,这也从某个角度验证了您对书写记忆的心态。
朱天心:是的。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用这样细致的方式写京都,那就一次写足吧。写作的过程绝对很愉悦,好像神游,想起每一次去京都时是怎么样的,什么季节,甚至会记得第二天去了哪里。我们很像朝圣者,每次去的路线常常重复,我甚至给有些路线取了名字,A路B路什么的。写的时候,有些重复的部分就舍弃掉了。
中华读书报:你在书里写到的那些人物,很多都是今天华人文学、艺术界的“大人物”,张大春、侯孝贤、阿城、蔡琴……感觉写得还是很直率的,有些部分在动笔时会不会有些顾虑?
朱天心:完全没有顾虑。我受不了为什么有些人私底下可以月旦人物到这种地步,当面还是你好我好?毕竟他也是公众人物,公开说一套,私底下做的事那么断裂。这样写,我很缺乏小说家的世故吧?记得这些文字在《印刻》(记者注:《印刻文学生活志》,台湾文学杂志)连载时,初安民(记者注:《印刻》总编辑)就说,天心啊你写这些会惹祸哟。我就是想做一次《国王的新衣》里那个小孩吧。
中华读书报:书中回忆的章节是按时间排序的,但具体到一个章节中的讲述往往插入更多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回忆,有些随性的跳脱,为什么采用这样的叙事方式?
朱天心:我写作的时候,最初的文字跟最终定稿之间不会有太多修改,主要是誊抄。应该这么说吧,这样写是为了野放自己的记忆。行文到这里,想起什么就写什么,并不是精心的设计和炫技。
中华读书报:书中引用了朱天文纪念父亲的一段文字,那里提到了“供养人”这个概念。胡兰成以及您的父亲对包括你们姐妹在内的后辈多有生活和写作上的帮助和扶掖,他们是作家,也是文学的“供养人”。
朱天心:父亲在抗战末期迁校数次,包里一直放着一本张爱玲的《传奇》。张爱玲曾经写到他,“你就是沈从文笔下那个最好的小兵”。那时父亲已经在写作,后来他总是感慨,要是那个时候有文学前辈点拨他一下,写作上会少走多少冤枉路啊。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帮助了很多学生。后来碰到那些学生,很多会说,哦,我在你们家吃过饭,因为我买书把钱花光了。我常冷眼看他们,觉得很多人没存着真正追求文学的心,根本就是来吃饭,有些是凑热闹,有些甚至是来追天文……有时我会跟爸爸说,你的时间也很有限啊。他总是会说,我年轻时,要是有人帮助,会有多大不同,所以我现在帮助他们,是同样的心情。
中华读书报:京都虽好,从您的书里也还是能读出对时间流逝物是人非的一些感触,那些你熟悉、喜欢的路径、林木、寺庙或者小店,有些也在消逝或改变。由此不禁想到您近年来表达过一些对于写作、文学的看法。写作这个行当,文学这个领域,在今天的处境似乎也是时势所趋、不可阻挡?
朱天心:是的,以前文学要担负的东西太多了。现在网路这么发达,娱乐或者远方有趣的事情——比如你的朋友在撒哈拉沙漠看狐猴,你很容易分享,又何须再
去读三毛笔下的撒哈拉呢。今天有太多方式能够分担文学的功能,这也不是坏事,也许文学的萧条会使得更纯粹的创作者留下来。
中华读书报:读到这本书的尾声,发现越到后面的章节记录去京都的时间离现在越近,文字篇幅反而越短,倒数第二次京都之行不过写了一两页,最后一次更是不着一字,为什么这么安排?
朱天心:“老人家”对过往记忆要比新鲜的记忆记得更清楚啊。另外,最初那几次去京都,很多地方都是第一次看到,感受非常强烈。到后来,比如清水寺,看过好多次,写一次就好了。除非它有变动,被拆或是天际线被破坏,才可能再去写。这本书后来的章节篇幅越来越短,也是这样的考虑。到最后戛然而止,我是把责任交给读者,读了这本书你们想必知道去京都怎么玩了吧?大概有一点这样的心情。
中华读书报:你在书末和作家蔡逸君的答问中,提到写作“像在一火场里绣花”,这个比喻很妙,但又很难具体阐释。
朱天心:我三十几岁时,正好是台湾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但我会觉得,天大的了不起的主张,也不可能凌驾在我的文学之上。外面的时代变化这么急促,可是写作的时候还是要有文学该有的生长期,还是得耐下心来一字一字写出来,像在一火场里绣花。
中华读书报:您的父母、姐妹、爱人都是很好的作家、翻译家,孩子也从事写作,难怪阿城觉得你们家人这样的情形世间罕有。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身份带给写作的影响?
朱天心:父母的初心到底是不是希望我们将来继承他们的衣钵从事写作?这个我不知道。可是我很确定他们非常希望我们成为有文学鉴赏力的好读者,可以一辈子手不释卷,文学的世界好大好大。所以,从我有记忆起,他们很小的书房对我们姐妹是完全开放的。记得我十二岁时读《洛丽塔》,心里暗想,将来一定要写一本属于我的《洛丽塔》。那时可能他们也在偷偷摇头叹息吧,但不会阻止我。我们很自然地摸索着阅读,我和天文喜欢读的书不同,读某一本书的时间也不同,所以我们的生命样态非常不一样,后来我们很自然地从事写作。我觉得,父母当初但凡有一点暗示,哦,将来写东西吧,我可能就什么都去做,只有写作绝对不会去做。等到我开始写作,看到他们开心才明白。
中华读书报:写作过程是近乎孤独的个体行为,而社会运动往往需要集体的力量。您在写作之外也是台湾一些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您如何理解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朱天心:文学创作是有一定酝酿期的。你想写一个题材,酝酿的时间长则十几二十年,短也要两三年。要用文学介入或改变现实,可能时代都变了,想想就好急哟。作为公民,还是立即去做些什么吧。有些朋友会说,你参与社会运动是不是为了搜集写作题材?我说,不用这样吧,那对你关注的对象是不尊重和不公平的。最好的状态是互相深化,文学的养成可以帮助你做社会运动,参与社会运动也可以帮助文学的丰富。从事文学和参加社会运动是完全相反的事情。做运动,语言要简单,要说得大声,不然群众听不懂。可是文学,怎么复杂怎么去写,人家遗忘和没注意到的记忆你才去捕捉。我对此很苦恼,到现在也难找到很好的平衡方法。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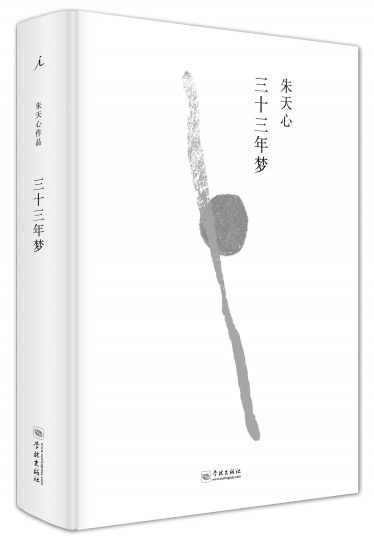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