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是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刘泽华先生的回忆录。作者忆往抚今意在说明,一位颇具典型化的学人,是如何经过深刻的文化反思而走上文化自觉之路的。
土窝窝里的“学前教育”
时下人们把学前教育看得极重要,不惜重金请家教或上各种各样的学前班,以求孩子的智能大放异彩。我每每感叹,真是时代不同了!我的学前教育,则是在泥窝窝和庄稼地里进行的。我能搜索到的学前记忆就是,捉蝈蝈,掏鸟窝,捅马蜂窝,舔蜜蜂的尾巴找蜜吃,和小伙伴之间“打仗”,还有浇地时看水畦以及同小毛驴一起拉水车等,与时下“赢在起跑线上”的学前教育全无关系。
中秋时节是蝈蝈最为活跃的时候,金黄的大地被蝈蝈的大合唱震得发颤,这是小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捉蝈蝈不是一件伸手可得的事,要沉稳、机灵、有耐心,还要不怕热。初学时,几乎是每战必败。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逐渐掌握技巧。相比之下,在学习上绝没有那样的耐心和毅力。如果学习也能像捕蝈蝈那样投入,门门功课肯定都会得一百分。小虫的叫声连成一片,你必须像乐队指挥分辨每位演奏者的音阶那样,确定蝈蝈的位置。行动时要猫着腰,蹑手蹑脚,轻如微风,到大庄稼地里,顺着声音寻觅爱唱歌的小虫。这时的庄稼都接近成熟期,枝叶变得粗硬尖利,有点像刀子、钉子。尤其是谷子地和玉米地,进去后常把皮肤划得竖一道横一道的血痕,好像披着一个网,红红的,连成一片,酷似动画片里的蜘蛛侠。中秋的骄阳似火,炙烤得浑身冒油。此时要我干农活,一定会发出怨言或磨磨蹭蹭以示抗议,可是要捉蝈蝈,这些全都不在乎。捉之前,首先要学会用高粱秸秆和麦秸编成蝈蝈笼子。这是一种很巧的手工活儿,开始编得很粗糙、简单,后来就能编成各式各样的笼子,有的像房子,有的像飞机,有的像首饰盒。还有用高粱秆皮编成圆形的小笼子,到了天冷的时候,把蝈蝈放在里边,可以揣在怀里保暖。蝈蝈有时可以活很长时间,直到春节。小东西不时地高唱,这就是我们能享受的最优雅的乐曲。
小孩子们能喂养的鸟主要是麻雀,也有玩鸽子的。我只有喂小麻雀的经验。我们常掏麻雀蛋,美餐一顿。麻雀妈妈会围着我们叫个不停,有时还会被啄一口,挺疼的。刚孵出的小麻雀很难成活,必须捉快会飞的小麻雀,然后是喂养,要给它捉小虫,喂水,清理粪便。开始它常会罢食,要耐心等待。熟悉之后彼此就会成为朋友,它看到小虫便张着嘴,振翅扑来。随着时间的延长,它的依赖性就更大,待到它会飞时,多半也不飞走,往往在天空中转一个圈,又会飞回来落在肩上,此时是最开心的时刻。养小麻雀很费功夫,要有耐心,成功了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马蜂蜇人,很招人讨厌。家里房檐下常常有马蜂窝,我最爱捅马蜂窝,这既需要野气,又要有点勇气才行,不怕挨蜇。有一次捅后跑慢了一步,一群马蜂追来,把我横蜇一通,我的脸就像面包一样鼓起来,全脸通红发紫,眼睛肿得只留下一条细缝,疼痛过度,倒只剩下发烧的感觉,过了好几天才渐渐消肿。后来又学会了火烧马蜂窝,在一根竹竿的一头绑上蘸油的棉花,点着之后,戴上草帽,快速伸向马蜂窝,马蜂的翅膀一下子就烧掉了,落在地上的马蜂,若没有死,稍后再用火烧死。火烧马蜂窝,其实很危险,弄不好会引起火灾,大人们一般不让我们这样玩,发现后免不了一顿臭揍。
小时只听说蜜很甜,大约七八岁时,突然想到蜜蜂采蜜,便以为蜜蜂身上的花粉就是蜜。那时正是玉米开花的时候,蜜蜂到处可见。虽知道蜜蜂也会蜇人,但与马蜂不太一样,没有那么疼,于是我就跑到玉米地中间,用手抓蜜蜂,快速把蜂针揪掉,用舌头舔蜜蜂身上的花粉,竟没有得到甜味,有点扫兴。有一次蜜蜂针没有揪掉,用舌头舔时,正好蜇了舌头,我疼得大哭起来,七十年过去了,记忆犹新。
儿童之间玩打仗,是冬天夜里最有挑战性、多少有点危险的游戏。我们村不到六七十户,分两条街,名“前街”、“后街”,我家在后街,只有二十几户。同龄的孩子有近二十个,我们组成一队与前街的对抗,相隔一条道和一个水坑,互相投掷土块和碎砖块,还有用弹弓射击,或投掷沙袋等。这玩打仗,竟也有一套战术,包括潜伏、藏身、卧倒、诱敌等等。瞄准对方互相投掷,有时会打得鼻青脸肿。那时候都没有钟表,也不知时间长短,估计每一仗会持续两三个小时。大家奔跑不止,浑身大汗的同时是高度的兴奋,大人们三呼四唤,才很不情愿地休战。
春天一过,就甩掉鞋子,光脚板走路。而夏天,在我记忆中,总是一丝不挂、浑身光溜地满街跑。村边有个浑水池塘,回想起来,其污染程度应该在今天的“红色警告”级别以上。雨后村中流出的水汇集在池塘,妇女们先在这里洗各种衣物,包括婴儿的尿布,然后再回去用井水漂洗一遍,一群孩子则在其中戏水。这一切都很自然,既没有卫生的概念,也没有害羞的意识。这是我最早也是最快活的游泳经历。
从我有记忆起,就与劳动为伴。大人们拔草,孩子们也必须跟着拔,在拔草中逐渐就分清了苗和草的区别。我们那里用井水灌溉,用牲口拉水车,我们家有个小毛驴,力量有限,要人助拉,大人们给我也做个套,与驴并肩拉水车。这是我最不愿干的事,倒不是怕出力,实在是枯燥无味。家里的零碎活更多,诸如扫地、抱柴火、清理牲口圈等等,数不胜数,从无闲时。
我们家几乎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压根儿就不会有人教识字,我口头数数大概也不会过百。
对我来说,所谓的学前教育,就是土窝窝里的摸爬滚打。
难忘师生情
一九四七年初春,开学不久,战争的烽火烧到了宁静的校园。学校关闭,我失学了,刚过十二岁生日。我到哪里去?到处都是硝烟,我只能回到自家的土地上,开始了两年的务农生活。
农活对我并不陌生,庄稼和农活就是我的记忆史。我们家的田里有一个窝棚,从麦收前一直到秋收完毕,几乎日夜有人守在窝棚和临时谷场里(麦收和秋收时临时平整一块场地,堆放收割的庄稼并进行脱粒等)。从记事起,我最高兴的事之一,就是跟着舅舅和哥哥住在窝铺和草棚里。因为是在野外,比家里要凉爽。更有吸引力的是可以吃青。比如青豆灌满浆,还没有长硬时,自家人也不能随便摘,但在地里看青的人可以例外;红薯长到能吃的时候,也可以吃鲜;还有玉米等。从有记忆开始,就要做力所能及的一些农活,如跟着大人去拔草、看水畦、送饭,播种之后赶鸟,天旱时日夜浇地,帮助牲口拉套和赶牲口(不要让牲口停下来怠工)等等。
过去是假期和课间帮家里干活,现在则成了全职农民。一九四八年,我的四个哥哥都出去谋生了,在我家多年的舅舅因是贫农,回到他自己的家。我虽只有十三周岁,但个子比一般孩子高,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开始学习和独立操作同龄孩子们所不能做的农活,比如赶车、使唤牲口和耕(读音“经”)、耩、犁、耙等,我都能上手。土改之后,分给我们家大毛驴,虽不如骡子,但也很好使唤,经常出车去拉公粮,既有服役性质,也有一点报酬。我整日赶着驴车,奔波在路上,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是不多见的。我很为自己的能干而得意。我与这头毛驴形成互为主仆的关系,干活时它听我使唤,虽然也手持一鞭,但从来没有打过它;等下了套,我对它悉心喂养,每过几天,总会用刷子梳理它的毛发,此时它纹丝不动,大概是一种享受吧。
农活中间的空隙,我便读武侠小说,如《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大八义》《小五义》等。文字上尽管还有障碍,有些地方看不大懂,但能明白大意。受武侠的影响,我成了武术谜,和几位同龄伙伴到临近十里铺村拜一位教头为师,每天晚上去学武。开始不让摸刀枪棍棒,只学武术的基本动作,先练腿上功夫,光骑马蹲裆式就练了数月之久。开始两腿酸疼得连路都难走,几个月之后,我能纹丝不动蹲很长时间也不感到累。那个时候没有钟表,具体蹲了多长时间也不清楚,估摸约有个把小时,真是实功夫。其后又练劈叉、踢腿等,大概持续一年多,直到一九四八年冬天我去上补习班才中断。
两年的时间就是干农活,读武侠小说、习武,学业上的事,没有用一点点心思。我四哥随着晋绥干部学校到山西临汾去了,他来信能看,回信就难了。记得有一次我急得满头大汗,横竖写不出来,娘在旁边抱怨我窝囊,上了快五年学,竟连个信也写不成。我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偶尔也会想今后向哪里去,不能一辈子务农吧。
一九四八年初夏,几位小伙伴心血来潮,临时相约去投考正定中学,考前没有任何准备,就莽莽撞撞去了。第一门考算术,一岀考场,我就嚷嚷不考了,因为一道题也没有做对,再接着考没有意义。没有想到其他几位也有同感,说明他们也考得一塌糊涂。这次考试给我极大打击,对考中学完全失去了信心和追求。去正定县城要过滹沱河,滹沱河是一条漫无边际的沙河,雨季时汪洋一片,浩渺无边,干旱期几近断流。时在雨季前期,已有点水势,为了考试我们不敢冒险,渡船而过;回程时变得胆大无惧,几个人赤条条闯了过去,泅水时还喝了几口水,有惊无险,总算平安过了河。我由此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学会审时度势。
干农活的确很苦,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也没有任何人给予指点,最多我娘说,再过几年,你也出去谋个事吧。谋什么事,天晓得,眼下只有老老实实务农。
常说天无绝人之路,说不清什么时候就会遇到一个机会。一九四八年秋收之后,一个非常偶然的巧合,在我家门口遇到老同学王新长。王新长是我原来的班长,比我大三岁,学习总在前三名,我特佩服他。我是插班生,那时欺生现象很常见,每遇到挨欺负,王新长总会出来制止,我打心眼里感激他。一晃两年不见,他告诉我,学校为五、六年级举办了补习班并动员我去。上学有极大的吸引力,可我担心我家是被斗的富农,学校不收,王新长安慰说不会受影响。回到家里同我娘商量,她立刻表示支持。第二天我就去学校顺利上了补习班,人不多,大约有二十多人,班长依然是王新长。
学校停办了一年多,补习班是复校前临时加的一个班。开始还有点害怕,没过几天,便有一种被吸引住了的感觉。印象最深的是“师生打成一片”。我不明白什么叫师生打成一片,怎么能打成一片?时间不长,便体会到老师对学生很尊重,不打不骂,课教得非常认真。课外,老师常到学生中来,耐心辅导,教我们唱歌,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体育活动,有时还聊天、说故事,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同过去老师的严厉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我也打消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
补习生大多住校,当时没有炊事员,全靠自己动手,大家轮流做饭。每人每月交三十斤小米,也可以拿五斤红薯顶一斤小米。大家都不会做饭,常常做糊,时硬时软。菜就是腌菜。伙食虽然很单调,但每天能吃上一顿真正的粮食,比家里强多了,和同学们在一起相处也很愉快。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遇到许多好心人给我以极大的帮助。前边说到的王新长是其中之一,补习班里教我们算术的冯老师是另一位。辍学两年后,我连普通的“四则”题也忘了,属于最差的学生之一。冯老师的丈夫去世了,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不容易,但她对所有的学生都充满了爱心,对我这样的差等生也极其耐心,课后常单独给我补习。以前上学,我多半是甲等之末、乙等之首,因有秃疮,常被同学耻笑,很是自卑,抬不起头来。后来读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读到阿Q护秃疮一段,我很有感触。先前的老师,对我从没有特殊关心过,现在也记不起任何一位老师的模样,而冯老师对我的关心,则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有一次发烧躺在宿舍里,冯老师来看我,摸摸我的头,给我端来一碗热水(学生没有热水喝)。时至今日,忆起此情此景,我仍有一种深深的感动。补习了两个月,我的算术竟然考得了八十多分。更让我难忘的是冯老师的评语给予我的鼓励。大部分的内容已经忘了,但有四个字我至今记得。冯老师一是说我“用功”,二是说我有“智慧”。当时我不懂“智慧”为何意,问了冯老师后才知道。在以后的时间里,我慢慢悟到,我的“智慧”就在于“用功”。
一九四八年冬季的补习,对我一生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没有这次补习,我根本不可能再有上学的机会。而没有冯老师耐心的辅导,我的成绩也很难赶上来,更不可能考上中学。我上中学后,曾回校看望老师,主要是想看望冯老师,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听同学说,她调到别的学校去了。再后来,又听到让我异常悲伤的消息,冯老师患病已离开了人世。
六十多年过去了,冯老师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矮小而瘦弱的身材,几分饥黄的面容,清晰温暖的话语,包蕴着母爱的温情,还有一丝不苟的耐心。如今我年届八旬,每回想起冯老师,依然有说不尽的感激。我只能在心中供上一炷香,愿冯老师的在天之灵安宁、祥和。
学术“三个一”
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六这两年,学校兴起创收热潮。文科中文系创收最为突出,当时教师工资一般都在七八十元,他们的创收差不多能翻番。校长多次在会议上表扬中文系,并点名历史系落后了。我认真思索这个问题,创收是历史系的生命线,还是学术是生命线?熊掌和鱼,两者是否能兼得?
历史系也不是没有一点创收,当时办进修班、硕士生班、在职硕士生班,也有一些收入。投入的力量已经很大,如果再扩大,势必会影响教学与科研,特别是研究很难进展。我考虑的一个问题很简单,时间是个常数,用于这方面就会影响另一面;从长远来说,学术是历史系的生命线,如果学术上不去,终究要落后,甚至垮下来。但创收的风吹得很盛,我也难以简单站在对立面。基于上述两点,我提出,愿意搞创收的,可以多分成,但下一轮职称晋升,创收不算数;职称晋升主要看研究成果和教学效果,请诸位自己选择在哪方面下功夫。我的用意是希望同仁们能排除干扰,潜心从事教学和研究。我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相对多些,根据自身的经验,稿酬虽然有限,但也能有所补益。系里有一点点小收入,为鼓励同仁发表论文,我决定将这点钱主要用于鼓励研究和发表论文。针对当时情况,我提出要力争“三个一”,即一门课、一本书和一门外语(这主要针对年轻人)。
提出“一门课”,主要是针对选修课太少,几门基础课占用了多半学时,学生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教师们也都盯着几门基础课,整个系的学术空间很窄。我提出,副教授必须开一门选修课,讲师也可以开设;要求每门课都有自己的特点。相应地,教学计划进行了较大调整,压缩基础课时,增加选修课。在短短一两年内,历史系就开设了二十多门选修课,只要有五位学生选修就行。这一改,大大改变了历史系的课程结构。对老师来讲,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或培养自己的长处;对同学来讲,扩大了知识的眼界和自由度。
“一本书”是针对当时有一本学术著作的人很少。此前的大环境,不停地大批判,文祸频生,使人慑于笔耕。“文革”后,环境虽有很大变化,但著文是个积累的过程,所以,八十年代中期,不要说青年,就是中年这一层,有几篇文章的教师也不多,有著作者更是寥寥无几。在我看来,新时期没有几篇有系统的文章或著作,怎么能当教授?从历史上看,多数的学者都是靠著作支撑的。就南开历史系的情况而言,缺少著作和大块文章,是致命的弱点。与其他著名院校历史学科相比,我们的缺陷就更为突出。我强调“一本书”(包括大块文章),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
我之所以强调一门外语,是与北大历史系比较,我们的语种少,水平又不高。当时只有英语、日语、俄语、朝鲜语,全系能进行学术口译的只有几个人,其他语种基本没有。对一个学科来说,语种显然太少,离整体性的高水平也显然有距离。我鼓励要有人学德语、法语,还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等。我多次强调,如果我们有七八种语言,能“四会”,整体水平就能提高一大块。为提高教师的外语水平,特别开设了提高班;有的教师去学习某种少数民族语言,也大力支持。为此,系财务也给予一定数额的学习费用。
提出“三个一”的目的,是鼓励潜心做学问。我反复强调,从长远看,谁在学术上积累多一些,谁的日子就好过一些;今后的职称晋升,主要看教学与研究成果,而这些都不是能临时凑出来的,临时抱佛脚无用;用更多的精力搞创收,可解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但无补于今后的职称晋升;如果有人不看重今后的职称晋升,那是你的选择。还有,只要不用历史系的名义,收入全归自己;如果用历史系名义,动用人员不多,创收大头,也归创收者。把事情都讲清楚,今后谁都不要后悔,不要抱怨。
这样一说,绝大多数教师心静下来了,沉心于学问。提出“三个一”,端正了方向。提出“三个一”,也与八五年大面积的职称晋升有很大关系。我接手系主任后,冻结三年多的职称晋升解冻了。有十几位教龄近三十年的教师,面临晋升副教授问题。他们多是五十岁上下,与我同龄。三十年里,他们响应号召,参加数不清的各种运动,最后又卷入“文革”,以致下放劳动。面对晋升副教授,他们既缺乏论著,教学也不多。既然是晋升,不能不考虑专业水平,但更沉重的是“人道”问题。我只能绞尽脑汁,向校方要求增加名额。我的确想出了好几种鬼主意,迫使校方不得不给我们增加名额。主管副校长拿出各系晋升比例表让我看,他说,你们的副教授晋升比例,比其他系科高一倍还多,叫我怎么应付别的系的攀比呢?我据理力争说,我们是老系科,积压的人才多,晋升之后,可以输出。就这样费尽心机,还是有几位没能如愿晋升。面对他们老泪纵横,我也感到十分沉重和无奈,觉得对不起几位同龄人。由此,我想到只有提出“三个一”之类的要求,以后的职称晋升才有所遵循。
用收藏诠释思想
收藏古董,也许说不上,我只是偶尔玩玩。玩古董,一般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有闲;三是有趣。说到钱,在只靠工资吃饭的时候,我每时每刻都是紧巴巴的,就这一点而言,再便宜的东西,也不能问津。八十年代,有了稿费,日子多少有些宽松,但主要是用来买书,我还无力他顾。另外,那正是我当红的时候,每天人来人往,日程排得满满的,写文章无时无休,即使有点闲心,也无闲时。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不能说对古器物一点兴趣也没有,但由于钱紧和无闲,只能搁置,还排不上日程。
人总是要找一点兴趣,放松一下精神,于是想到了古玩。玩什么呢?一辈子缺钱,就玩钱吧!其实还是有业务目的的。过去讲历史对金融涉及的极少,现代的生活告诉我们,金融是社会的血脉。中国古代的商业与交换相当活跃,金融也相当活跃。别的不说,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提出以商治国,这在《管子》一书中的《轻重篇》中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作者提出,国家只要操纵货币,玩尽“轻重”之术(即回笼与发放货币),即使免除税收,国可安,君可富。我对《管子》中的《轻重篇》特别留意,在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时,专立了一章,讲如何操纵物价和垄断货币以求大利。可是,我对当时的货币知之甚少。
九十年代初,天津市沈阳道古物市场,还不容许进行公开的古钱买卖,卖主怕抓住挨罚,不敢把古钱放在明处。每问有否古钱,他们多半要瞟视周围,看有否稽查。因此,成交时,多半是在匆匆忙忙中进行的,好像做贼似的。后来放开了,再也没人干涉,于是满街都是古钱。我开始阅读有关古钱的各种书籍,学校图书馆的有关藏书,几乎被我翻遍,相关文章也读了许多,增长了不少知识。在收集过程中,我逐渐把目标集中在“半两”和“王莽钱”上。说起来,我还真有若干枚颇为珍贵的品种。我没有去过专门的古币市场,在杂摊上要想找到珍品,实在极难,像沙里淘金。如果摊贩略懂古币,他会把稀见品挑出来,单独要价;如果不懂,一大堆钱混在一起,你只能一一挑选,很费功夫。有些摊贩不卖挑,你若挑,他先提价,比如按堆、按串卖,一枚一元;要挑,可能一枚两元或更多。有一次,我在一大串钱中发现一枚铁质“大泉五十”,我不露声色,按事前说好的价钱付费。我付费之后,摊主发现卖漏了,发出嘘唏声,显得后悔不已。又一次,我在一个摊位上以极便宜的价格,淘得一枚“王莽十布”中的“中布六百”。当我又一次去逛市场时,摊主看到我,叫苦不迭,不停地说:“卖错了,卖错了,赔大了!”我也笑答:“对不起,我也上过不少当。”记者刘武曾写过一文《教授与钱》,写的是我,颇风趣。
我大约玩了两年钱,便改玩铜镜。铜镜是青铜大器之后青铜器新的高峰,含有丰富的科技和文化内容,另一层意思是自己也照照镜子。当然也是先读书,随后买了几面,细细品味纹饰、铜质、铜锈、品相特点等等。玩铜镜的弯路,比玩古币要少些,一开始就瞄准先秦与秦汉时期的。过了一段时间,感到这样收藏,有些底气不足。铜镜的价位,当时虽然不太高,但一面有点品相的,也要上百元或几百元。一般玩古玩的人,有进有出,以玩养玩。我呢,只有进没有出,自然没有后劲。于是,我进一步调整收藏路数,把目光集中在目前著录中不见或少见的纹饰上,这要求我要非常熟悉著录情况,而且要印在脑子里,在市场上的一瞬间能做出判断。说实在的,做到这一步谈何容易,因为我的记忆力不太好,即使看过图录,过后多半就忘了。
由于财力限制,我收集的镜子,从数量上说不算多,但有些纹饰是著录中所未见的,可谓孤品或罕见品。李学勤先生曾多次鉴赏过我的藏品,有一面西汉的草叶兽纹镜,他曾著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纹饰属匠心之作,美轮无比,实属罕见。有此一面,我心已足矣!
我收藏的铜镜,尽管品相大多一般,也不是大型的,可多数的纹饰都有特色,在考古上有相当的价值。收藏的数量也有限,但唐以前各个时期的都有,也算成系列。唐以后的,也有几面别品,其中有一面“大宣年制”,我没有查到中国历史上有“大宣”年号,包括农民起义年号和周边国家的年号。是不是宗教的?另立年号,是绝对要杀头的!这是一个“谜”,有待破解。还有吴三桂的“昭武通宝”镜,也是少见的。
跑到市场,常常不能遵守自定的收藏范围,看到一些自以为合意的,我便顺手购入,颇为杂乱。比如,我收藏了一批地契和文书。其中有辛亥革命太原起义的《子夜宣言》,可谓孤品,至少是二级文物。历史系王先明教授专文评述了《子夜宣言》的历史价值。有雍正时期户部出售的“监生文凭”(交一百两银子);有清代的“典卖人契”;有“乡试试卷”,“殿试试卷”故宫很多,但地方性乡试试卷很难得;有清后期的“合会”契约、民间融资契约,也不多见;有清后期中等人家的“析产契”,也很少见;有康熙以下历朝,以迄五十年代初各个不同时期的“地契”,虽缺少洪宪期间的正式“契约”,但有洪宪时的契纸,为民国所用,很是奇特。有若干份“地契”表明的税收量,“斗”之下依次竟达十位数,以“粒”计,出奇精细。另外,还有几片“贝叶经”,偶然得之,自己无法鉴定。
我还收有一些别的有意思的小东西。我是闲来乱玩,但这点小东西都有相当的文化意义,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已表示,在适当的时候,捐赠给南开大学博物馆。来自社会,回归社会吧。
(本文摘自《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刘泽华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7年1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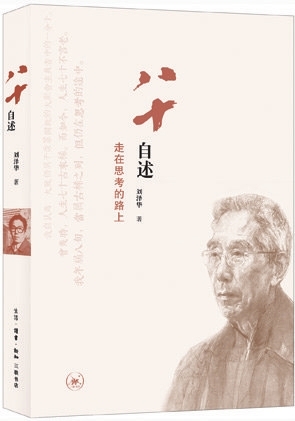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