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很热。
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一些知名学者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一批冠名“中国”的论著。其中,许宏、何驽、韩建业、李新伟、李零等考古学背景出身的学者的讨论颇引人注目。继“文明”“文化”“文明标准”“国家”等概念的讨论热潮之后,“中国”成为新的的热点,这与21世纪以来中国文明探源研究注重整合与总结的特点息息相关。这也正呼应了张光直先生在《论中国文明起源》中的设想:“谈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说,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论证何为“中国”,所设定的倾听对象不独限于国人,更在于世界。
正如韩建业先生在《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一词在研究早期中国的论著中习见,但学者对其涵义及演变却鲜有措意。韩先生试图从考古学文化、古史传说、人地关系等角度全面考察“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并认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要追溯到“庙底沟时代”(公元前4000年前后)。与此不同,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先生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公元前1750年~前1520年),在其《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三联书店2014年版)中多有阐发。而陶寺考古队队长何驽先生则认为陶寺才是“最早的中国”(公元前2300~前1800年)。李零先生强调“中国”的成立,不但有“中”而且要有“国”。按此标准,将“中国”追溯到“龙山时代”的陶寺,或许更近事实。
韩建业、李新伟两位先生更注重“中国”形成的历史背景。李新伟先生近来在《文物》《考古》《光明日报》《读书》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试图以“上层远距离交流网”说明新石器时代精神文化的交流现象。李先生这方面的认识,要追溯到他2004年发表的《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一文,在此前后刘国祥等先生也提出过类似看法。李先生从人类学的线索出发,试图以社会上层的亲身旅行说明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等文化之间的远距离交流,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探索。
李新伟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新石器时代不同区系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同”,也强调“上层”的特殊意义。“同”可能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这也是传播论者最热衷解释的途径。但“同”未必说明一定存在文化的传播现象,平行比较也是一个思考的角度。至于“上层”,强调“大传统”与精神文化,跳出了考古学研究所倚重的一般陶器,这确是我们思考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思考维度。
在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时间与空间的因素。如果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似因素出现有先后,那么结合其他文化交流的线索则可以大致推定谁传给谁的关系。而若时代相当,文化交流的线索又不清晰,那么孰先孰后、孰为源头便难以遽断。至于空间的关系,则涉及地理背景。无论是许宏先生的《何以中国》、韩建业先生的《早期中国》,还是李零先生最近的《我们的中国》,在讨论“中国”时均极强调地理的因素。笔者一直以来极关注“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研究进展,发现李新伟先生指出的典型远距离交流现象,大多分布于从长江沿线至东部沿海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一空间特点值得重视。近来在《我们的中国》中读到李零先生明确提出中国有两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大受鼓舞,以下试作阐论。
我们知道,童恩正先生——这位才华横溢的考古学家兼科幻作家,曾在《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中提出著名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道传播带,实际上由长城地带和藏彝走廊两部分组成,笔者拟称为“长城-藏彝”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而另一道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论者则关注不足。李零先生在《茫茫禹迹·两次大一统》中指出:
童恩正讲,中国大地,从东北到西南,有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是讲中国的西北和西南,即中国的高地。其实,中国的沿海,也是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同样值得重视。
两个半月形地带:高地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戎、狄文化;沿海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夷、越文化。北中国海,渤海和东海,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是夷的天下;南中国海,黄海和南海,从浙江到越南,是越的天下。
这两条弧线,画出个大圆,中间是中国的核心区。天下辐辏,各种族群都往里跑,有如漩涡,有些被吸进去,有些被甩出来。吸进去,变成华夏;甩出来,变成蛮夷。(第23—24页)
李零先生所说的沿海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以海岸线为根据,笔者则强调“长江-沿海”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与李先生的理解不尽相同。正如李先生所言,这两道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以地形为基础的。而以地形为基础,实际上又可区分出族群结构、生活方式、交通形式等方面的差异。“长城-藏彝”传播带自中国东北沿着长城地带延伸向藏彝走廊,分布着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的各族群,面向欧亚草原的宏阔空间,是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长江-沿海”传播带自长江沿线延伸至东部沿海,以水路交通为主,分布着苗瑶语系、壮侗语系的各族群,则面向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的广袤天地。
不少前辈时贤已经注意到早期中国文化二分或三分的现象,如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苏秉琦先生“面向内陆”“面向海洋”两大板块说,严文明先生的鼎文化区、鬲文化区、筒形罐文化区三大文化区,以及韩建业先生的东方、中原、北方三模式。
笔者并不希望以文化圈、文化区之类的概念以及机械、单线的传播论来讨论史前的文化交流,而试图以地理为基础,从两大文化传播带的互动与辐射出发勾勒出更为立体的文化交流图景,强调传播带所奠基的文化底层。两大传播带有两个交汇点,一在东北,这一区域的史前文化与族群结构兼有两大传播带的特点;一在西南,这一区域的文化与族群结构至今仍有很深的两大传播带相交融的烙印。两大传播带各自向外辐射,一者面向内陆与草原,一者面向海洋,分别奠定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它们又同时影响中原,两大传播带所闭合的空间便是中原地区,即狭义的“中国”。
“长城-藏彝”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已有不少学者讨论,以下试结合近年来分子人类学、考古学等方面的新认识,重点讨论“长江-沿海”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就族群结构而言,“长江-沿海”传播带影响的人群主要有苗瑶语系、壮侗语系的族群。苗瑶语系的族群源自古代的苗蛮集团,在今天则体现为苗、瑶、畬诸族,他们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壮侗语系的族群源自古代的百越集团,在今天则体现为壮、侗、傣、黎、水诸族。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百越集团的Y染色体DNA单倍型以O1-M119为特征,具有这一遗传特征的人群,孕育于华南的北部湾地区,后来沿海岸线北上扩张至江浙、山东、东北。东部沿海的先民,既包括越,也包括夷,夷、越有密切的联系,可以统称为“夷越”。环太平洋地区南岛语系的族群,与壮侗语系的族群亦有同源性,除了遗传学的线索,尚有语言学、考古学的佐证。玉器、有段石锛、文身、鸟图腾崇拜、人工拔牙、枕骨变形、口含石球等特征,见诸夷越族群乃至环太平洋的南岛语系族群。壮侗语系、南岛语系的族群,又可以统称为“澳泰族群”,这方面,生命科学领域的李辉等先生已经从遗传学的角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长江-沿海”传播带所辐射的范围,相当于苏秉琦先生所称的“面向海洋”板块,亦大致相当于严文明先生所称的鼎文化区、韩建业先生所称的东方模式。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于华南、浙北、华北、东北,主要在“长江-沿海”传播带的辐射范围。而“长城-藏彝”传播带的新石器文化则起步较迟,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延续了较长时间。作为新石器文化的重要标志,陶器最早出现于华南,其他区域的陶器出现稍晚,并且有受华南陶器影响的迹象。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浙北的上山文化与东北的双塔一期文化均出现豆类圈足器,颇耐人寻味。李新伟先生所揭示的长江下游与东北的远距离交流,可能要追溯到约万年以前。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或存在这样的线索:发轫于华南,随后向北扩散至东部沿海、中原乃至东北。这与分子人类学所揭示的O1-M119人群的迁徙路径有相合之处。活跃于江畔海滨的夷越先民或许相对早慧,他们的辛勤创造奠定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基础。
“长江-沿海”传播带以长江下游为节点,可以大致分为长江沿线与东部沿海两部分。该传播带的文化交流,韩建业先生在《早期中国》中已有不少涉及。新石器时代中期以降,长江沿线的文化交流愈趋密切。长江中游至下游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有一致的生产基础。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独木舟(距今七八千年),类似的遗物在长江下游多有出土,是为先民扬帆江海的交通工具。跨湖桥文化的产生,受到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跨湖桥文化也影响了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皂市下层文化。长江中下游至华南地区逐步整合为“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除了长江中游、下游有持续的文化交流,长江下游与黄河下游也有密切的互动,诸如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特殊关系已为人所熟知,长江中下游与黄河下游最终整合为“鼎—豆—壶—杯”系统,并且与东北的红山文化存在诸多共同因素。
精神文化的交流更为引人注目,这与“大传统”或者“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密切相关。如高庙文化的八角星纹沿着“长江-沿海”传播带向长江中下游、山东乃至东北传播,高庙文化的兽面纹也深刻影响了长江下游及黄河中下游的文化,成为后来商周饕餮纹的前身。玉玦这样的早期玉器,见诸兴隆洼文化、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也沿着“长江-沿海”传播带分布。至于太阳、鸟、龙、龟等天体及神灵动物的崇拜,广泛分布于“长江-沿海”传播带,体现出先民精神世界的共性。
最为奇妙的莫过于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的共见因素,这也是李新伟先生最为强调的。一者在东北地区,一者在长江下游,相隔一千多公里,却出现了极为相似的玉人、玉龙、玉龟、双联璧、箍形器、石钺等器物。张明华、田名利、韩建业等先生认为这是红山文化南下影响所致,朱乃诚先生认为凌家滩文化向北影响了红山文化,李新伟先生则以社会上层的亲身旅行游学来解释。笔者以为,若置诸“长江-沿海”传播带的视野,将会得到更深刻的理解。最典型的莫过于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出土有手势(很可能是与宗教有关)相同的玉人,可以说出奇的相似。张明华、郭大顺、王仁湘等先生还在各自的文章中提到了李新伟先生所未提及的多件台湾原住民木雕人像(乃至于美洲印第安人创造的类似形象),姿态仍如出一辙。O1-M119这一典型的夷越遗传特征,不但广泛见于长江下游,在红山文化的先民遗骸中也有发现(东北是两大传播带的交汇点),台湾原住民也有与越人一致的遗传结构。“长江-沿海”传播带视野下的文化交流,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层。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共性,不能因为距离过远而否定其联系,也不能简单以传播论来解释。
李新伟先生的理论依据是:从社会距离上讲,越是远离普通民众且只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的价值越高;从地理距离上讲,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的价值越高。但他所列举的例证,多与原始宗教有关,而且在器形上并非单纯的模仿、借鉴,而是出自共通的精神旨趣。这些“长江-沿海”传播带的相似文化因素,很可能根植于夷越族群的常见精神信仰。它们沉淀于文化底层,未必是通过文化交流、借鉴产生的。
“龙山时代”无疑是“中国”形成的重要阶段。“长江-沿海”传播带的文化因素大量涌入山西襄汾的陶寺,直接刺激了这座大型城邑的崛起,中原地区自此奠定“中国”的基础。陶寺所在的山西襄汾,古称“平阳”,相传为尧的都城。清华简《保训》记载,尧因舜“求中”“得中”而禅位。如若按李零先生“中”“国”兼备的标志,陶寺确乎可以说是“最早的中国”。
陶寺文化晚期遭到“长城-藏彝”传播带文化因素的大规模渗透,中原地区经历了一次新的洗牌。在此契机下,大量域外文化因素涌入中原,一个经过重铸的“中国”已然呼之欲出。两大文化传播带因而经历更多的碰撞,陶寺便是重要的中介。“中国”的成立,不独在于其汇聚周边文化,更在于重新整合后的文化能够辐射四方。这一点,后来的二里头显然向世人展现出了更为壮丽的图景。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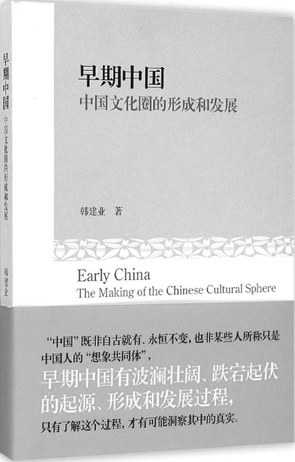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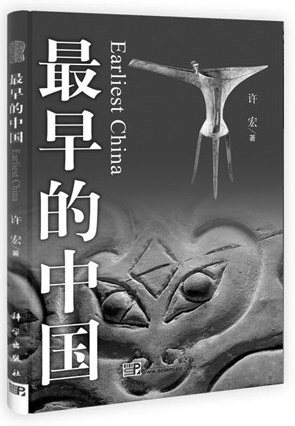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