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科用侦探小说的元素创作了一部反侦探小说,如同《堂吉诃德》用骑士小说的元素讲述反骑士小说的故事。
翁贝托·埃科最后的小说《试刊号》是一部关于小人物的喜剧,书中角色(正如作者所说)都是失败者。主人公科洛纳是个不得志的中年文人,“做着所有失败者都做的梦:有朝一日写一本书,从而赢得荣誉和财富。”他靠各种临时性的文字工作为生:翻译德语,为出版社审稿和校对,在地方性的报纸发表文章,甚至为一个侦探小说家当“枪手”等等。在丰厚报酬的诱惑下,他入伙一家神秘的报社编辑部,参与筹备一份“永远都不会面世”的报纸——《明日报》。其幕后出版人是一位渴望跻身出版界、金融界乃至政界顶级沙龙的商业大亨,谋划在一年内刊行12期试刊号,通过有选择性地调查分析已经发生的事情,有倾向性地预测“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炮制不利于顶级沙龙的报道,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以此为筹码换取对方的邀请函和入场券。不料在开展调查的过程中,一名记者被杀,直接导致编辑部匆忙解散,试刊号遂不了了之,科洛纳也踏上了尴尬的逃亡和自我救赎之路。
埃科用他最拿手的阴谋论题材和侦探小说模式,探讨了关于“真相”的问题。什么是真相?真相存在吗?我们能看清真相吗?怎样找到真相?有多少真相?应该怎样对待真相?在科洛纳及其他人物身上,我们看到,对于真相的不同态度影响了他们的命运。
《明日报》的记者和编辑虽然同属于失败者,却各有不同的症候。其中,与科洛纳关系最密切的两位,就代表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类型。一个是后来被杀的布拉加多齐奥(Braggadocio,在英语里意为“吹牛大王”),阴谋论的狂热爱好者。埃科经常在小说人物身上投射自己的影子,布拉加多齐奥就是一例。他是弃婴的后代,这与埃科本人的身世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埃科另一部小说《傅科摆》的主要人物之一迪奥塔莱维也是弃婴之后。布拉加多齐奥对于真相和阴谋论的迷恋,或许与这种不同寻常的出身有关。他认为人们都生活在谎言当中,所以“不再相信任何东西”。然而,作为怀疑一切的阴谋论者,他对于自己的调查结论却坚信不疑,一切不符合其发现的事情都是虚假的。据他的调查,墨索里尼并没有被意大利游击队员杀死,被倒吊在洛雷托广场上的尸首属于墨索里尼的替身,其本人则在梵蒂冈教廷掩护下逃到了阿根廷。“被认为已经死亡的墨索里尼的影子,笼罩着1945年以来,甚至是今天所有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而他真正的死亡,触发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为恐怖的时期。”同盟国企图利用墨索里尼来对抗共产主义革命,并且成立了半军事性的秘密机构“留在后方组织”,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开展“短剑行动”,从60年代到90年代,在欧洲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政治活动,直到苏联解体。小说的故事时间是在1992年,距离苏联解体还不到一年。埃科动用大量的标志性事件和细节让读者穿越到90年代,以便更加自然地理解这一调查将会引发怎样的轰动效应。
阴谋论是一种目的论证,其典型思维特征就是把结果当成目的,将事件视为早有预谋的结果。如有需要,阴谋论者可以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看成是有故意或必然联系的。本书题辞引用的爱·摩·福斯特“唯有联结!”一语,可以说是阴谋论者的信条。用布拉加多齐奥的话说,“只要懂得咖啡占卜术,就会发现一切事情都是彼此关联的。”埃科将布拉加多齐奥塑造为一个走火入魔地调查“真相”的侦探形象,却又给他安排了一个被杀害的下场,极富黑色幽默。细思这起看似无头案的谋杀,读者会发现凶手不是别人,正是布拉加多齐奥自己。更准确地说,是对阴谋论的狂热诱使他一步步走向意外的死亡。可以说,埃科用侦探小说的元素创作了一部反侦探小说,如同《堂吉诃德》用骑士小说的元素讲述反骑士小说的故事。布拉加多齐奥成了有史以来最可怜的侦探,真是对阴谋论者的莫大讽刺。
与布拉加多齐奥恰成对照的人物是科洛纳的女友玛雅。如果说布拉加多齐奥是偏执狂,玛雅则有自闭症倾向。科洛纳发现这两个人生来反相,自己被夹在两种不同的疯狂之间渐渐分裂。玛雅是一位聪慧敏感的单身大龄文学青年,在听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时会哭泣,梦想着成为一名严肃记者,却报道了五年的绯闻八卦。“我感到玛雅感情脆弱,因此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愿意看到他人世界里发生的事情。”作为小说中唯一的女性,虽然着墨不多,其形象却比占据一半篇幅的布拉加多齐奥更加丰满。按照福斯特的小说人物分类法,布拉加多齐奥显然属于“扁形人物”,而玛雅则属于“圆形人物”。福斯特指出,扁形人物被塑造成为喜剧性角色时最为出彩(参《小说面面观》),或许这正是埃科给予布拉加多齐奥很大戏份儿的原因。玛雅看似一个弱女子,却有着超出男人的智慧和勇气,当科洛纳深陷被留在后方组织追杀的妄想不能自拔时,她将其藏在自己家里,并帮他最终走出恐惧,重返日常生活这一平凡的真相之中。
康德认为喜剧中的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参《判断力批判》),埃科直到小说最后才抖开这一喜剧的包袱。当藏身在玛雅家中的科洛纳(可能也包括读者)焦虑到极点时,碰巧看到电视里播放BBC纪录片《短剑行动》,“那部片子的剧本就像是布拉加多齐奥写的一样,里面包括了布拉加多齐奥想象到的所有情节,甚至还多出一些东西。”节目直言所播内容都是不可靠的指示性证据,不足以为任何人判刑,也就不会影响任何人的利益。致命的“秘密”突然以这种最公开的形式曝光,其危险性顷刻间烟消云散。科洛纳一时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解脱,接下来两人的对话是全书的点题段落:
“这个节目使所有其他发现都显得无用和荒唐,因为你知道(那本法语书叫什么来着?),现实超越虚构。或者,更恰当的说法是,任何人都无力编造任何东西。”
“所以,我自由了?”
“当然,谁说出真相,谁就还了你自由。这个真相会使任何其他发现都变得如同谎言。”
玛雅引用的那本法语书,应该是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年)。该书认为在“仿真的超级现实”面前,传统的现实已经崩溃,虚构失去了它的母体,编造故事已不可能。“今天则是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全部日常现实都吸收了超级现实主义的仿真维度:我们到处都已经生活在现实的‘美学’幻觉中了。‘现实胜于虚构’这个符合生活美学化的超现实主义阶段的古老口号现在已经被超越了:不再有生活可以与之对照的虚构”。这不是埃科第一次引用波德里亚。在小说开始,布拉加多齐奥对一年前的海湾战争是否确有其事的质疑,显然是对波德里亚“海湾战争未曾发生”这一著名论断的戏仿。
在其第一部小说《玫瑰的名字》中,埃科借威廉修士之口评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失传的论喜剧卷道:“也许深爱人类之人的使命就是嘲笑真理,‘使真理变得可笑’,因为唯一的真理就是学会摆脱对真理不理智的狂热。”可见,喜剧是摒除狂热的一个必要途径。埃科推测,喜剧是“人类对恐惧死亡作出的典型反应”(参《巴黎评论》)。基于这一推测,如果说悲剧来源于酒神精神的激情与狂热(参尼采《悲剧的诞生》),那么可否设想喜剧来源于作为人类繁衍之门的女性对抗死神的幽默与冷静?
虽然人物形象稍嫌单薄,对话略显繁冗,埃科最后的小说毕竟与其处女作《玫瑰的名字》形成了首尾呼应,堪称一期成功的喜剧试刊号,庶几功德圆满。席勒说,从维护心灵自由、完善人性的角度来看,喜剧高于悲剧(参《审美教育书简》)。在这狂飙突进、浩歌狂热的时代,我们不妨读读埃科,学会冷静,用喜剧精神呵护一下脆弱的灵魂。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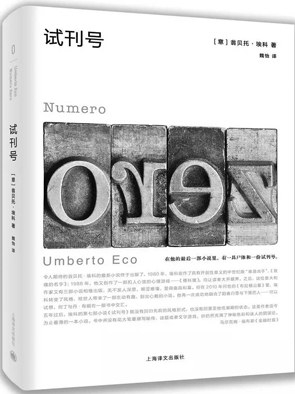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