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笔者编过一本《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2007),立足于诗人译者或具有诗人气质的翻译家视角,注重译论构建与翻译实践并举,梳理与总结中西诗歌翻译并不漫长却充满“论战”的百年历程,当然也收录了著名诗歌翻译家飞白先生的“风格译”,便于我国高校从事诗歌译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师生,尤其是广大的诗歌及译诗爱好者,全面地了解我国诗歌翻译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2017年到了一个推出修订版的重要时间窗口,因为今年既是中国新诗走完百年的辉煌之年,也是几代诗歌翻译家共同彰显百年诗歌翻译实绩之年。年前飞白先生不仅如约修订了《论风格译》,还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之邀在“译家之言”丛书中推出一整本个人译诗六十周年译论集《译诗漫笔》,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翻译思想与译诗经验,可喜可贺!
一
“文革”后新时期之始的1979年,飞白先生终于得到辞去政委军职的许可,打算回阔别三十年的母校联系工作。然而这里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已不是他离开时的浙江大学外文系而是杭州大学外语系了,在谈妥主要事项后他关心起开课问题,岂知外语系当年只有语言课,居然不开文学课!谈到这里他便“拎包就走”,马上转到杭大中文系去洽谈了。当年杭大中文系名师云集,如一代词宗夏承焘、国学大师姜亮夫等。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转业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潜心做一位外国诗歌领域的园丁,为学生开设“世界名诗选讲”“世界诗歌史”“现代外国诗”等课程,声名远扬,吸引中文系以外的学子慕名前往。那一年恰好笔者考入杭州大学外语系学习,前两年尽是些“听说读写”的语言类课程,第三学年才有外国文学课,午后晚间常溜到中文系去蹭课,譬如“美学概论”“文学概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等课程都是在中文系蹭来的,也是在那儿知道杭州出过一位著名的“湖畔派”诗人汪静之,他的儿子汪飞白就在中文系任教,讲解西方外国诗歌。这我岂能错过!后来知道外语系俄语班的汪剑钊同学也有过类似的蹭课经历,继而成为飞白先生的研究生,成长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著名的俄罗斯诗歌翻译家。80年代,那是一个没有动漫、没有电脑游戏、没有微博、微信的时代,那时我们灿烂得如午后的阳光,清澈似水,飞扬的青春在每一颗年轻的心头喷涌,火一样炽烈的情感无处宣泄……唯有诗歌——那个时代里唯一精致的东西,陪伴我们走过那段彷徨、狂飙、闪亮的岁月。杭大77-78级中文系也曾出过全国知名的诗人王自亮(第二届青春诗会)、余刚,小说家李杭育等。我也正因有过这样一段蹭课经历,尤其是蹭完飞白先生的“外国诗歌”,才开启一颗青春萌动的诗心,在稚嫩的心灵“惊起一圈涟漪”。翻阅眼前泛黄的日记本,一道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徐徐打开,一些久违的东西潮水一般漫上心头,激越与忧伤、光荣与梦想,穿过几十年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越过被生活磨平的棱角,由朦胧变得清晰,当初的日记写下我“最初的诗意”:一枚石子投入水中/惊起一圈涟漪/层层叠叠//清澈的湖面/顿时模糊不清/茫茫然,不知所措……//不一会儿,又一枚石子/一枚又一枚,投向更远的湖心/丁零零……下课铃响了/先生收起外国诗歌的讲义。
1986年我报考上外的“当代美国诗歌”研究生,“从岸边承租一条船,载坐几个自己/等待一个无风或有风的早晨/告别堤岸//海就在岸边,船就在海边”。阴差阳错,我却从文学院拐入了医学院的大门,但幸运的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陈维益(1924-2010)先生竟然是飞白先生在浙大外文系的同学,早已从文学转行成为一位资深的辞书专家,无意间承接了百年英汉医学辞典的使命。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如果说文学让人步入一个美妙的精神世界,淬炼与净化人的灵魂,那么医学让人更接近生命的本体,直面自己的肉体、疾病与死亡,继而替我开启了诗魂的大门。笔者一生有幸蒙受两位资深翻译家的启蒙与教诲,让我触摸到老浙大外文系的文脉。今年浙江大学迎来了第120周年的校庆,百年峥嵘,薪火相传。我一直以语言为原点,一手触及枯燥乏味的医学语汇,一手深入鲜活奔逸的诗歌语符,在汉语与英语的两个世界里自由穿梭。我把整个残存的灵魂都投入到这一次旅程,庭院再深,天空更深邃;生死一瞬间,生死历程更隽永。飞白先生在我心中燃起的诗歌之火从未熄灭,2007年我编选出版了《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给飞白先生寄去一本样书,设法重新联系上他时,他在电话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海岸想必是你的笔名吧?你是杭大的毕业生,是不是我的学生?”是的,您的“编外”弟子!如今汪门诗歌翻译家,桃李满天下!2014年笔者翻译的《狄兰·托马斯诗选》荣幸地与飞白先生翻译的《哈代诗选》、剑钊兄翻译的《王尔德诗选》一起入列外研社策划的“英诗经典名家名译”系列。事后我告诉出版社的编辑,飞白先生与我曾有过一段师生渊源。同年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联系我捐赠80年代诗歌翻译手稿时,我自忖只有翻译狄兰·托马斯与萨缪尔·贝克特诗歌的两部手稿,建议他们收藏飞白先生及其弟子们的诗歌翻译手稿,还陪他们一起去飞白先生在杭州的寓所接受他一拉杆箱手稿的捐赠。这也是我从杭大毕业三十年后再次见到飞白先生,他依然是那么清瘦,身姿笔直,透着一股硬朗之气。我们还在浙江大学图书馆为浙大师生做了一次“诗海漂泊者——飞白、汪剑钊、吴笛、海岸师生漫谈诗歌创作与翻译”演讲,再次聆听到飞白先生用十余种语言朗诵他心目中的世界名诗。2015年早春时节,我随上海翻译家协会去嘉兴参观著名诗歌翻译家朱生豪(1912-1944)故居,在南湖烟雨楼与资深翻译家潘庆舲先生聊起老浙大外文系他们最后一批毕业生的名人轶事。他回忆道: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那时每年考入外文系的人不多,几个年级的同学一起上课,既然进得了外文系,语言都过关的,上来就读原文名著;汪飞白、陈维益、钱鸿嘉(1927-2001)都是同级的,学习都非常刻苦。飞白未毕业就随解放军四野南下了,三十年后回到杭州,陈维益、钱鸿嘉和他则相继落脚在上海。他们各自都在新中国翻译事业中留下了重彩浓墨的一笔。如今年近九旬的飞白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依然有忙不完的翻译计划,戏言自己是“老人出海”,“诗海水手”常在杭州与昆明间候鸟般迁徙,何等潇洒!
二
飞白,全名汪飞白,1929年生于浙江杭州,祖籍安徽绩溪。“金黄的林中有两条岔路,不能两条都走”,1949年他选择投笔从戎,历任第四野战军/广州军区军事兼外事翻译直至某部政委等职,在军区报社任职期间遭遇“文革”,遭秘密逮捕,后复出致力于部队冤假错案的平反;而“路是连着路的”,1980年起他又选择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中文系、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他这一选择就走出了“诗海漫游者”的航迹,长期致力于世界名诗的译介与研究,认定“从原文直接翻译”为译诗的不二法门,“转译只能是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故而他先后掌握了十余种语言,先后出版了《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上下卷)《诗海游踪:中西诗比较讲稿》《古罗马诗选》《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法国名家诗选》《马雅可夫斯基诗选》《勃朗宁诗选》《哈代诗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上下卷)等著译二十五卷,主编并参与《世界诗库》(十卷)拉丁文及英法西俄荷等十余个语种外国诗歌的翻译和译介,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特别奖等主要奖项十余种,其中《诗海》是我国第一部“融通古今、沟通列国”的世界诗歌史,《世界诗库》被公认为是全球第一套全面系统的世界诗歌名作集成,被誉为“世界诗史的一个奇观”。2009年他宣布“下课”,第二年送走最后一批研究生后,才静下心开始整理长期积累的译论,直到2016年底个人译诗六十周年之际,出版了个人译论集——《译诗漫笔》。
事实上,飞白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写“译诗漫笔”了,当时还引起译界的关注和热议,诗人翻译家卞之琳誉之为“中国译诗艺术的成年”。飞白先生因教学工作繁忙,写了几篇就一搁三十年,直到今日才续写成全书。他在80年代末就把翻译主张归纳为“风格译”,并看作是译诗艺术的核心。这次他把1995年第3期《中国翻译》上发表的《论“风格译”——谈译者的透明度》收录在第四辑旧作中,全文刊出原《论“风格译”》未发表的前后两节“以怎么说统率说什么”和“论见仁见智之不可怕”,强调“风格、风姿高于一切,译诗就应以怎么说统率说什么,这是他针对译诗提出风格译的原因”。全文开门见山,“认为译诗的方针既不是直译也不是意译,而应该是风格译”,继而定义“风格译的着眼点是诗歌翻译的艺术性之整体,既包括诗的文体和类型特色(例如雅与俗、庄与谐、豪放与婉约等),诗人的风格气质(例如飘逸、沉郁、象征、超现实等),也包括语言修饰风格和音律风格等形式方面的特征,是形神统一的,有别于直译、意译两家的形神割裂观”,他更是提出风格译的目标就是努力呈现诗风之争奇斗艳,而不是把不同风格纳入同一规格、同一模子里。90年代飞白先生这篇《论“风格译”》在业界影响深远,他提出译者应如何理解与揣摩诗人的风格姿致,继而译出诗人一生风格的变迁,切忌一整本或多本译诗集都是“面貌雷同”的腔调,更重要的是将译者个人的翻译风格如何巧妙地融入其中。这也都是笔者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标。
《译诗漫笔》前三辑29篇都是飞白先生近年新写的,清晰系统地阐述他的译诗观,他在晚年连续十五年带教研究生“翻译学”后再来谈译诗艺术,视角更开阔,思路更全面清晰有趣。第一辑共有9篇文章,他在首篇《翻译的三分法》里指出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翻译世界已经多元化,单一标准已不适应翻译多功能的实际,不同翻译类型需要不同的方法和标准,习惯把翻译分为“直译”和“意译”,既含糊又不科学,他归纳出“信息型语义译”、“审美型风格译”、“功效型交际译”。他继而在《制筌者说》一文里分析“审美型风格译”和“信息型语义译”对待语言的看法、态度和不同的处理方法,前者注重“意在言内”,后者关注的则是诗家所谓的“意在言外”。《跨境的诗翻译》一文则说到诗翻译时会有局部的“信息译”“功效译”的成分,诗翻译跨境不可离境太远,走得太远而脱离诗翻译本质就不能算诗翻译了。从诗翻译跨境进入信息译的状况比较多,一切中规中矩,只可惜离诗歌本质远了些,比较起来还是“功效译”方向有趣些,在追求实效的广告类、宣传类翻译中是黄金法则,但在文艺类翻译中还是谨慎运用为好。
第二辑有10篇文章,《拨开直译意译之雾》与《翻译的多维世界》以信息型、审美型、功效型的翻译三分法辅之按多维度(词义、语法、语境、文化、形式、风格、功能)细分的20个翻译取向,拨开简单化直译意译两分法造成的一团迷雾。《为不忠实一辩》和《为忠实一辩》强调审美风格译领域里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要重视对原诗的努力逼近和对原诗风格的刻意求似。第三辑依然有10篇文章,飞白先生早期译诗全凭记忆而不能在纸面上进行,故而形成一种“基于听力的口译式风格”,他在《译诗需要敏锐听觉》一文要求译者通过听觉充分感受诗歌风格的韵味并谙熟于心,才能在跨言语重写中对总体风格作综合模拟;译诗中常常遇到的音乐性元素不限于行末是否押韵,还应充分考虑诗中的元音协同、辅音协同元素。《接受格律的挑战》一文提出诗律只有在同一系统的语言之间才可能移植,但译者得接受格律的挑战,模拟原作诗律的风格特色努力求似。《镣铐,还是翅膀?》一文表明译诗体现音律不易,经常要在音和义间协调取舍;“戴着镣铐跳舞”好辛苦,且历来诗家对诗的音乐性所持观念不同,古典派认为音韵应为义理服务,而象征派则把音韵置于义理之上,但真正的舞者、诗人或译诗者都不会视音律为“镣铐”,而视之为舞和诗飞翔的“翅膀”。诗的音乐性蕴含在诗内,是维持诗歌生命的“循环系统”,而不是在诗译成后“加韵脚”而成的。凡是外加韵脚都难以与音韵、意境融合无间,终难成飞翔的翅膀。而《转译之“隔”》颇有降温当今转译之风的功效,“诗是不宜转译的,转译的诗是不可信的,若不看原著而从人家的译本转译,就会感到非常‘隔’,好比是‘隔着布袋买猫’,不仅诗的艺术特色全被‘隔’掉,就连转译透出来的词义也因‘隔’了一层而捉摸不准了……至于诗的形式、格律、风格等就更近乎盲目了,岂止是隔布袋,简直是隔了堵墙。一串人玩传话游戏,传的是同一句话,不须作语言转换,结果也常会闹笑话;诗的转译更要历经转换,且受制因素很多,传的结果更可能面目全非”。本雅明在著名的《译者的任务》中声言:“翻译就是把原作译入更为终端的语言领域,因为原作一到此就不能再次转译了”,看来一切诗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只能从原作重新开始。
三
中西诗歌翻译史已逾百年,外国诗歌翻译的实践可追溯到晚清诗人苏曼殊、马君武的文言格律体翻译,最早的白话译诗在胡适尝试白话诗的同时首开先河,五四运动前后,外国诗歌翻译掀起了第一个浪潮。20世纪20到30年代,鲁迅、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戴望舒、施蛰存、朱生豪、梁实秋、冯至、梁宗岱、孙大雨先生等在诗歌翻译领域作出了示范性的贡献。鲁迅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曾翻译过德国诗人海涅的作品,后来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又介绍过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裴多菲等诗人的作品。郭沫若先生很早就开始翻译德国诗人歌德的《浮士德》和波斯作家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冰心翻译出版过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先知》,朱生豪先生更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先行者。那个时期从事诗歌翻译实践与诗歌翻译理论构建者大多为诗人兼翻译家,他们的新诗创作与翻译实践互为作用,共同推动着中国新诗运动的发展,迎来了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蓬勃发展,新的诗歌翻译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呈现,1954年査良铮先生翻译出版了普希金长诗《青铜骑士》,1955-1957年又先后翻译出版了《拜伦抒情诗选》《普希金抒情诗》及长诗《欧根·奥涅金》。1955年方重先生翻译出版了英国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954-1962年间朱维基先生翻译出版了但丁的《神曲》三部曲,1956年屠岸先生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方平先生翻译出版了《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1957年飞白先生更以军人身份翻译出版了苏联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反法西斯战争名著——曾经传遍苏联红军前线战壕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后又翻译马雅可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苏联著名诗人的作品。
80到90年代期间,外国文学的翻译蓬勃发展,诗歌译坛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劫后余生、重建辉煌的老一辈诗歌翻译家,如卞之琳、王佐良、罗念生、田德望、余振、戈宝权、袁可嘉、许渊冲、屠岸、方平、飞白、杨德豫、江枫、钱春绮、汤永宽、吕同六、王智量、黄杲炘先生等为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复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可谓是外国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互为促进的时代,也是中西诗歌美学思想相互汇通的时代。一百年间古希腊、俄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伊朗等数十个国家的大量诗歌作品或早或迟地被介绍到了中国,史诗、哲理诗、抒情诗、叙事诗等五花八门的诗体成为中国诗坛的主角,经典外国诗歌作品甚至被多次重新翻译。步入新世纪以来,新一代诗人翻译家出入译界,为诗歌翻译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们遵循“诗人译诗、译诗为诗”的原则,在阐释与重建诗歌文本的过程中吸取养分,融入到自身的创作中,为置身其中的当代汉语诗坛与译坛带来新的活力与繁荣。
纵观我国百年的中西诗歌译学理论,无论从“信达雅”“化境说”到“多元互补论”,还是从“形似论”“神似论”到“风格译”“三美论”乃至“三兼顾”等等,中西诗歌翻译实践基本围绕“直译”或“意译”、“格律体”或“散体”等几个方面展开,试图解决“语言形式与内容关系”这一诗歌翻译本体论主题。与其他各种翻译相比,诗歌翻译实践有其特殊性,由于诗歌语言精炼繁复,比之其他形式的翻译更能集中地体现对语言技巧的理解、把握与处理。中西诗歌翻译的关键最终要落实到语言技巧处理问题上来,亦即形式与内容的协调问题;本体诗歌翻译实践讨论的焦点也集中在特定的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客观地看,我国至今在诗歌语言形式技巧与内容的协调关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翻译家各人间的分歧已然存在。当代诗歌翻译家在翻译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分歧,都难逾越翻译者个性的制约。例如,某个译者译得太直白,则该译者多半强调直译的重要性;某个译者译得太自由,则该译者多半强调意译的重要性;某个译者译得讲究韵律,则该译者多半强调音韵的重要性;某个译者的翻译太注重形式,则该译者多半强调形式的重要性;某个译者的翻译太注重神韵,则该译者多半会强调创造性与意译的重要性。当然,这些都不是绝对单一的,主张直译者并非主张绝对的直译,在具体情况下也是可以默许变通的;主张意译者也并非主张完全抛掉原作形式而任意胡来,而是认为原作形式一旦不便模仿,就可以大胆变通,在不违背原作本意的条件下发挥翻译主体的创造性。各种诗歌译学理论与翻译实践可不同程度地兼收一二种或融合多种观点。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次推出的飞白先生的《译诗漫谈》,以诗歌“风格译”为中心,译论系统全面,言之凿凿,值得向广大诗歌翻译研究者及广大诗歌翻译爱好者隆重推荐。
(作者为复旦大学学者、诗人、翻译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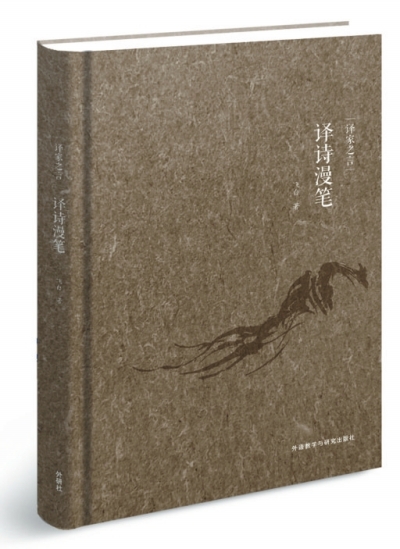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