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汉鼎,生于1938年,我国著名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成功大学文学院客座讲座教授。德文专著有《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中国哲学基础》等,中文专著有《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等,译著有《真理与方法》《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等。
2016年,洪汉鼎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该书回忆了作者从少年时代至今的人生经历,介绍了作者个人的哲学观点,其中对冯友兰、贺麟、洪谦等诸位老师的深情回忆尤为动人。近日,洪汉鼎先生在京以“哲坛旧事——我北大的那些老师们”为题做了一次讲座,本文系根据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编者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这本书(《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我在台湾讲学多年,2013年离开台湾时,那里的博士生对我作了一个访谈,这个访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于是以访谈内容为基础出了这本书。书中记录了很多北大往事。北大张岱年先生的博士生陈来,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洪老师,你书里边讲的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真是太好了,这本书让我能了解北大更深层的一些东西。
“得天独厚”的北大哲学系
今天我讲一些哲坛旧事,主要谈北大的老师们。我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北大的哲学系可以说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时期,因为只有北大一所高校有哲学系。当时把全国所有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全部集中在北大,所以北大有近一百位全国知名的教授,像熊十力、贺麟、洪谦,美学方面有朱光潜、宗白华,历史哲学方面有朱谦之,梁启超有一个弟弟叫梁启雄也到了北大。还有从中山大学调来的几位哲学教授,有一位叫方书春,希腊文很好,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就是他译的。
当时全中国的哲学教授都集中在北大。我感到很幸运,因为能有这样多的教授来熏陶自己。
我的哲学生命跟贺麟先生联系在一起
我首先要谈的是贺麟教授。在我看来,贺麟教授是能把西哲用中国语言表达出来的一位大哲学家。贺先生翻译了很多黑格尔的东西,是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同时又是研究阳明学、陆王心学的代表性人物,所以他往往把黑格尔的理论一方面跟朱熹的理学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从王阳明心学的角度进行批判,等于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起来了,因此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个时候我去拜访贺先生,他首先问我:你从什么地方想到学哲学?我告诉他:我是从文学进入到哲学的。贺先生说太好了,哲学本来是抽象概念,你如果完全从抽象概念出发,肯定做不好,只有从文学中感受到这种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对哲学的理解才会更深刻。我以前只知道看文学书,没有想到贺先生把从文学到哲学这条路的有益之处给我指出来了,所以当时我感到有了信心。
接下来贺先生问我:你知道哲学要怎么学吗?就我们今天来说,学哲学有很多的东西要学,首先要学的就是哲学史,这与学其他学科不一样。比如物理学,物理学史都没人注意了,要学的是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但是哲学不一样,哲学的渊源就在古代经典里,所以学习哲学史对学哲学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环节。贺先生告诉我:要想在这个领域站住脚,除了要有一般的哲学史概念,更重要的是要从一个点上做起。这对我一生的启发太大了。从今天来看,在哲学界比较有名的学者,绝不是什么都研究的,而是在一个点上做到了“深”。我举一个例子,已故著名哲学家方立天教授是我的同学,他的研究领域是佛学,他只研究佛学。很多的学者都是这样,比如贺先生是研究黑格尔的,洪谦先生是研究分析哲学的,冯友兰先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都是在一个点上。贺先生说千万不要变成万金油。
我在大学跟博士研究生谈话的时候说,我对博士研究生有四点要求:第一,做哲学研究一定要客观。第二,要从一个点做起,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要向大师学习,大师很重要,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胡塞尔的学生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学生是伽达默尔,都是非常优秀的。第四,博士研究生一定要有霸气,没有霸气不行的。还有,学习哲学,必须要做翻译,不做翻译,你不能够完全理解,不能完全进入。
我的哲学生命是跟贺先生联系在一起的。我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别的老师都对我避而远之,但是贺先生没有。在那个时候他要我读斯宾诺莎,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斯宾诺莎的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人生。我们读书要跟我们的人生结合起来,人生有时候非常不幸,想要从苦难的意识中摆脱出来,可以读一读斯宾诺莎。斯宾诺莎24岁时就被犹太教放逐,他不仅没有工作,而且人们都要与他保持距离,不能跟他说话。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哲学研究,后来成为一位很重要的哲学家。
在我的人生当中,既有不幸的一面,也有幸运的一面。在人生幸运的时候,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位哲学家就是费希特。费希特的人生也很奇特,他家境贫寒,连学都上不起。但是他很聪明,记忆力很强,别人说过的话他马上就能背出来,后来一个大地主资助他,一直到大学毕业。当时他有一个强烈的意愿,就是一定要去见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结果他就徒步去见康德。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整个欧洲都反对法国大革命,但费希特说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花朵,连续写了几篇论文,在欧洲影响很大。他后来获得了耶拿大学的教席,当时听他课的学生非常多,教室里装不下,于是他把学生带到教堂里去上课,结果遭到教会人士的反对。歌德建议费希特换个教室,但费希特不愿意,他说他认为正确的事就要做。这就是他的性格。
由此我悟到了人生有阴阳两面,有动和静的两面。人生有不幸的时候,也有幸运的时候,在不幸的时候我可能会更多地想到斯宾诺莎,在幸运的时候就会想到费希特。
在我最不幸的时候,贺麟先生是这样来教导我的。尽管当时我的右派帽子已经摘了,但还是受到影响。考研究生考第一,结果不录取我,给我分配到陕西,然后从省里又分到咸阳专区。在困难的时候,贺麟教授经常给我写信,使我非常感动。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第一届研究生招生,贺先生要我报考,当时报考研究生的年龄上限是40岁,我已经超了,41岁,但贺先生说没有关系,他向社科院为我特别申请。就这样,在贺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我考回了北京。贺先生在我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老先生们有“经世致用”的观念
当然,从民国过来的这些老师,也有很多我们今天的人不太了解的一些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冯先生表现并不好,但是你要了解这背后的原因。老教授们有一个情结,叫经世致用。
贺先生也同样,我有一次陪他去看徐梵澄先生,我陪贺先生到中央党校讲课回来,徐梵澄刚从印度回国,见面时问了贺先生一句话,说贺先生你从哪来?贺先生说,我是从中央党校讲课来。徐梵澄老先生马上说:“贺先生,你始终抓住党校不放啊!”这句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我是深有体会的。为什么呢?在1949年前贺先生就被蒋介石多次约见,并在国民党的“党校”讲课,1949年后因为讲黑格尔,毛泽东接见了他,又在中央党校讲黑格尔。对贺先生来说,关键是传播他的学术,他讲求“经世致用”,这大概是这些老先生们很重要的观点。朱熹、王阳明,可能都是这样一种观点。
“颜子之乐”
知识分子有一个境界,就是在学术中感觉到愉悦和美。我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气象与颜乐》,促动我写这篇文章的是北大王博、李中华等谈到的一个现象,他们说,我们北大哲学系老教授都是长寿的。的确是这样,冯友兰活了95岁,周辅成98岁,贺麟90岁,宗白华89岁。他们说,北大哲学系是一个长寿系。为什么?因为这些老教授心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进入哲学境界,感觉哲学是生命当中的爱好。我现在也是如此,尽管我年纪这样大,但是一讲到哲学,心里就完全被哲学的意义所充满,感觉到愉悦。
我再举个周辅成教授的例子。我记得我1985年从德国回来,那时周辅成教授已经74岁高龄,有一天早晨他从北大跑到我家,说听说我回来了,问我带回什么德国的古典音乐了吗?他还跟我说,他现在每天都要听德国的那些歌剧,他收了好多磁带。这就是心境,有这样的心境他能不长寿吗?
还有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他是1986年去世的。我从德国回来后去看他,那个时候他身体已经不怎么好了。他半睡着,我叫了他一声,他醒了,还认得我。我说我刚从德国回来,他一听说德国,马上坐起来,跟我说,他在30年代到过海德堡,它是那样漂亮。我说我正好拍了一个海德堡的录像,他说那你要带过来,我说好。我走的时候他还反复叮咛,说下一次一定要把那个录像带来,结果隔了两个月,我就听说他去世了。所以有时候我心里非常难受,一个老教授到晚年这点心愿都没能帮他实现,让他带着遗憾走。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身体虽然已经很不好了,但他的心还寄托在当时在德国研究哲学的时候,在海德堡那个城市。
还有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伽达默尔,活了102岁。我在他101岁时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身体还非常好,眼睛看得见,手写字也不打颤,思维很敏捷,心情很好。所以那天我说,这就是哲学家。
还有我的老师张世英先生,现在研究西方哲学史最年长的可能就是张世英先生了。张世英先生精神好得不得了,身体也很好,我们一去就谈哲学。进入哲学境界以后,人就能够精神起来。这叫什么,就是颜子之乐,不在于这个衣衫穿得怎么样,而在于你进入那种精神境界。
再举一个例子,人大的苗力田先生,因为让我最难受的就是苗公的事情。那年韩东晖博士研究生毕业,他的题目是斯宾诺莎,苗公请我去做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他说研究斯宾诺莎没有洪汉鼎的批准不能算及格。他当时非常高兴,因为韩东晖的论文通过了。吃饭的时候,苗公跟我讲两样事让我帮他:一个他要继续带研究生,而且是研究斯宾诺莎,让我帮他;第二个是他搞康德全集,一定要我把关。苗公爱喝酒,饭桌上喝了茅台酒。苗公当时毕竟八十多岁,我就说,苗公已经喝了一杯,我们是不是不能让苗公再喝了。但大家看苗公很高兴,就让苗公喝了两杯。第二天我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说苗公不行了,当天晚上住了院,结果第二天就去世了。我当时非常难受,马上写了一篇悼念苗公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一直后悔当时没有坚决阻止他多喝的。
门风:能够成就你也会限制你
还有一位老师是洪谦先生,现在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八十年代以前研究分析哲学的人不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洪谦先生。在西方哲学家看来,能跟他们对话的中国哲学家没有几个人,陈康是一位,然后就是洪谦。洪谦是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他适应不了1949年后的学术生活。他认为他那一套分析哲学是最重要的,可是当时我们国家又不认为分析哲学重要,甚至于大部分人都喜欢思辨哲学,他感觉到很孤独,所以他能够做的工作就是翻译。1978年回到北京,我就投入了洪先生翻译分析哲学的工作中。对我来说,洪谦先生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
我们那一代的老师,很讲究门风。贺先生这一门的门风,一方面是老师本身好,另一方面就是学生非常推崇贺先生的学问,愿意去继承他的学问。贺先生经常讲一句话,青出于蓝胜于蓝。他经常跟我们说,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你们将来有好多地方会超过我的。学生都愿意跟随他。
门风当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它的弱点。对于我来说,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既是贺先生的学生,又是洪先生的学生。尽管贺先生跟洪先生的关系非常好,但是他们在学术观点上完全不同。有时候我到洪先生那里,洪先生问我:“贺先生那个语言经得起分析吗?”因为作为分析哲学来说,语言一定要有明确性,要有论证和清晰性,逻辑的范围外延都要合。我到贺先生那里,贺先生有可能会问,洪先生那个语言是很清楚的,但是哲学难道都研究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吗?我觉得这个话也蛮对的,洪先生研究语词是否有意义,对我们人生有用吗?
所以后来贺先生对我也有过意见。在1979年,我是文革后最早毕业的研究生,那个时候国家很重视,《光明日报》整版做了介绍。当天晚上,中国社科院在西单的四川饭店吃饭,所有的知名教授都参加了,在那个会场贺先生实际上讲了门风,他说,洪谦,洪汉鼎现在已经毕业了。他在举酒杯的时候,跟大家作了一个揖,他实际上就是说,这是我的学生。所以问题就是门风有时候会把你限制住。
我有一次写了一篇文章叫《西学东渐记》,可能里面把洪先生写得很好,贺先生当时很生气,他说他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没有进入哲学。
“再没有人像他们那样”
我再说一位老师,温锡增先生。他长期在英国留学,在英国大学做教授,五十年代周总理发出邀请,希望海外的专家都能够回到大陆来,他响应这一邀请回到了北京,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做研究。他回来的那一年大概是1962年。1963年正好赶上当时的第一届研究生考试。当时我先找贺先生,说想考贺先生的研究生,结果贺先生说,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颇密切,离政治很近,而我又是摘帽右派,我考他的研究生可能不行,我最好选一个离政治远的研究方向,就是古希腊哲学。而温先生正好是搞古希腊哲学的。温先生刚从国外回来,全部用英文出题,而我的英文很好,所以当时我考得是最好的。到了快放榜的时候,我听到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会录取我,因为我毕竟是摘帽右派。
于是我就到温先生家去跟他告别,也告诉他我不可能被录取。我到了温先生家,看到他有那种英国的绅士派头,他坐在椅子上,他夫人站在他旁边。他跟我说,只有我的考卷他满意,其他的都不行。我和他说,我打听到消息了,这次可能我录取不上,我有政治问题。你们知道温先生当时怎么说?他说:我招的是优秀的研究生,政治问题我不管,如果他们不让我录取你,我这一次就不收研究生了。这是1963年8月的事情,我记得从温先生家出来以后,那微风吹得我都流眼泪了。
后来我在陕西待了15年,然后1978年回到北京,再去拜访温先生,你们知道温先生跟我说了句什么话吗?“汉鼎,我告诉你,你那份考卷我还保存着。”当时他这句话一说,我眼泪就下来了。
这些师生情我永远忘不了。当这些老师去世以后,我感觉到自己非常孤独,再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没有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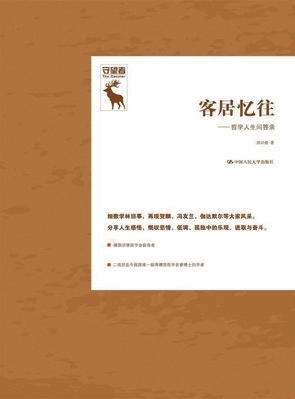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