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界风起云涌。有一批历史学家试图打破现代史学对于历史时空范围的限定,将人类放归生命乃至宇宙的演化之中加以理解。其中的杰出的代表,就包括主张“大历史”的麦考瑞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克里斯蒂安,和宣扬“深历史”的哈佛大学考古与历史学教授丹尼尔·罗德·思麦尔。相较于后者,前者在国内更具影响力,其作品也已渐被引介到了中文世界。克里斯蒂安教授领导撰写的《大历史》的中译本最近问世,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其主张的好机会,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大历史”的大致模样。
首先是呼唤跨学科的历史学研究。克里斯蒂娜所主张的“大历史”,强调打破专业化史学的樊篱,让不同学科知识都进入历史叙事。一如前言中作者所言,“在本书中,我们会向你们介绍一种看待过去的新视角,它是由众多不同学科的作者在晚近建构起来的,这些学科涉及历史学、地质学、生物学以及宇宙学等”(第2页)。自兰克以来的史学专业化和学科化,在精进“技艺”、推动学说/学派迭起、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书写权力的垄断倾向,专业史学家成为了克里奥女神的祭司。早在20世纪中期,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就已表达出对此种情形的不满,并试图加以改变。但是,直到今天依然时常听到学界内“跨学科”研究的呼吁,可想而知垄断的情形如今也大体不变。但是,在《大历史》中,作者大量引用了二战后西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用以厘清前人类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大历史》构成了一部按时间排列的百科全书。这种对于自然科学的开放态度,的确应当对其他历史学家有所启发。
其次,笔者以为“大历史”另一主要诉求,在于打破“自然史”“史前史”和一半意义上的“历史”三者的樊篱,为宏大视野下的新历史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正如导论中众位作者的激动之语:“我们现在能够研究的,不是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史,而是数亿年前的过去,包括生态圈、地球以及整个宇宙的历史。”一般而言,智人的出现被视为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在大历史的视角下,三者之间的藩篱并无法阻断历史学家如炬的目光。取而代之的是以复杂性为标准的“八大门槛”:大爆炸、恒星、较重的化学元素、行星、生命、智人、农业和现代世界。在《大历史》的作者眼中,历史发展和变化的基本趋势并非目的论地指向人类诞生。与之相反,人类及“人类史”的出现只不过是宇宙复杂性强化的一个阶段性标志而已。
很显然,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书写,也是《大历史》的核心诉求之一。呼应过去几十年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历史研究趋势,近年来国内史学界也逐渐意识到了碎片化历史书写的局限,“全球史”“跨国史”“国际史”等二战后西方史学界的一些新概念逐渐得到引进和重视。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在于打破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狭隘视角,强调回归宏大叙事。其中,视野最为广阔者,恐怕当属主张“大历史”的克里斯蒂安等学者。在吸取自然科学的观念的基础上,他们摆脱了历史学家对于人类和文本的崇拜,从整个生态系统的高度理解人类历史。
在生态学领域,对于人类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由来已久。人类自视为万物灵长,因此人类出现的前时代往往被视为“史前”的荒芜时代。但是,在《大历史》的叙事框架中,这部分的历史却占据了大量篇幅。从最初的大爆炸到地球出现,再到智人的诞生,亿万年的岁月孕育了人类。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自然所提供的一切似乎是天然为人类所准备的,但事实上我们只不过是生物圈的一部分。虽然,“在近40亿年时间,我们成为了第一个有能力独自改变生物圈的物种”(第411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逃避可能随之降临的大自然的最后裁决。在《大历史》关于人类历史的描述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得到了充分展示。同时,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对环境的破坏,在《大历史》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思。
所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思,构成了《大历史》最重要的主张。长久以来,预测和展望未来都是历史学家所不喜的一项工作,正如《大历史》的作者所言,“有小部分人避免去思考未来,传统历史学家或许就是这类人”(第415页)。不同于他们的同行,大历史学家则立足于现实和未来审视过往。为此,大历史学家自信地写道:“要想领悟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就得具备明晰性、创造性、激情和勇气。大历史视野是清晰观察这些问题的出色方法。”(第431页)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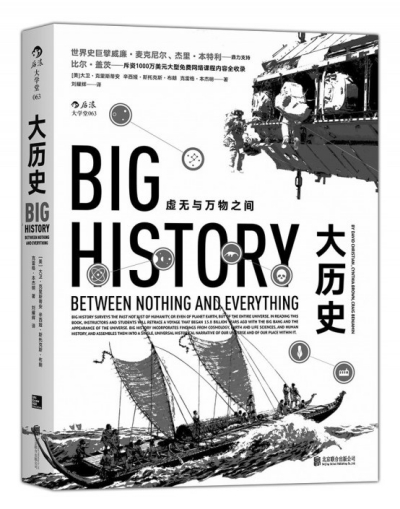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