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始于情感”?就是对笔下的东西有感觉,有情感,有某种冲动,不是搬个理念或者技巧来哗众。什么叫“终于人物”?就是要落实于人物,把人物写得鲜活、结实、丰富,不能成为一些华丽的影子和流行的标签。
韩少功被公认为思想型作家,因为他总能敏感地抓住社会动荡、变革的深层动因,并以文字的形式,极端艺术化的手法诉诸于作品。在他的创作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人类文明、对人性的思考。无论是代表作《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日夜书》,还是新书《孤独中有无尽繁华》和《夜深人静》。
与20世纪80年代贴着“先锋”标签的作家不同,韩少功算不得先锋派作家,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保持着先锋的姿态。他的文体革新与精神探索并驾齐驱,他对中国经验加工提炼的深度,显然超出了同时代的作家。这一姿态,既缘自他与当地农民血脉相连的融洽与体贴,也缘自他胸怀天下的开放。
中华读书报:《孤独中有无尽繁华》和《夜深人静》,收入了一些旧作,但是阅读时,不论翻到哪一页都能迅速吸引我看下去。我觉得这才是好小说。您对小说的评价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
韩少功:文无定法,很难有个好小说的行业标准。不过有些基础标准绕不过,比如标准之一,我归结为八个字:始于情感,终于人物。什么叫“始于情感”?就是对笔下的东西有感觉,有情感,有某种冲动,不是搬个理念或者技巧来哗众。什么叫“终于人物”?就是要落实于人物,把人物写得鲜活、结实、丰富,不能成为一些华丽的影子和流行的标签。没有这一条,玩结构、堆情节、秀文体,就都成了空中楼阁,画鬼容易画人难。
中华读书报:您是最重视文体探索的中国作家之一。是什么原因使您具有这样的探索精神?擅长在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的作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先锋作家,但是另外一些人,外语能力强的作家,比如您,似乎走得更远。
韩少功:西方文学是他山之石,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中国第一流的作家和学者几乎都在学外语,都在做翻译,因此30年代至80年代的翻译质量总体上最高,使中国文学创作受益匪浅。但后来的情况有些变化。一是出版社热衷于抢档期,拼市场,粗制滥造者多。二是外语教学的应试化和功利化。我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才子,词汇量不算小,语法点都精确,肯定能考出高分,但一旦离开课本,对很多寻常的历史和文化知识,常常是一脸茫然。有一次我说到自己的知青经历,说“农村就是我的大学”,一个学西班牙语的博士竟然拒绝翻译,似乎觉得这句话不通。这样的人来做文学翻译,岂不可怕?我这里的意思是说,语言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眼下很多外语人才的文化修养不够。当年梁实秋建议每一个中国作家都来翻译一本外国文学,支了一招,但眼下实行起来太难。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翻译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吗?据说当时很多出版社都拒绝出版?后来是什么机缘出版的?
韩少功:当时主要是因为昆德拉没什么名气,相当一部分编辑只认名气,那就没办法了。后来作家出版社的白冰先生等力排众议,才接受了译稿。当时这本书在捷克还是“禁书”,外交部审读后,要求“内部出版”,要求“磨”掉一点敏感词句,以免影响对外关系。但不管怎么样,中国读者甚至比很多东欧国家读者更早读到这本书,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吧。去年我与这本书的法译者许均先生一起吃饭聊天。他说到国内好多同译一本书的,最后都不能见面了,像我们这样能一起吃饭的相当罕见。这也算是一个小“八卦”吧。谈到昆德拉在中国有这么多读者,有这么好的运气,我们都觉得有些意外。
中华读书报:您经常直接阅读外国原著吗?这种优势是否体现在您的小说创作中?
韩少功:以前读过英文版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索绪尔等,都不算“原著”,不过双语比较,会有很多乐趣和一些感悟。当然也读过毛姆、莱辛、福克纳、卡弗等英语作家,不过对自己的写作好像没有多少直接的作用。仅就语言而言,方块字的组合变化空间好像更大些。我读外文的时候,常常觉得这一句或这一段,用中文可以表达得更漂亮。这可能是我读书的坏毛病之一,时不时就挑剔一下。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被翻译的情况如何?在和翻译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印象深刻或有趣的故事吗?
韩少功:碰上好翻译家是难得的幸运,比如英国的JuliaLover,到我所在的湖南乡下待过好几天,功课做得扎实,连一些乡间的农具、家具、物种都不放过,如果找不到相应的英文词,就让我画,就去现场看。因此她的《马桥词典》英译也是广受好评的。她在译序中提到,我一开始根本不相信她能译好这本书,建议她放弃。但实际结果是,后来好几位英美读者对我说,他们读下来几乎没感觉到这是本中国的书,可见已译出了无迹可求、出神入化的效果。当然,遇到好译者的概率并不高,尤其是中国作家,要碰上汉学家兼好作家的高人,真是难。有些人只是从英文本草草转译,也从不与作者沟通,甚至想当然地胡删乱改,天知道译成了什么样。违规的情况也有。有两、三位译者一直回避与我见面,因为他们曾协助出版社盗版,大概有点难为情。
中华读书报:有哪些作品被改编成影视或其它剧种?看了《西江月》话剧和《爸爸爸》音乐剧的剧照,我也有些意外,这些作品被改编,是通过什么途径?
韩少功:荷兰MuziektheaterDeHelling改编音乐剧《爸爸爸》,是经过译者联系的,经过了我的授权。不过改编都是再创作,他们采用韩国的音乐素材,对于西方观众可能没什么,在我听来当然很有趣,也有莫名的陌生感。韩国乡景剧团改编《西江月》,在首尔市政厅演出,是刚好被我撞上了,事前完全不知道。现场效果应该说不错,编导既加入了电子视频手段,又加入了韩国传统的鼓乐,构成从头至尾的音乐背景,看得出用了不少心思。这都有效增强了表现力。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创作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人类文明、对人性的思考。无论是《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或是《日夜书》这种思考,在不同的年代是否也有一些变化?
韩少功:当然会有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社会变化在产生逼压,也是自己知识和感受的变化在促成变焦。两种变化交错,差不多就是古人所说“文料”和“文意”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爸爸爸》加上语言哲学,才会有《马桥词典》。《马桥词典》加上中国的城镇化,才会有《山南水北》。正常的作家都在不断地做这种加法。写作就是吸收各种变化的过程,以便把感受积累做成一些“有意味的形式”,做出各种文字的形式感。
中华读书报:作为生于湖南的作家,您的笔下无数次出现过湖南的山山水水和平民百姓。您如何评价地域对作家的影响?
韩少功:一般人会注意作家笔下的民俗、风物、方言等等,那只是最表浅的层次。地域及其历史对作家的影响其实远不止这些。卡夫卡笔下有什么民俗?几乎没有。有什么方言?几乎没有。但他生长在波希米亚的犹太区,而中欧的排犹仇犹最厉害,基督徒们普遍认为犹太人应该对耶稣之死和欧洲的黑死病负责,就在他所在的街区,市政厅大楼上那四个塑像,其中犹太人代表最可恶的“贪婪”,其压力可想而知。因此卡夫卡退守于自我和孤绝,对国家绝望,对政治冷漠,其实有深深的“地域”印记。只是这一点很少被人们注意。
中华读书报:您曾两次与茅奖评选擦肩而过,对中国的文学评奖怎么看?会不会觉得遗憾?
韩少功:我没把获奖的作品读全,但相信大多数是实至名归,受奖无愧的。即便有的写得不够好,但得到一些鼓励也不是坏事。在这个圈子里混,得有平常心。同行们都不容易,这是第一条。不用太多时间,哪怕只有一、二十年,人们记忆中就没有奖不奖了,只会看作品好不好,这是第二条。我也得过奖。得奖时多想想第二条,没获奖时多想想第一条,这就比较好办。
中华读书报:如果请韩老师自我评价在文坛中的地位,您会将哪个点确定为自己的坐标?在中国文坛中,您认为自己的作品有何独特的价值?
韩少功:文学生态需要多样性,大家各干各的事,不必要互相看齐。中国是一个世俗化传统很强的社会,文学从来不缺烟火气,拿电视遥控器摁上一圈,你会发现一个个频道都充满着高分贝的饮食男女和你争我斗,纸媒和网络上也差不多。这大概算不上什么错。但能不能更多关注精神的“上半部”,面对人和人性的一些难点,可能是我更有兴趣的工作。上要着天,要有哲学和美学的远望;下要着地,有老百姓真情实感的和泥带水——我最喜欢读的作品就是这种。至于写作,自己常有力不从心之感,谈不上什么“坐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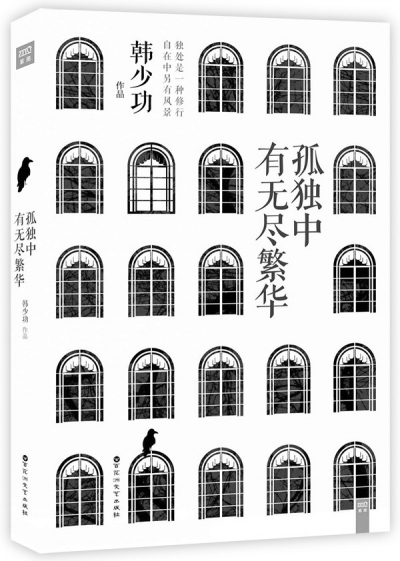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