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辞书编写工作已经五十几年了,而与商务印书馆辞书结缘时间还要长一些。
我的老家在河南省东部一个小县城以东15公里的农村。尽管豫东地处中原,又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但在黑暗的旧社会里,由于水、旱、蝗、汤(指盘踞河南省多年的国民党军阀汤恩伯,借指战乱)四害为虐,那里竟变成民不聊生的穷乡僻壤,以“土、古、苦”(土气、古老、贫苦)闻名于世。我在家乡上学时,很少能接触到什么字典、词典。直到1957年我读高中时,才买到一本《学生小字典》(乙种),部首排列,注音字母注音,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可以说如获至宝,我对注音字母的熟悉与此有关,也由此,我与辞书开始结缘,也与以出版辞书而闻名的商务印书馆开始结缘。
一
1961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读书时,在阅览室的工具书架上见到一部《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它是分作八本装订的“试印本”,后来我曾多次翻查过这部词典。也许是机缘巧合,三年后的秋天,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1977年5月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以下简称“词典室”)工作,时任编辑室主任的丁声树先生发给我们新来室里的同志每人两本书:一本是《新华字典》,另一本是《现汉》(试印本)。我们词典室的工作正是编辑、修订这两本辞书,它们都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1965年《新华字典》新修订本完成后,词典室又在广泛调研、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辑了一本《新华字典》(农村版),1966年春交给商务印书馆。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研究所、出版社停止了一切业务工作,《新华字典》(农村版)未能出版,后来竟然连书稿也不知道了去向。
1970年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全体人员下放到河南省息县东岳公社“五七干校”。开始阶段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劳动,读书学习的机会很少,第二年学部干校全体人员转移至信阳市的明港镇集中搞清查运动,后期才有了较多的时间看书学习。当时见到一本商务印书馆新修订出版的《四角号码新词典》,丁声树先生和我一起翻看,他啧啧称奇,想来,几年时间没有摸辞书,老先生也许是有些技痒了吧。
1972年7月,学部全体人员回到北京。由于社会上急需辞书,国务院科教组领导指示要快些出版《现汉》,以应社会急需。下干校以后,语言研究所原来的办公地址北京西城区端王府原有建筑全部被拆除改建,被别的单位(据说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占据。回京后语言所已无处办公,只能暂时栖身于南小街51号对外文委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大楼的门厅和过道里。由于工作任务急迫,词典室只得暂借大楼南边原文字改革委员会印刷厂排字车间的三间低矮的平房进行工作。
因工作条件限制,没有地方摆放图书资料,而上面要求的出书时间很紧,只好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先利用1965年排出的《现汉》(试用本)稿本的原纸型稍加挖改,1973年5月印制出一定数量内部发行。词典出版后,很受社会欢迎,同年9月又缩印成小32开本增量发行。那时,我们词典室的工作人员蜷缩在陋室中重操旧业,从能购置的报刊、书籍中勾乙词语资料,抄写资料卡片,为《现汉》的正式修改、出版做一些资料准备工作。
实在出乎预料,词典出版还不到一年,“四人帮”竟借“批林批孔”之机,对《现汉》进行打压、扼杀。姚文元直接出马,以“问题相当突出”的缘由,指令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判,当时给《现汉》加上“客观主义”、宣扬“孔孟之道”、是“封资修大杂烩”等罪名,勒令停止发行,全部封存,进行销毁。
那时,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特别是词典室主任、《现汉》主编丁声树先生背负着极大的压力:几十位专业工作者花费17年时间竭尽心力完成的,又是国务院指令编辑的《现汉》竟落得这种命运;商务印书馆也同样承受着很大压力:投入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在排印、校对上下了很大功夫的一部词典竟然得到如此结果。多亏陈原同志想方设法上下周旋,没有将封存起来的《现汉》付之一炬,而是阳奉阴违地以暗中赠与、销售等方式进行消化。
1975年5月,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丁声树先生也被作为专家应邀出席会议。会议决定让语言研究所修订《现汉》和《新华字典》,因语言所词典室人手不够,《新华字典》转交到北京师范大学修订。当时的学部临时领导小组也将修订《现汉》列为学部的重点项目。
年底,根据广州会议精神,语言研究所以词典室为基础,又从古汉语研究室、方言研究室、语音研究室暂调十几位专业人员进行支援,还请来陕西省韩城县燎原煤矿、北京无线电联合厂的20名工人师傅和解放军通讯兵部的三位官兵加上商务印书馆三位编辑同志(实际上只来一位)组建起60多人的“三结合修订组”,对《现汉》(试用本)进行修订。
1976年初,词典室随语言研究所搬迁到位于四道口的原地质学院的主楼办公。修订组在工作中还多次派出小分队到工厂、矿山、部队去征求意见,实行“开门编词典”,这期间我就曾跟商务印书馆的同志及矿工、解放军战士一起先后去过陕西韩城燎原煤矿和北京西郊某中央直属机关的警卫连。在当时极“左”思潮盛行的大环境下,三结合开门编写、修订给词典带来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使《现汉》在收词、释义、举例方面都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来自工厂、解放军的人员先后撤离了修订组,词典室的专业人员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努力清理“文革”中的修订带来的消极影响。即使如此,由于量多人少也难以做到定稿的“齐、清、定”,只能准备着边排校边修改,1977年底将书稿送交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出版部接稿后紧张地进行排版并一次次地校对、修改,我们词典室同志也跟着进行一次次看校样、修改、过录,正是当时所说的“校到底,改到底”。那时丁先生负责组织编辑人员在办公室看校样、改稿,我带领几位同志到商务印书馆将改动的地方过录到在商务的校样和底稿上。商务印书馆领导及汉语编辑室、出版部校对科的同志给予我们密切的配合,为我们提供诸多方便,特别是责任编辑柳凤运同志和校对科的同志一直协同我们工作。我还向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原同志、副总经理林尔蔚同志汇报过有关情况。由于当时承担《现汉》印制工作的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有些字模的字形不规范,词典室还抽出几位同志协同商务印书馆出版部的同志承担改正排印字形的任务,出版部的同志曾多次去湖北省丹江口字模厂铸造新的字模。
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为尽快出版《现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紧密配合,1978年12月,终于使《现汉》正式出版,公开发行。正像老生常谈的“我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那样,《现汉》的出版记录着词典室和商务印书馆的团结协作、紧密配合的紧张、繁忙的工作历程,凝聚着两个单位同甘共苦、努力奋斗的深情厚谊,也是两个单位同心协力打造精品辞书、传世词典的一个范例。
二
《现汉》修订工作完成后,1978年11月词典室开始了由丁先生主持编辑《现代汉语小词典》。1979年3月,《小词典》完稿,交付出版。之后又计划编辑《现代汉语大词典》,经全室人员民主选举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和编委会常务委员会,丁先生任主编,我被选为编委会委员兼秘书。编委会商定了编辑宗旨和规划,制订出编写方案。确定大词典编成后仍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词典室全体人员秣马厉兵,准备投入一场新的战斗。
然而,极为不幸的是,丁先生在此关键时刻患脑溢血住进协和医院,一病不起,使词典室的大词典编写还未正式开始就受到了重创。
吕叔湘所长决定,对词典室领导和业务工作进行调整:停止编写《现代汉语大词典》,改为编写《现代汉语词典·补编》,由时任词典室副主任孙德宣先生改任副主编,负责此项工作。不久,商务印书馆通知《现汉》纸型损坏,需要重新排版。词典室利用重排的机会,对《现汉》稍加改动,出版新的版本。后来又由时任副主任的刘庆隆先生负责编辑《倒序现代汉语词典》。
《小词典》《现汉》重排本、《现汉·补编》和《倒序现代汉语词典》先后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前的排校、修改、过录等事项,两单位紧密配合,分工合作,一如既往。
在纪念《现汉》出版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中,吕叔湘先生指出:“凡是‘现代’词典都要跟上时代,不断修订。”自吕先生调离词典室以后,词典室负责人换过好几届,但无论是哪一届都是把修订《现汉》作为室里的首要任务和中心工作。《现汉》出版发行以后,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修订。每次修订前,词典室负责人与商务印书馆领导及汉语工具书编辑室负责人都要在一起进行深入细致地商讨,制定周密的计划。在排校、印制中紧密配合,使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词典出版后两个单位的有关人员还要分别通读全书,清扫排校中没有看出的差错,尽可能做一些弥补工作,少留下一些遗憾。之后还要召开会议,对词典的编写、修订、排校、出版进行总结、研讨,为以后更好地合作共事做新的更为充分的准备。
除了词典室与商务印书馆进行的集体协作外,我个人也参与了商务印书馆一些辞书的研究和编写、审定工作。
1999年商务印书馆成立辞书研究中心,我被聘为特约研究员。2000年我参与《古今汉语词典》的编稿和审稿工作,这部词典由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组织编写,商务印书馆汉语工具书编辑室副主任李达仁、南开大学教授杨自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楚永安主持;2005年我参与《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的编写、修订和审稿工作,这部词典也是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由北京大学教授符淮青和商务印书馆编审张万起主持。在两部词典的编写过程中,我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同志、校对同志甘苦与共,协同工作,商务印书馆工作同志的认真负责、勇挑重担、坚持不懈的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感动。
我在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的工作中还编辑过《〈现代汉语词典〉五十年》《〈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学术论文集》《学问人生大家风范——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几本书,先后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几本书记述了语言研究所词典室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表现了词典室负责人丁声树先生及其他《现汉》编辑者的敬业和奉献精神,也记录、表现了语言所、词典室和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和友谊。
此外,我还编辑了一本语文知识科普读物《语文应用漫谈》在商务国际有限公司出版,这本小书20年间竟再版了四种版本。在这些书的出版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的责任编辑同志的学识广博深厚,工作认真细致、作风严谨谦虚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2年,在语言研究所、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辞书界的社会组织中国辞书学会成立了。我曾多年担任中国辞书学会的常务理事、副会长和秘书长,参与学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开始的几年,中国辞书学会理事会的办事机构——秘书处设在湖北大学,而会长在国外讲学,代会长在上海,日常工作存在一定困难。2002年,秘书处迁到北京商务印书馆,工作开展才较为便利,一年两次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和一些业务活动都在商务印书馆会议室进行。在中国辞书学会组织的学术研讨会、辞书质量检查、辞书编辑培训班、辞书评奖等各种活动中,我与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在学会工作的同志林尔蔚、杨德炎、王维新、于殿利、周洪波、胡中文、余桂林等一起为祖国辞书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共同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三
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在编写、修订、出版《新华字典》《现汉》几十年的密切合作过程中,还遇到过不止一次到法庭一同状告别人和一同被别人告上法庭的事情,而且长期一同打辞书的版权和编写质量的官司,说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更是再恰当不过。
1986年5月20日,新华通讯社四位资深编辑编写出版了一本《新法编排汉语词典》,严重抄袭《现汉》,侵犯其著作权,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一起就此事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提起诉讼。当时我是语言所词典室的学术秘书,柳凤运同志是商务印书馆汉语工具书编辑室《现汉》的责任编辑,我们一同坐在原告席上与对方庭辩。对方在陈述中对抄袭侵权供认不讳:他们利用《现汉》的内容,进行词条的重新排序成就一本倒序词典,其中原封不动抄自《现汉》的内容竟占该书的90%之多。1987年6月27日,由法院经济庭调解结案,我方胜诉,对方赔偿了经济损失。这次诉讼案因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从开庭到结案用时一个多月,可谓速战速决。想不到七年以后,我们两个单位又被迫陷入了一桩棘手的、旷日持久的版权诉讼案,案件进程一波三折,前后用时达四年之久。
1993年7月15日,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起诉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抄袭侵权。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抄袭侵权问题是1992年被揭露出来的。当时,上海辞书出版社发现王同亿主编、三环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大典》的两个附录《中国历史纪年表》和《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完全是影印自《辞海》的。
1993年初,媒体宣传王同亿主编的《新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新编新华字典》即将出版的消息,5月20日,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三部辞书的首发式,宣称它们是“20世纪90年代的换代性新产品”,从书名和宣传上严重侵害了语言所和商务印书馆的利益。当时,有人发现《新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不少条目释义、例句与《现汉》及其《补编》雷同,引起了语言所和商务印书馆的注意,两单位组织37位专家用了24天时间进行全面查对,发现《新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抄袭《现汉》及其《补编》的词条数量惊人。两单位经过研究,联名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久,《辞海》编辑部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古今汉语实用词典》编写组和四川人民出版社也向同一法院状告同一被告的抄袭侵权活动。
整个诉讼案件经过三个阶段审理。开始是管辖权争议。王同亿认为在北京的法院打官司对他们不利,就暗中做手脚,8月26日将本在北京市百万庄的户口迁往海南省海口,并让人把迁出的时间篡改为6月26日。他们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案件应由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经法院认真调查,认定案发时王同亿不仅户口一直在北京,而且其侵权著作的编写、出版发行也都在北京,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被告上诉,维持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裁定。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还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组成专家组对有关诉讼材料进行比对鉴定工作,1995年11月开始对各案进行开庭审理。1996年12月24日,开庭宣判,确认被告抄袭侵权承担法律责任。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不服判决,1997年1月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7月25日开始进行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诉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侵权案最终胜诉。年底,海南出版社执行判决,在《光明日报》的一角登出道歉声明。
过了三年,湖南省长沙市张明等三人以《现汉》的差错高达两万多处为由,将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告上法庭,原告中就有王同亿编写班子的骨干成员。诉状毫无道理地以王同亿词典的释义为标准,指责《现汉》释义不准确,应视为伪劣产品,要求销毁词典,向读者道歉,并赔偿高额损失。因为书是在长沙购买的,所以官司由长沙的法院受理。
2001年7月11日,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一状告《现汉》的诉讼案,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派出六位工作人员(韩敬体、李志江、周洪波、张稷等)出庭应诉。经过庭上质证、辩论,原告方说不出什么坚强的道理。9月7日,法院再次开庭审理,判决原告败诉。后来又有人以《新华字典》差错率奇高、质量低劣为由将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告上法庭,两单位又努力应对,打赢了官司。
在多次一同作为原告和被告的诉讼中,在与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诉讼的漫长的岁月里,语言研究所领导和商务印书馆领导、词典室和汉语编辑室的同志,同心同德,协同斗争,经过多少次诉讼会商,多少次应对讨论,做了大量扎实的资料工作,所长江蓝生、总经理杨德炎也曾率队上阵,亲自坐在法庭的原告席上,与对方质证。有关人员为保卫版权,为捍卫正义,进行不懈的努力,付出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进行了难以计数的应对工作。千辛万苦,努力奋争,终于赢得官司,取得了共同的胜利。每忆及此,总是让人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也使人更加珍惜两单位历经风风雨雨凝结的历久弥坚、密切配合、荣辱与共的战友情谊。
二三十年来,每到春节期间,商务印书馆领导及汉语辞书编辑室和我们语言研究所、词典室都要举行一次新春联谊活动,双方互致节日问候,互相汇报工作情况,不断地加强联系、协调工作,加深友情。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一个是研究机构,一个是出版机构,为了把我国的学术事业、辞书事业和出版事业做大做强,为了实现强国梦尽自己的努力,我们走到了一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某一方面,成为亲密战友,成为命运共同体。我们要与时俱进,让协作共进的乐章演奏得越来越和谐、越响亮,让两单位间的亲密无间的友谊之花开放得更为旺盛,更加绚丽多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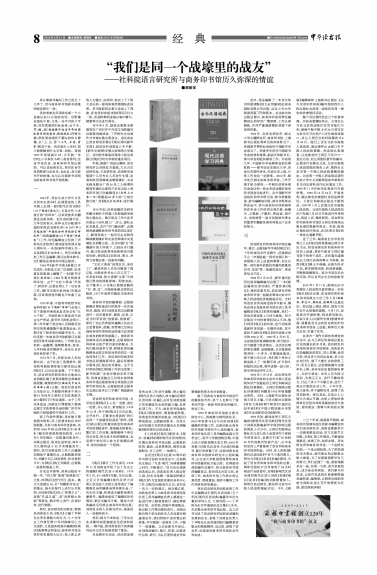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