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他来说,真正的史料不仅是历史研究者所要面对的文献与考古材料,它必须与批评、生活和思想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史料。也就是说,不存在纯粹自在的“历史”,一切历史总是在它的理解(综合)者面前的“历史”。
胡翌霖博士的这本《过时的智慧——科学通史十五讲》很好地继承好了这种历史学视角。的确,相比于一般历史,科学史更容易给我们带来“编年”纪实的感觉。这其中的缘由,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们对于科学的理解。当今时代,科学似乎作为“真理”的化身,把握着解释自然的绝对权威和制高点。任何一种被认定为“科学”的解释似乎就被理解为天然正确,与之相反,那些在科学边缘和对立的解释,则常常被人所忽略和抛弃。与之而来的,科学自身的历史就被理解为一个关于自然真理的“发现史”。
然而,这种历史理解是过于简单的,它自身缺乏历史学的反思。如果按照科学史家巴特菲尔德的说法,把这种“进步史”“编年史”的科学史叫作“辉格史”的话,那么这种“辉格史”观背后常常预设着一种对于科学的理解(即上文所说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历史不是单纯的客观的事件集合,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言:“历史是一种说明的事业,一种导致理解的事业,因此历史不仅必须表现各种事实,而且也必须表现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纵观全书,胡博士的这本《过时的智慧》是对“辉格史”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超越。
可以说,与传统的编年化的“辉格史”相生成的是“实证主义科学观”。那么,《过时的智慧》一书也必然包含着一套与“实证主义科学观”不同的对于科学的理解。关于这一点,胡博士是有着充分的意识的,在第二讲的第一节,胡博士便清晰地提出了“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并且以这一问题作为潜在引导全书的线索。
因此,对于《过时的智慧》,我的第一句评论是:这是一部有着充分编史学自觉的历史著作。它不仅着力于历史叙事,更是力图通过历史的维度重新反思和理解我们当下所遭遇的“科学”。
如果我们拒绝实证主义科学观,拒绝将科学理解为对自然规律的客观描述和反映,以及可验证的知识的话,那么科学又是什么呢?然而,作为一部历史著作,《过时的智慧》一书并没有直接地辨析和讨论这些哲学问题,而是通过历史学的叙事隐微地显示出答案。胡博士的研究进路是关注科学思想、概念自身的历史构成。
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科学不是由概念和命题组成的知识系统。概念、命题是组成科学知识的基本语言和元素。然而,这些元素和语言本身却是具有历史性的。透过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概念自身存在着演变的历程。那些描述和构造自然的希腊概念经由罗马和中世纪的变化,经历了科学革命的洗礼,可以说是面目全非或者说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背负科学活动的基本载体是概念,它意义的变化即是科学内在的、依照于自身逻辑的发展与变化,依照于自身和突破自身的活动。在《过时的智慧》一书中,对于概念的历史分析最为精彩的两个例子是对于“力”“原因”概念的历史辨析,以及关于古今数学思想结构的分析。
在科学革命发生以前,“力”常常是指一种内在的、有生机的、指代意志的东西。它好似恩培多克勒的“爱”概念一样,是运动变化发生的原因。而“机械学”常常表示一种外在的、受迫的、冷冰冰的东西。然而,经过牛顿的工作,“力”的概念与“机械学”的概念统一为一体。这两个概念的融合和变迁实际上牵涉到整个世界图景的变迁。古代的“力”概念所描述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谓“自然学”(物理学)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事物自身运动的原因来源于自己,事物自身有一个自在的“本性”,物理学的使命就是如其所是的研究事物本身的“本性”。然而,科学革命时期机械论思想的兴起,或来源于基督教的影响,彻底打破了这个自在自为的领域,事物运动的原因可以来自于事物本身之外。内在性的与外在性的界限被打破了。新时代的“力”概念导致“力”恰恰成为“因果关系”发生本身——当作为原因的施动者给予了作为结果的受动者的一个力时,两者就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力是因果关系的传达而非原因本身。牛顿的“力”概念既残留了内在性理路的“原因”概念,又完全按照外在性理论的机械论思维来构建事物的关系。
正如胡博士在文中所讲,在20世纪后半叶,反辉格的历史研究已经逐渐成为科学史的主流,但唯独数学是个例外。很多数学史的写法仍旧是辉格的,对于数学的内部的概念变迁鲜有发掘。从常识出发我们也很难设想数学存在着概念变迁的空间。然而,借助雅各布·克莱因(Jacob·Klein)的研究成果,《过时的智慧》一书探究了数学从事物中的起源以及经由韦达、斯台文完成的符号化意向变革。“数”的出现必然蕴含事物同一性的把握,计数活动要以一种对“单元”的理解为前提。在希腊人那里,所谓数总是“确切数目的确切事物”,对于数的把握总是无法脱离对于具体事物的把握。然而,韦达却提出了与未知数相区分的参数概念,胡博士将这种符号代数的出现称作为“抽象的抽象”。的确,如果我们把希腊人对于数定义理解为对于事物的抽象,那么,这种符号代数完成了对于抽象事物的进一步抽象,它不再针对特定的事物,不再指代并把握事物,而成为纯粹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活动了。实际上,这种符号的抽象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X”的出现,它作为一个数,同时却又不是任何一个确定的数,它并不意指确定的对象。这种不是任何确定对象的对象,在希腊人那里是完全不存在的和不可理解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二阶的抽象更加高级。克莱因认为,这种抽象来源于笛卡尔区分“心灵世界”和“外部世界”,它预设了我们的心灵与这个世界的疏离性,我们并非直接接近这个世界,而是通过这种“抽象的抽象”来接近世界。数学在近代发生的变迁,同样伴随着一套意向方式与概念的转变。
对于概念、意向方式的关注常常会带来观念论的误解。对于思想内部的特别关注通常会被看作为陷于观念论的框架。从概念到概念,似乎历史发展的进程仅仅是纯粹理念的自行展开与推进,而与社会、经济、政治和复杂的技术生产环境全然没有关系。然而,在这本《过时的智慧》绝非如此,对概念自身的关注同样牵涉着对于所谓“外部环境”的关注。这种对“外部环境”的关注并非是一种时代语境的一般介绍和铺垫,毋宁说,胡博士将所谓的“外部环境”看作概念构成的整个先验条件。所以说,这不仅仅是一部纯粹观念史,更是一部经验-先验的观念构成史。在此书中,常常可见对于这种外部技术环境的分析,从希腊的“场所”到中世纪的大学,再至近代的工业革命。但对这一要点和联系最为精彩的阐发当属对印刷术的分析。
通常地,印刷这一技术的出现仅仅被我们看作为复制效率的单纯增强,难以从其产生的技术环境角度去理解。借助著名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的洞见“媒介即讯息”,胡博士全面地分析了“印刷术”这一外在技术所造就的新的媒介环境。印刷术所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复制的效率,它同时改变了经验记录的保存,推进了知识的公共化,建立了基于文本秩序的新的自然秩序,并且通过“文本知识”构筑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那道帷幕。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胡博士看来,这些所谓的“外界环境”的经验变化,恰恰形成了“内在的”概念运动的前提和动力。依循这条经验—先验的构成模式,胡博士的进路打通了“内史”与“外史”的本质区分,并且强调外部技术环境与内部概念本质的联系。
作为一部通史著作,通史之“同一性”需要始终关注,通史不是编年纪实的拼凑。正如前文所言,历史本身追寻着理解,而通史需要不断关注着如何获得整体的理解。此书分为十五个独立专题章节,从古到今,由西到中,看似眼花缭乱。实际上,这种叙事兼顾了历时的线索,但又不是单线式线性因果(cause)线索,而是一个关联性的、理解要素化的星图。通过对于阿拉伯与中国文明的引入,呈现出理解科学这一希腊产物的特殊性。对于先验性技术环境的强调,阐述出世界与观念的交互空间。对于科学历时性的追溯,清晰地勾勒了科学自希腊至今的变迁与蜕变。这一系列的工作共同构成一个立体化的、结构化的、嵌套性的阐释结构,它不是线性的因果解释,而是整体的理解要素分析。实际上,这种整体而富有厚度的解释结构也是来自于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正如吴国盛教授在序言中所写,此书在思想来源上相当程度上来自于“科学通史”的教学工作。
所以说,这样一本体量不厚、语言平实的通史书籍,实际上包含深厚的学术基础和深刻的历史洞见。因而,这绝不是一本在智性上简单的书籍。同时,它语言直白而生动,绝没有因为洞见之深而拒人千里之外,它引人入胜,必定能为思想之上的有心者带来助益。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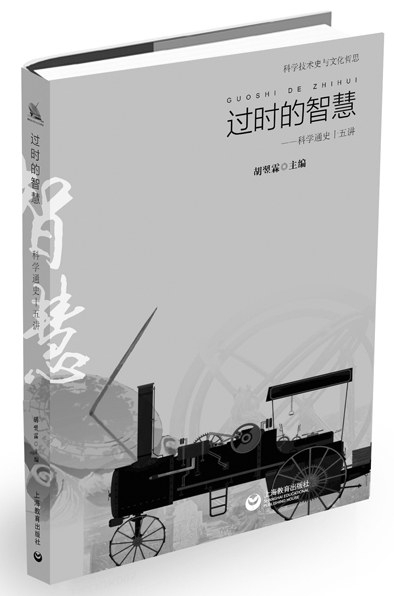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