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来如山倒,除了求医问药,我们真的毫无办法?当衰老到来时,除了迎接死亡,我们只能得过且过?面对疾病,我们总是盲目地听从医生的安排;面对衰老,我们则不假思索地把自己交给命运。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其他选择?在《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中,积极心理学奠基人埃伦·兰格为我们揭开了医生和心理学家没有说出的真相,激励我们成为健康学习者,活出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从托尔斯泰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漫不经心地把自己托付给医学世界,就像他早先把自己托付给社交世界和物质世界一样。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对我们的健康并不好。
如果我们认为某种疾病是不可治疗的或者无法控制的话,那么我们也许绝不会尝试去治疗它,因为我们认为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医学界征服过的大多数疾病,在某个时候都曾被认为是不可控的,实际上,当时它只不过是不确定的,而这一切转变都是从认识上的转变开始的。
调整心态,掌控健康。在30多年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有关人类心理的重要事实:追求确定性是一种可怕的心态。它会让我们的思维抵制可能性,并与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隔离开来。当一切都确定的时候,我们就无从选择。
对形式的关注超过对内容的关注,这一特点在我们身上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很少质疑医生的嘱咐。医疗界也很少劳神地要求我们遵从他们的“命令”,他们只是给出“命令”。与其说他们给出的是“命令”,还不如说是建议,他们只是期待我们不怎么质疑就接受这些建议。
诊断并不是没有用,而且我也绝不是建议人们像疑病症患者那样过度警惕。我的建议是,用心关注我们的身体,这样,我们就能在出现大问题之前发现那些细微的变化,并将其处理掉。
成为合格的学习者,要求我们把那些从世界中学到的所有东西都尽收眼底、了然于心,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大事情,而且要关注小事情,并且要明白,有时小小的变化就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经常觉得某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减掉45斤体重,多么艰巨的任务!但是,我认为,很少有人觉得减掉28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减掉28克的信心。
看过医学课本、咨询过医生之后,他的情况加重了。当他每天将自己的身体同前一天相比时,几乎觉察不出差别,这样他可以欺骗自己说,恶化速度并不快。但是,当他向医疗界寻求建议时,一切好像都在恶化,而且是在迅速恶化。然而,不管怎样,他还是继续咨询医生。那个月,他换了一个医生,也是一位著名专家,但是,这位著名专家所说的话几乎和第一位医生所说的一模一样,只是提问的方式稍微有所不同。听过这位著名专家的建议之后,伊万·伊里奇的疑虑和恐惧加重了……体内的疼痛一直折磨着他,而且每次发作起来,持续时间似乎越来越长,程度也越来越严重。他嘴里的味道变得越来越古怪,他自己都觉得这个味道很恶心。他的力气和胃口都在变弱。
——托尔斯泰《伊万·伊里奇之死》(TheDeathofIvanIlyich)
医疗界并没有给伊万·伊里奇提供多少帮助。他所咨询的那些知名医生,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治好他的病,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或者给他提供多少情感支持。他们只是让他不断地尝试各种疗法和药物,但是结果证明这些疗法和药物没有一个有效。托尔斯泰的小说向我们展示了许多人都能想象得到的一幅图景,患病之后的最坏情况莫过于此:患上一种莫名的、不可治疗的疾病,身体每况愈下,内心感到无助。
从伊万的挣扎中,人们可以挖掘出很多意义,而我看到的是:伊万不是一个很好的病人——不管他对医疗界多失望。从托尔斯泰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漫不经心地把自己托付给医学世界,就像他早先把自己托付给社交世界和物质世界一样。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对我们的健康并不好。医生兼作家杰尔姆·古柏曼(JeromeGroopman)曾经说过:“我们医生需要你们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我们需要你们质疑我们,在我们自以为了解了很多的时候打击打击我们,在我们误人歧途的时候提醒提醒我们……当医生真的不容易,但是,当病人更不容易。”伊万从来没有接受过这项挑战。
如果说做病人很难,那么我们根植于健康和疾病方面的心理定势会让这一角色变得更难扮演。1891年,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在论感觉时写道:“在婴儿的意识里,任何感觉都是一团模糊、嗡嗡作响的混沌,不管这种感觉是来自眼睛、耳朵、鼻子、皮肤还是内脏。”后人经常引用这句话,用于支持减少不确定性从而让生活变得简单的观点。我们大多数人都毫不迟疑地赞成简单,即使在我们抱怨自己的生活太过简单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密切关注那些在我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东西,尽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结果发现,正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发挥了关键作用。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为了方便理解,我们都习惯贴上一个标签,这样,我们就不会从其他角度看待这件事情了,那些角度也许一样有意义,并且也许更有用。相较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更喜欢确定的看法,只有在连专家也不能确定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沮丧。
在逆时针研究之后,我和我的学生们又继续做了很多研究,以探索健康与心理定势之间的关系。我们最近做了一项研究,考察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像那些比我们年长或者比我们年轻的人一样生活,那么我们的生理年龄是更接近那些人还是更接近我们的同龄人呢?我们发现:同一般女人相比,那些嫁给比自己年轻很多的男人的女人活得更久,而那些嫁给比自己年长很多的男人的女人死得更早。对于男人而言,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即使男女的预期寿命并不一样。心理学家伯尼斯·诺嘉顿(Ber⁃niceNeugarten)指出,“社会时钟”深
深地影响着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用一套内隐信念来度量生命,认为每个年龄阶段都有与其适宜的态度和行为(10岁的人有10岁的样子,20岁的人有20岁的样子,以此类推)。我们这样推理:如果我们按照配偶的年龄来调节自己的社会时钟和生物时钟的话,那么就可以改变一切。这样的话,配偶中年老的一方会变得“更年轻”、比预期寿命活得更长;而年轻的一方会变得“更年老”、比预期寿命活得更短。
其他研究者发现,女人不大可能在生日前一周去世,而更可能在生日后一周去世。男人呢,正好相反,不大可能在生日后一周去世,而更可能在生日前一周去世。戴维·詹金斯(DavidJenkins)在评论中说,这一发现意味着男人和女人“用不同的方式将现实打包”。我们将信息打包的方式,或者说我们将信息结构化的方式,对我们自身具有极大的影响。比如,在自己生日前夕,女人满怀希望,期待着庆祝,而男人似乎就不怎么在意。
在最近一项有关人格、衰老、寿命三者关系的研究中,我的第一个学生——心理学家贝卡·利维(Bec⁃caLevy)——及其同事发现,与我们以及我们的医生所关注的那些典型生理因素相比,人们的心态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大。他们的研究被试有650多人,主要来自牛津和俄亥俄州。1975年,这些被试回答过一份调查问卷,上面列出了一系列有关衰老的或积极或消极的看法,比如,“随着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随着我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会变得越来越没用”“我现在和年轻时一样幸福”,等等。他们可以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这些看法。研究者根据被试的问卷得分将其分成两类,一类对自身健康和衰老持有积极态度,另外一类则持有消极态度。
20年后,研究者考察了被试的问卷得分与其寿命的关系后发现,平均而言,那些对自身健康和衰老持有积极态度的人的寿命,比那些持有消极态度的人长7.5年。仅仅保持积极的心态所取得的效果,就比降低血压或者减少胆固醇所取得的效果大,通常情况下,后两种方法只能让寿命延长4年。保持积极的心态,也比积极地锻炼身体、维持恰当的体重、不吸烟更管用,后三种方法只能让寿命延长1-3年。1999年,心理学家海纳·梅尔(HeinerMa⁃ier)和雅基·史密斯(JacquiSmith)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这项研究考察了死亡率和17个心智状态指标(包括智力、人格、主观幸福感、社交能力等)的关系,结果也发现对衰老的态度是影响寿命的主要因素。他们使用的数据来自柏林老龄化研究项目(BerlinAgingStudy),该项目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收集了500多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信息。
看完这类研究的结果,有人可能会想:“很有意思,但是和我没有多大关系。”信念也许是决定寿命的最主要因素,这一观念和我们“知道”的那些事实太不一样了。我们必须把那些漫不经心了解到的事实放在一边才能理解,当我们知道某个事物是什么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个事物不可能是什么。没有哪门科学可以揭示,某个事物是不可控的,不管这门科学有多高深。所有的科学至多只能告诉我们,某个事物是不确定的。
理解不可控的世界和不确定的世界之间的区别,能够带来很大的好处。某个事物没有发生,并不表明它不能发生,只是意味着人们还不知道让它发生的方法。如果我们认为某种疾病是不可治疗的或者无法控制的话,那么我们也许绝不会尝试去治疗它,因为我们认为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医学界征服过的大多数疾病,在某个时候都曾被认为是不可控的,实际上,当时它只不过是不确定的,而这一切转变都是从认识上的转变开始的。
如果信念影响着我们的健康,那么我们当然应该学会影响自己的信念。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做出一个关键的选择——必须选择相信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健康。我无法保证我们总能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是正确的,那么就一定能征服那些“不可控的”因素;如果我们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也能在追求可能性的过程中获得其他奖励。然而,如果我们选择不相信,那么我们将会蒙受巨大的损失——至少享受不到尝试的乐趣,而且还会丧失对自己的健康实施有意义的控制的机会。
调整心态,掌控健康
在30多年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有关人类心理的重要事实:追求确定性是一种可怕的心态。它会让我们的思维抵制可能性,并与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隔离开来。当一切都确定的时候,我们就无从选择。如果没有怀疑,就没有选择。当我们信奉确定性的时候,就看不到世界的可能性,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应该信奉的是不确定性,特别是有关我们健康的不确定性。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获得回报:为练习掌控我们的生活创造了机会。
我们通常意识不到心态对自身的限制。只要想想下面几条常见且为我们大多数人所持有的有关健康的信念就知道了。
我们的身体要么健康,要么不健康。就像我们喜欢把心灵和身体想象成相互独立的两极一样,我们也喜欢想象,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我们的身体要么是健康的,要么是不健康的。当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时候,我们认为不需要对它投入多少注意力;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能找到治疗这一疾病的权威信息。不管信息是来自一位专家还是传统智慧,我们都期待它可以成为自己的健康处方。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偏爱确定性,而不具体分析健康到底是什么。
医疗界懂的最多。总体而言,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医生当然比我们懂的多。但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自己。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需要将医生的观点与我们自己的看法——其他人无法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提供这些看法——结合起来,加以利用。
健康是一种医学现象。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把世界过度医学化了。如果我们体验到悲伤,那我们就说自己抑郁了;如果我们通宵达旦地玩游戏,那我们就说自己上瘾了;如果我们的睡眠时间少于8小时,那我们就说自己失眠了;如果我们不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那我们就说自己得了拖延症(尽管每次在我们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必定有其他事情还没有做)。为什么我们觉得给自己贴标签没有什么不妥?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呢?我们漫不经心地给身体体验贴上医学标签,以致身体的任何反应都成了一种医学状况或者症状——做某事有困难就是在某方面有残疾或缺陷。在把这么多体验都归结为医学状况的同时,我们限制了自己对这些体验的理解(这确实是我们自愿如此,因为我们认为医生对其有更好的理解),结果使得医学状况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为了重新掌控健康,我们需要明白自己不知不觉地放弃掌控的原因。在做专念讲座时,我经常问:“谁知道自己的胆固醇水平?”这个时候,通常有个最近体检结果很好的人举手回答。在他说了自己的胆固醇水平后,我问他最后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我每次碰到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一般在一个月以前。于是我说:“那么,自那以后,你就没有再吃东西、再锻炼吗?如果你再也不去体检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你会健康地死去啰?”这话总能引起一阵笑声,但是,实际上,它道出了一个严肃的事实。医疗界给我们提供了胆固醇水平之类的数据,而我们总认为这些数据不会变化(至少在我们下次体检之前不会变化)。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健康状况,并不是由过去的健康状况决定的。
我们漫不经心地对待自己的健康,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日后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一直忽视自己的健康状况,直到我们认为自己需要成为一名健康专家。我们应该改变以上做法,一边用心地学习与健康有关的知识,一边密切关注自己的健康。
漫不经心地答应请求
我们不知道,在与世界以及他人进行互动的时候,我们会多么漫不经心。我们通常不去质疑什么,只要它符合一些已有的信念或者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即使它很荒谬。
1978年,我和我的学生阿瑟·布兰克(ArthurBlank)、本齐翁·班查诺维兹(BenzionChanowitz)做了一个研究。在研究中,我们走近排队等待使用复印机的人,问他们我们能否插个队。我们请求允许的方式有以下三种:“我能先用一下复印机吗?”“我能先用一下复印机吗?因为我要复印。”“我能先用一下复印机吗?因为我很急。”就像通常可以想到的那样,使用第二种、第三种方式的话,排队的人更可能允许我们插队,因为我们给出了一个理由。有趣的是,使用第二种方式得到允许的可能性几乎和使用第三种方式一模一样,而第二种方式所说的“因为我要复印”几乎不能成为插队的理由。毕竟,如果我们不用复印机复印的话,那用它干什么呢?第三种方式所说的“因为我很急”是一个能说得过去的插队理由,但是,使用此种请求方式获得允许的可能性并不比使用第二种方式大多少。
我们下结论说,人们之所以漫不经心地同意“我能先用一下复印机吗?因为我要复印”这个请求,是因为里面包含一个“因为”,在句子结构上给出了一个插队的理由,尽管在内容上并不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只要给出一个理由,人们往往就会漫不经心地答应你的请求,不管这个理由多么空洞。这看起来很愚蠢,但是,当我们漫不经心地接受一条信息并把它当作事实的时候,当我们把建议当作处方的时候,当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医生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性质其实与上述做法差不多。我们不关注内容,是因为我们漫不经心地把注意焦点放在形式上了。尽管在无关紧要的社交情境中,这样做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在我们的健康面临风险的时候,这样做就很要不得了。
对形式的关注超过对内容的关注,这一特点在我们身上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很少质疑医生的嘱咐。医疗界也很少劳神地要求我们遵从他们的“命令”,他们只是给出“命令”。与其说他们给出的是“命令”,还不如说是建议,他们只是期待我们不怎么质疑就接受这些建议。而我们呢,确实是这样做的。就像在“复印”研究中我们给出一个形式上的理由“因为我要复印”就能使得别人答应让我们插队一样,在看病时,只要医生给出任何形式上的理由——内隐的形式理由是“因为我是医生”,外显的形式理由是“因为这种药物能够减轻或者消除症状”——就能让病人乖乖地服从“命令”。
这并不是说医疗界不值得信任,这只是说,很多医学问题本身是不确定的,尽管有些医生把它们说成确定无疑的样子。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因为很多医学问题本身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确定而不参与与我们健康有关的决策。
诊断不是答案,而是起点
多年以前,我和我的一个学生安妮·贝内文托(AnneBenevento)研究了给胜任感贴标签所导致的效应,我们把这一效应叫做“自我诱导依赖”(sel-induceddependence)。在一系列实验中,我们发现,“助手”之类的头衔会明显地削弱自己的能力。推而广之,当我们把自己看作不如医生有见识的病人的时候,同样的效应也会出现——我们的能力会减弱。另外,当我们把控制权拱手让给别人的时候,往往就很难把它要回来了。结果,我们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即使我们并非如此。
例如,诊断就是标签。诊断告诉我们,某些感觉意味着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加以解释;诊断告诉我们,一系列体验是慢性的还是天生的,某个衰弱迹象是意味着复发还是恶化;诊断告诉我们,要期待什么,要小心什么,疾病是不是可以治愈;诊断告诉我们,某种疼痛是一种症状还是一种副作用,或者仅仅是一种感觉;诊断告诉我们,要担心什么,应该学会忽略或者忍受什么。诊断是医学决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就像其他任何标签一样,诊断把不确定的现象看成确定的,只是提供了一个一维视角让我们理解一种多维现象(诊断并没有把所有维度都考虑在内)。诊断描述的是很多个体在一般情况下的体验,并不代表某一个体在任何一个时刻的体验。鉴于我们的身体、感觉和体验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所以,给任何一个诊断所描述的那些数不清的表现贴上一个标签,或者说,用一个标签就把一个人的身份、状况、体验或者潜力全部概括,是极其误导人的。就像对待其他标签一样,我们最好不要把诊断看作答案或者解释,而是应该看作起点,让其指导我们进一步追问其他问题。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却百分之百地相信诊断,并且直接因此而丧失了希望。
只有质疑回应医学信息的传统方式,我们才能变成有效的健康学习者。如果我们认识到,医生所知道的只有那么多,医学所揭示的并非绝对事实,不可治疗实际上意味着不确定,我们的信念以及大部分相关的外部世界都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就做好了寻找新方式的准备。
诊断并不是没有用,而且我也绝不是建议人们像疑病症患者那样过度警惕。我的建议是,用心关注我们的身体,这样,我们就能在出现大问题之前发现那些细微的变化,并将其处理掉。专念与警惕有很大不同,它是一种适度的觉醒状态,而不是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这种态度会阻碍我们更加全面地体验自我——关注我们身体的任何部分(或者和我们的身体有关的其他任何事情)。
在漫不经心地学习时,我们不会去细究两样事情——我们或者别人实际所做的、我们所认为的——之间有什么差别。我们从一个单一的视角解释经验,但却忽略了可能还有其他的解释方式。在专念地学习时,我们明白,从无数个不同的角度解释经验总是可以获得新的信息——从不止一个视角解释经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做法可以让我们仔细思考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以及自己是如何知道这些“事实”的。在具体经验水平上,每个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己可以从经验中学习?也就是说,如果事件本身不一定重复发生,那么一个过去的事件怎么能够告诉我们一个未来的事件是什么样子的呢?某一次的疼痛能够教会我们什么呢?
有一次,我和两个朋友边走边聊,其中一个朋友向我讲述了几年前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件可怕的事。我不记得事情的背景了,只记得她说自己站在一个瓷质马桶上,马桶碎了,她摔倒了,马桶碎片在她腿上划了一道很长的口子,医生为她缝了106针。她说自己从这次惨痛的经历中吸取了一个教训,我问她是什么教训,她回答说:“不要站在瓷质马桶上。”但是,我认为,教训可能是下面任何一个——“要谨慎些”“不要试着自己修理东西”“在尝试新东西时,要确保旁边有人看着”“不要尝试任何新东西”“在修理东西时,要穿上结实的衣服”“不要害怕尝试新东西,因为身体具有神奇的自我修复能力”“我承受得住打击,我不会被打败”,或者“减肥吧,免得下次又把马桶压坏了”。我可以不停地列举下去,但是我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所以我没有继续。我不是说她给出的答案是错的,而是说那只是看待那次经历的一种方式而已。我们最好专念地体验学习过程,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从经验中学习。
经验极可能是一个蹩脚的老师。当认为自己正在从经验中学习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学习的呢?我们回顾经验——一种本来可以从无数个角度加以理解的经验——然后把一种关系强加在两件事情上(即使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建构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旦把这种关系铭记在心,我们就会不断地去验证它,从而排除了其他任何可能的解释。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经验不过是向我们“传授”那些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有时,昨天的进步是今天的失败。如果我们摔断了腿,目前正在恢复中,我们可以试着拖着这条腿走路。第一天,我们觉得很辛苦,但是设法走了很远。正因为第一天走了很远,所以,第二天,我们走起来就不觉得那么费力了。我们应该已经明白,当再次面对同样的事情时,过去的经验可以让我们放弃,也可以让我们觉得更容易、激励我们更加努力。成为合格的学习者,要求我们把那些从世界中学到的所有东西都尽收眼底、了然于心,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大事情,而且要关注小事情,并且要明白,有时小小的变化就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经常觉得某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减掉45斤体重,多么艰巨的任务!但是,我认为,很少有人觉得减掉28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减掉28克的信心。
(本文摘自《生命的另一种可能》,[美]埃伦·兰格著,中国工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2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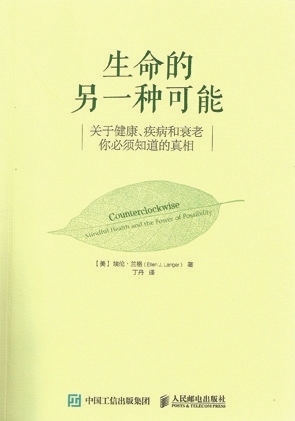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