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天国里,那些璀璨的星辰总是能够穿越历史的烟尘向我们发出永恒的光辉;在这光辉的照耀之下,我既珍重现世的幸福,又超拔了尘世的苦难,建立起自我的自由的宁静的恬美的精神世界。人类需要文学经典,就像需要阳光、食物和水一样。同时,对文学经典以及阅读自由、阅读机会的渴求,也足以代表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层次。经典的生成问题以及经典的阅读、传播和接受问题,实际上也是各个时代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时代显得比较异常。近年来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和论争时有发生,并成为文学研究界普遍关注的热点。
7月,原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教授新著《论经典》发布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而此前半个月,我已经得到了詹福瑞先生的签赠本。据我观察,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明显呈现出三线分布的研究格局:首先是一线研究,即直接研究作家作品;其次是二线研究,即研究作家作品的传播史,或曰影响研究或接受研究;复次为三线研究,即是研究的研究,实际是古典文学研究之学术史。这三线研究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形成了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多层次格局。而从研究方法和治学路径上看,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也表现在三个方面:理论形态的研究,文献形态的研究以及理论、文献兼融的研究。《论经典》则属于既与三线有密切联系而又超越三线的理论形态的研究。这种研究难度很大,当然也很有意义。面对当代社会传统文学经典已被边缘化的残酷现实,詹福瑞教授对文学经典,特别是与文学经典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十多年的苦心孤诣凝结为这部《论经典》。
《论经典》乃是一部关于文学经典的沉思录,一部关于文学经典的对话录,学者的理性、儒者的理想和诗人的激情在此书中融为一炉。王念孙说:“学问须有灵性,苦功而无灵性,是人役也。”(《高邮王氏治学且要语》,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苦功与灵性使得这部书亮点密布,读来饶有趣味,发人深思,引人入胜。这里,我们试为读者揭橥一、二,以彰明此书之现实意义和历史关怀。
其一,于丹缘何把大鹏变成麻雀?
捍卫经典的尊严,捍卫文学的尊严,这种严肃的文化态度贯穿全书。“考察经典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关系,重要的不是要看大众传媒是否传播了经典,而是看其如何传播经典。”(第214页)在此方面,他对《于丹〈庄子〉心得》的批评最为典型。对于这本《心得》,詹福瑞指出,“于丹讲《庄子》,为了使《庄子》的思想嫁接到当代人的生活实用,则把《庄子》的类似于《逍遥游》中的大鹏之思,降低为枋榆间的蜩与学鸠之飞。”“庄子逍遥游的实质就是要超越现实与自我,而于丹之所讲落脚点恰恰正是在现实与人的自我。抛弃眼前的遮目一叶,不过是为了谋取认得更大利益而已。所以于丹教给读者的不是超越,而是讨巧,是谋求更大利益的机心。这岂不与庄子的精神超越和由超越获得的自由精神南辕北辙!”批评似乎尖刻,但是,他对于丹似乎还有一种“了解之同情”:“从作者的讲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面向的是职场的青年,并且把抚慰这些受众的职场失意和工作带来的压力作为讲述的目的。他们既要贴近这些读者的关切,同时还要照顾其接受能力,因此,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尽量用穿插的小故事来调节气氛,如同戏曲中的插科打诨,都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争取有更好的收视率。而其付出的代价,就是减损经典的内涵,降低思想的高度,甚至曲为之解,把庄子这只薄天而飞的大鹏变成抢树数仞的麻雀。”伟大作家与伟大作品的精神核心就是其“不可摧毁性”(indestructibili⁃ty),任何人对经典的歪曲都是徒劳的,譬如,“文革”期间刊行的《论语批判》和《孟子批判》之类,并没有摧毁这两部伟大的儒学经典。误解经典或曲解经典的过程不仅是媚俗的过程,也是毁人不倦的过程,伪文化伪国学的罪恶无过于此。
其二,“样板戏”能够成为永恒的经典吗?
“权力影响经典的另外一种手段,是试图制造经典和神圣化经典。”“在中国,最典型的莫过于上个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权力机构推出的八个样板戏。”“1966年11月28日,在中央文革召开、万人参加的‘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宣布,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部作品为革命样板戏。1967年5月,八个样板戏齐聚北京汇演,直到6月中旬,演出达218场,观众达到33万人。”“时间过去了四十余年,当年红极一时的样板戏,今天又被命名为‘红色经典’,继续在舞台上演出。”(第178-179页)那么,这些样板戏“今后是否可能成为可以流传于世的真正的经典”?詹福瑞认为,“要看它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是否具有普适价值”(第180页),“经典的普适价值在于把一个民族、甚至个人的经验连接上人类经验,使经典不仅具有民族性和作者的个人性,同时具有超越民族性和个人性之上的普遍意义。”(第52页)以权力干预经典的构建与传播,历史的教训既荒唐而又沉重。在这种意义上,本书对于当代中国的人文建构,政府的文化决策以及出版事业和文学教育事业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参考意义。
詹福瑞的文学经典学充满了辩证法的精神。他分析问题不仅能够一分为二,而且善于一分为多,尤其善于在动态的变量中寻觅、发掘不变的东西,在不变的东西中捕捉到种种动态的变量。“经典阅读的关键亦是发现,而这种发现即来自阅读时对前见的证明、更是对前见的打破,为新的前见的建立打开了更深邃、更广阔的视野。”(第115页)“如果我们把经典文本称为经典原生层的话,经典经过历史累积而形成的读者阅读的前见,就是经典的次生层。次生层因依经典的原生层而产生,并且随着时间不断增加,仅仅包裹在经典原生层周围,构成经典完整的生态圈。经典正是在这种不断的重新阐释中得以流传,并且生生不息。”(第135页)“经典的累积性所造成的阅读前见,也会影响读者对经典文本的阅读和接受。所以就有一个如何对待经典的累积性前见问题。或者剥离外在的前见,回归文本;或者阅读经典文本,同时也接受前见;不仅如此,对前见的剥离、接受也总是有所选择。而读者在阅读经典时剥离什么前见,保留或认同甚至强化某些前见,都决定于读者阅读时的当下性所形成的与经典次生层的价值关联。”(第160页)这些精彩的观点都显示了一位杰出学者的卓越智慧。
在1911年以后,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儒家和道家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在,但是儒家经典《十三经》,除《尚书》《周礼》《孝经》等逐渐变为只具有认识价值以外,以上所说的几部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作为思想资源依然对中国社会发生着重要影响,其经典地位并未因社会变迁而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其原因即在于这些传世经典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里边保存着我们前面所说的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共识,并且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由此可见,不走偏锋,遍观衢路,兼容并包,打通古今中外,将诸家理论融为一炉,并巧妙吸纳,出以己意,是詹福瑞治学的突出特征。
《论经典》在学术上有厚度,有力度,有强度。书中有些地方点到即止,有些地方欲说还休,有些地方化整为零,明眼人均可见出作者的匠心和苦心,处处闪耀着文化信仰与学术信仰的光辉,相信它一定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伴随着那些不朽的文学经典走向未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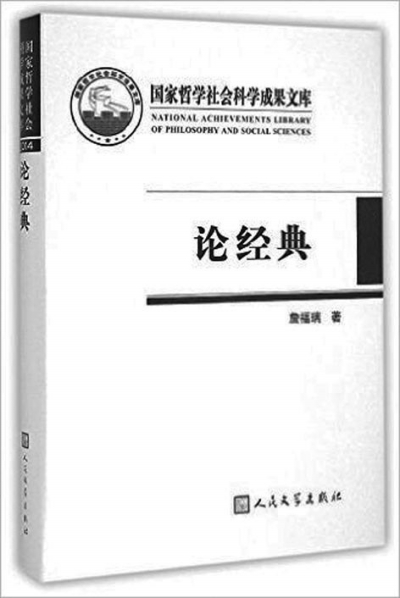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