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空一声鸽哨使我的心宁静,我不大敢细看后楼阳台上杂物堆积中的简陋鸽舍。我其实是因久已远于胡同文化才更想写这题目的。借了文学的材料去构筑胡同形象,其中有些或近于说梦。作家因薄雾微烟而大做其梦,研究者也不妨偶尔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这是鲁迅那篇著名的《秋夜》。我知道自己做的是平庸最没有出息的梦,其中没有悲歌慷慨,血泪飞迸,一弯冷月下的铁马金戈;有的是浮荡在远树间的炊烟,灶下的火光,碗盏敲击中最平易庸常的人间情景。
——赵园
普通北京人的找乐所欲不奢,所费不靡。不但讲“迎时当令”,也讲因陋就简。他们的满足并不必建立在庞大坚实的物质基础上。
《红点颏儿》开篇就醒神:
坛墙根儿,可真是个好去处。
外地人或许对此有神秘感,其实这“坛墙根儿”,北京地坛围墙边是也。北京以外的城市即使并无地坛,也一定会有什么公园之类的“墙根儿”的。小说所写北京人打这“坛墙根儿”寻出的种种乐趣都极寻常:“如若一大清早儿,遛到这坛墙子西北角儿里头来,就更有意思了。春秋儿甭提啦,就这夏景天儿,柏树荫儿,浓得爽人,即使浑身是汗,一到这儿,也立时落下个七八成儿去。冬景天儿呢,又背风儿,又朝阳儿,打拳、站桩,都不一定非戴手套儿不可。……”就这!“坛墙根儿”。你看清楚了,这“去处”的好并不因地儿有什么特别,只因北京遛早的人们从平平常常中咂出了别人咂不出的味儿。
普通北京人的找乐所欲不奢,所费不靡。不但讲“迎时当令”,也讲因陋就简。他们的满足并不必建立在庞大坚实的物质基础上。
《老槐树下的小院儿》说小院的好处:“最好的是:方砖漫地的院心,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在荫凉地喝个茶、下个棋啥的,不论茶叶好坏,也不管输棋赢棋,只要往这儿一坐,就是一个乐儿。”比之坛墙根儿更是平常,哪里只是北京人才有福气享用!
陈建功“谈天说地”之四的《找乐》,从北京人的“找乐子”说起,带有一点综合、总结的味道:“‘找乐子’,是北京的俗话,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即使讲到死吧,他们不说‘死’,喜欢说:‘去听蛐蛐叫去啦’,好像还能找出点儿乐儿来呢。”旧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戳在天桥开‘骂’和听‘骂’,是为一‘乐儿’”。嗜好京戏的北京人,“唱这一‘嗓子’和听这一‘嗓子’,也是一个‘乐子’”。粗人们围在大酒缸缸沿儿上神吹海哨,又是一“乐儿”。在另一篇小说里,陈建功还写到摩托车交易市场上以看和说为乐的,尽管是一种苦涩的“乐子”。“看的是一种活法儿!爷们儿的活法儿!”
“追求精神满足”亦是一种标准。《四世同堂》中的冠家,极会享用生活,在这一点上,是最标准的北京人,但北京人还有德行上的要求。虽有得样的服装和“几句二黄”,“八圈麻将”,也照样会为人不齿。冠晓荷的生活中小零碎极多,装潢得极精致,也看似悠闲,但他的那种“风雅”全是装饰,像衣裤鞋袜,无关乎“精神”,因而也不为正派市民看重。在极其有限(以至于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寻求一种只不过精神上的满足,也许是“匮乏经济”下的特有文化,在这一点上又非为北京人特有。其渊源有自:“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这种生活的艺术,本身就含有悲剧意味。“有限”因于“匮乏”;“乐子”之要找,则由于少余裕;精心营造生活的艺术也因生活的枯瘠。乐天、达观中可以隐隐看出的,是普通中国人生存的艰难和生存的顽强。发达国家的文明人或许会视此为贫穷中的自我解嘲,我们自己却不能不认为这里有作为“匮乏”的补偿的极细腻的审美情趣。“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胡同居民不必这样风雅,但在寻求精神满足以至美感陶醉上,却也与上述境界相去不远。这是传统中国文化培养的审美态度与能力,其间快感,也要中国人才能享用。“饭疏食饮水”,乐自然不在所“饭”,而在虽“饭”此仍能“曲肱而枕”的悠然心境。享用的是自然,也是自己的审美态度。这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的常见境界,与追求感官愉悦讲求实际的西方人欲求不同。这又决非“画饼充饥”式的满足。此种审美活动中有高度发展了的文化,高度发展了的人的精神能力,有人对于生活对于人生的美的创造。
邓友梅写经济拮据的落魄旗人贵族金竹轩:“下班后关上门临两张宋徽宗的瘦金体,应爱国卫生委员会之约,给办公楼的厕所里写几张讲卫生的标语,然后配上工笔花鸟。到星期天,早上到摊上来一碗老豆腐下二两酒,随后到琉璃厂几个碑帖古玩铺连看带聊就是大半天。那时候站在案子前边看碑帖拓本,店员是不赶你走的。”极实际而又精神性的享乐。不耽于空想,将“享乐”落到实处,也是普通市民与迂夫子的一点不同。谁又说这里没有普通人在物质条件制约中的生活设计以至“创造”?
然而也不必讳言,这不是童年期或青春期血气健旺的民族(如古代希腊人)的生存趣味,它属于一个充分成熟(以至于过熟)的文化。它也大不同于现代西方消费文化,没有后者中灌注的强盛的生活欲。它的过分精巧、雅致,它的严格适度,它的绝不奢华等等,都昭示着这种文化的形成条件。这应当说是距古希腊“酒神精神”最远的生活艺术、审美趣味,其中浸透了东方哲学,隐现着我们民族在人类史上最为长久的专制统治下铸就的文化性格。它以“知足”与“适度”为特征。在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之间,往往小心翼翼地把重心放在后面,以后者的满足缓冲了前者的贫乏所引起的痛苦,更以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的积久力量,使有意识的努力化为习惯、心理定势,造成和谐、均衡、宁静自得的内在境界。因而“酒神精神”中包含的那种亵渎(对于既成的伦理秩序、规范),那种破坏(对于常规状态),与这境界无缘。
不耽于空想,将“享乐”落到实处,也是普通市民与迂夫子的一点不同。谁又说这里没有普通人在物质条件制约中的生活设计以至“创造”?
有限物质凭借下的有限满足,以承认现实条件对于人的制约为前提的快感寻求与获得,在这里都更是个体的心灵状态,不像酒神欢娱那样表现为公众的狂热,从而为公众所共享。这是审慎的满足,不干犯道德律和其他戒律,甚至无关乎他人的自我内心的满足。在这种审美活动、审美的人生创造中,中国人也为他们个性的被压抑、个体需求的被漠视,找到了有限的补偿。
限度感(未必都出于物质制约——如上流社会)也系于中国人所理解的“合理性”。不过度,不逾分,不放佚。那种节制的、注重精神的享乐,也可谓之“合理的享乐”是不失理性自觉的快感,且快感的获得主要取决于领略快感的心理能力。北京人讲究吃,却决不饕餮。在饮食文化发达的拉丁民族,吃是为了充分地享受现世幸福人生欢悦,联系于拉丁民族热情外倾的民族性格。有教养的北京人对于精神性的追求,则有效地节制了单纯的享乐倾向,使“物欲”部分地转化为审美追求。在中国人,节制有时即一种美。老舍在《正红旗下》里写福海二哥,强调的即是人物的善能节制(甚至对身体动作的控制)。限制是外在的,这节制则是内在的:道德修养、人生训练,使客观制约主观化、道德化了。“安乐居喝酒的都很有节制,很少有人喝过量的,也喝得很斯文,没有喝了酒胡咧咧的。”(汪曾祺:《安乐居》)自然也就没有狂欢,没有纵欲中的兴会淋漓。他们不在乎酒的等次,酒菜的规格。对于那一点酒与菜,品得很细,一点一滴都咂了进去。老吕“三两酒从十点半一直喝到十二点差一刻”。就这种环境,这种喝法,有味。有味即可,无需他求。作者更是把这小酒店风味细细地咂摸过了,一点一滴都没有放过。令老北京人留恋的小酒馆、小茶馆情调就是这样清淡与悠然。限制与节制,造成内外和谐的境界,伦理规范由是人格化、日常生活化了。因而才更是一种深层文化,有深而坚牢的根柢。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物质条件的有限性一旦被理解为物质需求的有限性,自然就有了小农社会普遍的自足心态。这一社会中处于较高文化层次的人们,则把对“无限”的追求顺理成章地转向人生境界方面。以庄子的达观自足,而渴望作“逍遥游”,是最完美的例子。北京人的精神追求虽不企求哲人式的高远,但那多少也可以看作对现实人生的超越,对生存的具体物质性的超越的吧。
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过对于上述以节制、自足为特征的文化的声势浩大的反叛。在老舍开笔创作之先,《女神》(郭沫若)之属以其醉意淋漓的酒神气息,由文学的方面引入了异质文化的冲击,使当时的激进知识者有解放感。对旧文化的破坏,不免以取消“节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这破坏终于被证明是超出了必要的。“五四”时期的“解放”,就包括了由乡土中国、小生产者社会,由农民式的审慎安分卑微心态的解放,由市民传统的常识经验处世之道的解放,由东方哲学和东方式人生的拘限中的解放。新的地平线也只有在这种破坏与冲决中,借助于诗人们狂放的激情抒发才清晰地呈现。故而20年代周作人那些关于“生活之艺术”的唠叨,不能不是自说自话,尽管说得聪明,且不无道理。正是在这种破坏声中,老舍对北京人的生活艺术用了轻嘲口吻。直到40年代写《四世同堂》,出于故园之思和不同于“五四”、30年代的文化氛围,才放纵情感地写北京的四时果蔬及其他人生享用。
即使“五四”式的狂飙,也不足以颠覆几千年筑就的文化巨构。《女神》问世后,连它的作者也难以为继。中国是这样的中国,诗终究拗不过现实的力量。五四运动是知识者的运动,诗人的狂呼几不能达于普通小民的听闻。仍然是鲁迅,更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力量的限度,功能的边界。当年那些摩罗诗人们决想不到,要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由经济改革开路,出现了文化大规模重构的历史契机;他们自然也未能逆料这重构过程的复杂艰难,其间极难估量的文化得失。即使文化解体也暂时无妨于京味小说作者写小酒馆,这又是为“五四”诗人不能想见的新时期的文化宽容和多种文化价值取向。在纷乱世事中,并没有人惊讶于京味小说作者的选择,惊讶于当代京味小说凭借其文学选择渲染出的文化的宁静。
北京人在找乐中追求的更是个人的内心满足,这里还应当说,既生存于社会,满足个人的,总是一些非个人的条件。聊天固然娱人自娱,票戏更自娱而又娱人。
北京人在找乐中追求的更是个人的内心满足,这里还应当说,既生存于社会,满足个人的,总是一些非个人的条件。聊天固然娱人自娱,票戏更自娱而又娱人。 唱、做是要有听众、观众的。这种场合所能收获的,无非是个人表现欲的满足。但满足表现欲又确实更为自娱;非关政治,非关利欲,乐的首先是自己个儿。因而北京大小公园才至今仍有如《北京人·二进宫》所写那一景,无论唱曲的还是听曲的都一派悠然,最风头的行为偏偏透出散淡神情——也最是北京人的风神。
在现代人眼里更奇的,怕要算旧北京流行的“走票”吧。追求精神满足如若不达于下述极端性,还真不足称特异呢。据夏仁虎的《旧京琐记》,清末北京二黄(即京戏)流行,“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其中很有些故事。“内务府员外文某,学戏不成,去而学前场之撤火彩者。盖即戏中鬼神出场必有人以松香裹纸撤出,火光一瞥者是也。学之数十年,技始成而钜万之家破焉。又有吏部郎玉鼎丞者,世家子,学戏不成,愤而教其二女,遂负盛名,登台而卖艺焉。日御一马车,挟二女往返戏园,顾盼以自豪。”(第105页)用时下的北京话说,他们“晕这个”!旗人贵族还有“子弟班”,“所唱为八角鼓、快书、岔曲、单弦之类”,“后乃走票,不取资,名之曰‘耗财买脸’”(第106页)。——不计功利竟至于此;至此却又极功利,只是所求非钱财而已。
不惜“耗财买脸”的,更是北京人中的旗人,其人生追求的痴处、任情处,是可悲悯又复可爱的。这不是上海的交易所或弄堂所能造成的文化,不是那些讲求实惠的近代商业都会居民所能欣赏、认同的文化。他们要的是更实在的满足,决不如北京人找乐的不切实用。北京人也即以这“不切”,显示着“大气”。用了老舍描写人物的话说,“自然,大雅”。上述耗财买脸之举,认为“畸态”也好,“怪现状”也好,“畸”与“怪”中仍可辨认出北京人的特有神情。
有鉴于此,《安乐居》的结句才那么突兀,透着点惆怅:
安乐居已经没有了。房子翻盖过了。现在那儿是一个什么贸易中心。
这种文化不可避免地在没落中。当代京味小说的依赖于“老人世界”不妨看作征兆。当你把京味小说置于其他写北京的作品构成的大场景中,不难看出那些悠悠然的遛鸟者,小酒馆里自得其乐的酒客,以及小公园里围观如堵中旁若无人自我陶醉的唱曲者,被改革中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日益浮躁的人心、日益强化的物质欲求,被马路边的巨型广告牌、自由市场的商业竞争者给“古董化”了。老舍作为日常状态描写的,只是在这种背景下,才被另一代作家特意抽出。这种郑重,已经提示着材料在意义上的变化:渐成特例,须细心抽取的文化例证。会否有一天,这些北京人也如香港街头的遛鸟者,只令人感到滑稽?当代京味小说描写愈精致,愈苦心经营,作品愈古色古香,愈包含这种“凶险的暗示”。历史演进引出的文化后果,其意义从来不都是正面的。这儿有历史为其“进步”所索取的代价。有鉴于此,《安乐居》的结句才那么突兀,透着点惆怅:
安乐居已经没有了。房子翻盖过了。现在那儿是一个什么贸易中心。
依然那么干净,一个多余的字也没有。你却禁不住久久地想,那些老头儿们和他们的那点“乐子”呢?
“找乐”的不同层级及其沟通,前文中的说法不免混淆,比如把文化后果与成因混淆了,也把不同人赋予“找乐”的不同意义混淆了。我似乎过分着眼于“普通北京人”。即使当代京味小说所写,也有并非“普通”的北京人,和他们的近于无限度无节制的享乐。
不必讳言,古城风雅在相当程度上,系于晚清贵族社会的习尚。北京人的闲逸,他们的享乐意识,他们的虽不奢侈却依然精致的生活艺术,直接或间接地源自清末以来上层社会的奢靡之风,与旗人文化在市井中的漫漶。此类现象,衰世皆然,发生在清末的或非特例。但有清一代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清王朝覆灭前历史阵痛延续的长久,都足以使得享乐之风大炽,流风所被,广泛而又深远。
即使普遍风习,具体行为也因人而异。贵族有贵族的玩法,平民有平民的玩法。
写清代贵族的佚乐和享用的豪华,《红楼梦》的描写已达极致。同时代的笔记稗史,则为这巨著提供了大量注脚:“光、宣间,则一筵之费至二三十金,一戏之费至六七百金。……故同年公会,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数百金,以供一朝挥霍,犹苦不足也。生计日促,日用日奢,京师、上海之生活程度,骎骎乎追踪伦敦、巴黎,而外强中干捉襟现肘之内幕,曾不能稍减其穷奢极欲之肉欲也。且万方一概,相皆成风,虽有贤者,不能自异,噫!”盛衰无常,富贵难再。这里不消说有典型的没落心态。“晚近士大夫习于声色,群以酒食征逐为乐,而京师尤甚。有好事者赋诗以纪之曰:‘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听完听庆乐,惠丰吃罢吃同丰。衔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官府衙门尚且如此,社会风习更可想见。“贵家子弟,驰马试箭,调鹰纵犬,不失尚武之风,至于养鱼、斗蟀、走票、纠赌,风斯下矣。别有坊曲游手,提笼架鸟,抛石掷弹,以为常课。……玩日愒月,并成废弃,风尚之最恶者。”(《旧京琐记》第37页)
贵族社会通常是引领文化风气者。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贵胄之家、豪门子弟耽于佚乐,不免风靡水流,演成普遍习尚。六部灯、厂甸、火神庙、白云观,节庆相续,庙会不断。“大抵四时有会,每月有会。会则摊肆纷陈,士女竞集,谓之好游荡可,谓之升平景象亦可。”(同上)时人有诗曰:“太平父老清闲惯,多在酒楼茶社中。”——或许正是国势日衰,外敌凭陵的时候?
即使普遍风习,具体行为也因人而异。贵族有贵族的玩法,平民有平民的玩法。提红子、黄雀的,与提画眉、点颏儿的不同,喝二两烧刀子就一碟豆腐干的,想必不会是“熬鹰”的正经玩主。《少管家前传》开篇道:“北京城里,有这么句俗语儿: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接下来就说这不过是“二三流宅第的格局作派。要说那些够得上爵品的府门头儿、大宅门口儿么,可就另透着一番气度了”。《烟壶》写主人公未见得出色,其中一节写九爷的挥金如土,那种亦天真亦专制的行为姿态却备极生动。越在没落中越要发挥其豪兴,决不肯稍稍失了贵族气派。
老舍的《正红旗下》写定大爷的豪爽阔绰虽不免于夸张,描摹破落旗人贵族的沉湎于玩乐,却另有复杂的意味。如写大姐家经济早入窘境,大姐公公“一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便忘了时间”。在革命声起,贵族断了生计之前,经济困境是无伤雅兴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大姐夫则“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他的每只鸽子都值那么一二两银子;‘满天飞元宝’是他爱说的一句豪迈的话。他收藏的几件鸽铃都是名家制作,由古玩摊子上搜集来的”。
尽管有诸种层级,找乐仍然是北京人生活中最富平等感的场合。“世界上最能泯灭阶级界线的游戏,大约就是下棋。”(苏叔阳:《圆明园闲话》)找乐大多类此。
又沉痛又怜惜,老舍何尝真的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在封建时代,除民间外,艺术通常是由统治者中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老舍早在《四世同堂》中,就半是谴责半是怜惜地写到禀赋优异的旗人“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旗人好玩,会玩。北京像是特为他们备下的一个巨型游乐场。他们不但穷尽了已有的种种游乐,也穷尽了当时人的有关想象。关于旗人对享乐的投入和创造热情,《红楼梦》的描写几无以复加,而且你得承认那种才秉与享乐倾向在造就《红楼梦》的作者上发挥过的功用。
匮乏经济下被旗人贵族发挥到极致的消费型文化、享乐艺术,其豪华奢靡处,与“匮乏”适成反照,其平易俗常性质,又像是对于匮乏的由审美方面的补偿。至于胡同里更为世俗的生活艺术,则几乎是胡同生活中的仅有光、色,这光色使贫乏庸常较易于忍受。到得贵族为历史所剥夺,仅余了“文化”,那种“艺术”更成为痣疣一样的外在标记。优异禀赋,艺术素养,反而深刻化了悲剧性。至于因一代贵族的沦落而有人的再造,同时使其文化民间化(如《四世同堂》中小文夫妇的终于卖艺),个人悲剧由历史文化的发展取得补偿,从大处看,更难言幸与不幸。“大清国”或许是“玩”掉的,“玩”本身却非即罪恶。何况有对历史承担不同责任的旗人,和其赋予生活艺术的不同意义。或者可以说清末贵族的奢靡有罪于历史,却不无功于文化?
尽管有诸种层级,找乐仍然是北京人生活中最富平等感的场合。“世界上最能泯灭阶级界线的游戏,大约就是下棋。”(苏叔阳:《圆明园闲话》)找乐大多类此。广告牌下聊大天的,小酒馆里对酌的,泡在同一间茶馆里的,近于平等。在专制社会,这更是难得的一点“平等”。由此才有悠然、闲逸,有暂时的松弛舒张。北京人的特有风度,那种散淡暇豫,是要有余闲也要有一点平等感才足以造成的,生活也要这样才更艺术化。
这也自然地沟通着雅俗,使不同层级上依赖不同经济背景的“找乐”,在使生活艺术化的一点上相遇并彼此理解欣赏。在北京人,这不消说与价值相对论无关,而另有背景。上文已提到晚清宫廷艺术的流落民间,旗人贵族的没落所助成的北京市民趣味的雅化——虽然与民初以来艺术平民化的潮流不同源,却也不无微弱的呼应。在中国,俗雅之间,本无中世纪欧洲那样的深沟高垒。俗化、雅化的过程始终在进行。这也属于文化运动的正常秩序。匮乏经济既不足以维持云端上的艺术,以创造文化为己任的文人亦得以时时与民间、俗人互通声息。至于当代作家,却不能说未受启示于新的文化眼光(其中含有对大众文化的新的价值估量)。“传统”在这里,也与新的文化现实、文化经验遇合了。
“世俗化”本是清末贵族文化的基本流向,“以俗为雅”更有禀赋优异的旗人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姿态。普通北京市民,“住在万岁爷的一亩三分地上”,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烟壶》),濡染既久,无师自通,便于以俗雅间的调和作成自身风度。这风度也在“生活的艺术”中呈现得最为集中。领略俗中的雅趣,则更有京味小说作者的修养、识见——你看,有这诸种条件的辏集,酿出“京味”这种风格不是极其自然的?
(本文摘自《北京:城与人》,赵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定价:32.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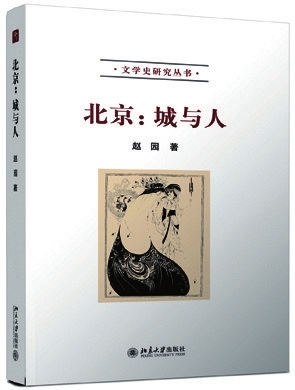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