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西部》像一个老人,他洗去铅华,不想再作任何修饰,不想再用任何技巧,不想再有什么鸡零狗碎,也不想再动什么机心了,他只想静静地跟读者们聊聊天,告诉人们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样的作品要么很无趣,要么很感人,而后者的背后,定然有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的西部》记录的,是雪漠的生命印迹。作品以西部偏僻农村一个文学青年的成长史和人生奋斗为线索,讲述发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到世纪末的西部往事,将西部的土地气息、民间传说、民间文化、人情世态和贫瘠土地上的梦想、追寻及人生感悟融为一体,呈现了一个博大、刚毅、丰厚、神秘的西部,一个梦想始终照耀着荒原的西部,一个精神的西部。那些和他一样希望通过灵魂寻觅和人格完善来改造命运的人们,或许可以从中触摸到一份温暖和希望。
雪漠将此书比喻为“堂吉诃德舞动长矛冲向风车的记录”。他说,堂吉诃德是他的一种宿命,而他甘愿做堂吉诃德,也不做那种非常精明的庸人。此前,他的《野狐岭》以独特的叙事手法,讲述了一个发生于百年前的中国西部骆驼客的革命历险故事,把丝绸之路上现已消失的骆驼客生活、骆驼客文化和近代中国西部骆驼客的“革命之旅”写得云波诡谲、惊心动魄,被称为是中国西部文学在当代文坛格局中寻找自觉、自信的重要收获。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陈彦瑾认为,《野狐岭》是一种境界的呈现,也是作家的智慧达到某种境界后的整体性流露,它不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不考虑文字是否朴素,不考虑对世界有没有启发,所以,它能任由精神肆意地飞翔;而《一个人的西部》考虑了这一切,所以它是入世的,是生命在不同阶段所进行的不同展示,其中不断出现不同的人和事物,是自然出现的。它也是对过去世界的展示,是把自己当成标本所做的一种剖析。
读书报:十五年之内您出版了二十多本书,而且大多是三四十万字的大部头,能谈谈这种写作状态吗?写作何以像喷泉那样不可遏制?
雪漠:这跟我的创作习惯有关。正式写作之前,我总会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是采访,也可以说是体验生活。每年,我都会留出大量时间来体验生活。比如,前年我在藏区住了半年,几乎与世隔绝,将生命融入当地的生活;去年,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了从岭南到西部的文化考察;今年,我去了美国和加拿大,每天都走在第一线……这样的考察,让我总能搜集到大量资料,其中有些资料甚至是罕为人知的;而且,我总会深深地扎进我考察的土地,直到能感受到那块土地的脉搏、感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心灵。所以,我很少觉得那里很贫瘠,无论在哪里,我都能发现它的独特,发现一个巨大的文化世界,总能得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这是我的第一个独特之处。
我的第二个独特之处是,每次采访完,我都会拒绝所有应酬,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空间里,直到把自己采集到的“葡萄”酿成“美酒”。我的意思是,与世隔绝给了我沉淀的空间,每当我静到极致的时候,智慧的闸门就会打开,作品就会像你说的那样,像泉水般喷涌而出。
第三,就是很多作家只是在生活中创作,我却是在创作中生活,就是说,我把所有生命都用来写作了,几乎拒绝了一切的应酬和生活,我和家人也是分开住的,我一个人住在某个小区里,就像闭关那样,与世隔绝地读书、写作、禅修。这种方式已经变成我的生命常态了,所以我的作品特别多。
读书报:从文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的西部》是一个西部本土作家的成长史,写了一个文学青年的三十年,还写了他的两百多位父老乡亲。这样一部作品,能有那么多读者呼应,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雪漠:据说作家的写作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文学性的写作;第二种是思想性的写作;第三种是灵魂性的写作;第四种是生命性的写作。《一个人的西部》正是第四种,生命写作。所谓的生命写作,就是写作超越了写作本身,让生命自己展示它想要展示的过程。在《一个人的西部》中,就是追求写作梦想的过程。这种写作是生命与写作的完美结合,它远离了很多文学性、概念性的干扰,也不靠语言或某个章节来打动读者。真正令读者感动的,是作品中饱含的生命力量,其中涵盖了生命的实践、生命的气息、生命的追求,和生命中所有的悲欢离合。这些因素构成一个整体之后,就会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读书报:《野狐岭》和《一个人的西部》呈现的是西部文化的两个横截面。《野狐岭》是沙尘暴式的,神秘莫测;而《一个人的西部》呈现的西部则非常特别,里面写的全是乡村伦理,完全是借中原式儒家思维来切入,非常平实。
雪漠:《野狐岭》有点像诸葛亮借东风,披头散发,拿着长剑,踏罡步斗,招来无数幽灵,让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一个人的西部》则像一个老人,他洗去铅华,不想再作任何修饰,不想再用任何技巧,不想再有什么鸡零狗碎,也不想再动什么机心了,他只想静静地跟读者们聊聊天,告诉人们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样的作品要么很无趣,要么很感人,而后者的背后,定然有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它让朴实的作品有了力量,就像强大的灵魂让平凡人变得优秀一样。人拥有整个世界的原因,永远都在于他有强大的精神,而不是因为他有强大的物质。因为,物质带来的一切都会很快消失,而精神却能感染、能传递,因而有可能永恒。
读书报:作为西部本土作家,您一直有一种本土化写作的倾向,您认为地域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雪漠:西部文化是我的生命基因,就像遗传基因一样,深深地扎根在我的血液里。其他文化更像是变异,就是说,它们进入我的生命,跟我本有的东西进行杂交,我的体内就有了新的营养。西部文化也像我的根,而其他文化则像树枝、树叶、阳光和空气。这个根太重要了,它让我能吸收各种营养,将各种文化化为己用,但我并不局限于本土化写作,也不是不会写其他文化的作品,我之所以一直写西部文化,是因为它虽然优秀,却很弱小,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影响力,知道它的人很少。所以,这个阶段西部文化需要我这样写作。
读书报:西部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被忽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几乎没有西部文学的板块。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雪漠:这很正常。因为西部文学没有话语权。这也正好印证了我上面所说的:不是我需要西部文学,而是西部文学需要我。若干年后,当雪漠作品的读者充斥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雪漠文学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时,人们自然会关注西部文学。现在人们看得到它,或是看不到它,都不重要,重要的,还是我们西部作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哪怕目前还不够大,或是被搅天的信息遮蔽了,也不要紧,因为,我相信,只要西部作家们共同努力,这种现象就一定会改变。西部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们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提供了不一样的风景,而我,愿意为这幅美丽的画卷再添上一朵鲜花。
读书报:您对自己的创作满意吗?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雪漠:我对生命中所有的状态都非常满意,因为我总是在做最好的自己。每个人在舞台上演绎的所有行为,决定了他此生的价值。剧情越复杂、越曲折,角色就越有价值。接下来,我的创作将回到西部大地,写写甘南草原,写写西藏。因为,那是我最了解的土地之一,我对它的研究已有十几年了,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写出一部关于那块土地的作品。我对它的重视,相当于三大战役中最重要的那场战役,我会把它当成后半生最重要的作品来写。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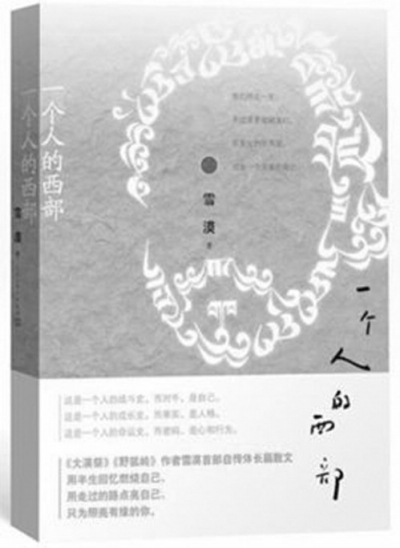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