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古文学巨匠庾信(513~581)的创作中,辞赋占据重要地位,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长篇的《哀江南赋》,较短的篇章则以《小园》《枯树》二赋特别是后者最为读者爱重。唐人张说《过庾信宅》诗云:“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包胥非救楚,随会反留秦。独有东阳守,来嗟古树春。”尾联二句正是指《枯树赋》,盖该赋开头便道——
殷仲文者,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此乃全赋之凤头,一下子就奠定了全文的基调,吸引住读者的注意。但前人也有批评《枯树赋》者,认为用典过多,文意晦涩,不能算是很高明,例如祝尧《古赋辩体》卷六指出:“庾赋多为当时所赏,今观此赋,固有可采处,然喜成段对用故事以为奇赡,殊不知乃为事所用,其间意脉多不贯串。”用典太多,脉络不那么分明,意思不容易理解体会,确为此赋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对此赋的探索研究一向并不甚繁荣;还是《哀江南赋》等篇更为引人注目。
可是到了四十年前的“文革”末期,《枯树赋》忽然成为一大热点,其流风余韵直到近来的报刊上还时有所见。
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非常关注庾信这篇《枯树赋》,让身边的人读给他听,他自己不仅反复背诵,还致力于研究此赋应如何解读。在比较早一点的时候,复旦大学的一些老师已经遵命为《枯树赋》作出注释,印成大字本呈上去,但毛泽东很不赞成。据知情人介绍说:
我们在注《枯树赋》时,基本上是参考清代倪璠注的《庾子山集》和近人臧励龢的《汉魏六朝文》、谭正璧的《庾信诗赋选》的注解和旧说。这几种注本都说,枯树之所以枯萎凋零,是因为树木在移植过程中伤了根本所致。他们因此都认为,庾信正是借此比喻自己身仕数朝,飘零异地,寄感慨于枯树而为之赋。这种解释即传统的“移植说”。它的影响很大,从未有人提过异见。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刘修明《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前言》,转引自骆玉明《〈枯树赋〉的解读及其他》,《悦读》第12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毛泽东在1975年5月29日对此注讲了四条意见;于是江青另行安排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梁效”)重新注释。新注得到某种肯定,有批示说:“此注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芦荻。关于注释的问题,请你们过细的研究。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八月。”
当时一度在毛泽东那里充当侍读学士的芦荻女士晚年曾谈起《枯树赋》问题,她说后来她自己很想重新作注,可惜始终没有动手。据准备去担任她助手的孟繁之最近撰文介绍说:
长期以来,她一直有想法,想为《枯树赋》重新作注,将主席当年的一些谈话及她近四十年来的一些体悟都收进去。此话她后来多次和我说起。2012至2013年,为纪念周一良先生百年诞辰,张世林先生和一良先生的哲嗣周启锐先生主编有一册《想念周一良》,里面有一篇宋柏年先生的文章,谈及当年毛泽东否决上海注本后,“梁效”曾为《枯树赋》重新做注,由某位先生先注,复经小组讨论,最后呈递上去。周一良先生遗物里,过去也曾见过一册油印的《枯树赋》注释讨论稿,上面有一良先生用铅笔所做繁复批点。有一次,吴小如先生读到宋先生文章后,和我说(此事他也同别的一些先生谈过):事过经年,一切皆应当还原历史真实,“某位先生”即是指他,说宋先生文章里本该注明的。——为此我也专门问过芦老师,芦老师告诉我,事情确实如此,她见过“梁效”的注本,但她不知预先作注者是吴小如先生。(《芦荻谈往》,《东方早报》2015年5月3日《上海书评》)
今按两校写作组之《枯树赋》注释本的执笔人确实是吴小如,他本人曾经说起过;吴先生去世后,柏寒在纪念文章中回忆说:
1975年,我有幸和吴先生一起参与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的注释工作,主要是诗词赋作品。其间,我和吴先生有过一次谈话,给我的教益匪浅。吴先生说,搞注释工作,最忌望文生义。一定要对作者的身世、原作的背景有较为深入全面的了解,对文中的典故出处本意都搞清楚。虽说是“诗无达诂”,虽说是“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但基本的意思不可以远离文本的原意。吴先生还举例说,李清照的《声声慢》:“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有人解释为我怎么生得这么黑,显然与作者的本意相去甚远。《枯树赋》中大量引用关于树的典故,都是在说它受到的种种急流逆波冲荡和人为的摧残伤害。而“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则是全赋的纽带,由树及人,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作者的心境,也可以说这是全篇的纲。
毛泽东晚年酷爱此赋,尤其激赏“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等名句,虽是垂暮之年的感叹,但枯树所受的摧残,“百围冰碎,千寻瓦裂”,实际上象征着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遭受的种种苦难,反复吟诵寄托着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忧虑,同时也蕴涵着他对生活的热爱。(《桃李满园人已去,终将情采壮山河——深切怀念吴小如先生》,《书品》2014年第3辑)
这应当正是“梁效”奉命注释《枯树赋》之时的事情。又葛晓音在一篇关于林庚先生的文章里提到“林先生对庾信《枯树赋》的解释,曾受到过毛泽东同志的称赞”。(《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化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196页)林先生当年也在两校写作组内,与《枯树赋》新注的关系一定也非常之大。
一般地来说,庾信特别关心枯树自有他的经历和悲哀在发挥作用,他本人由南而北,是“移植”过的;毛泽东在健康状况很不好的垂暮之年关心《枯树赋》也自有他独特的感慨和心态,“移植”与否,非所思存,而当下的嗟老之叹与古人之身世之悲亦未尝不可以相通。这些都有待进一步仔细研究。柏寒先生应当是很了解情况的,而在这里似未及畅所欲言。
现在从原作看去,“移植说”并非毫无根据。赋中明明说起“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又说到“拔本垂泪,伤根沥血”——不过该树之所以“生意尽矣”,却又不仅仅是因为遭到移植,它还受到了种种摧残,这才弄得惨不忍睹。原因既然比较复杂,只谈其中某一点那就有片面性了;至于更强调哪一方面,则各有见仁见智之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毛泽东当时更注意那些外来摧残大树的因素。
可是问题还在于,庾信此赋的重点似不在说树为什么会枯,而在枯了以后怎么安排才恰当。大树已枯或将枯是前提,值得关心的是何以善其后。
上世纪70年代中叶并非研究古代文学的正常时代;毛泽东如此关心《枯树赋》,也同一般学者对中古文学作纯学术的研究大异其趣。所以我们今天重新来讨论研究《枯树赋》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另出手眼,历史到底又走过了四十年。但那一段学术史仍然是重要的,而且既然曾经存在,并且牵动甚广,更不能视而不见或予以搁置,学术研究的规范是必须对有关学术史作出必要的追溯和反思。
二
《枯树赋》从东阳太守殷仲文这里写起,这是辞赋中常用的一种办法,著名的先例如南朝宋谢庄的《月赋》,就托之于王粲与曹植。
东晋文学家殷仲文(?~407)是大军阀桓温的女婿,当桓温幼子桓玄攻入首都准备取代东晋、自立为帝的时候,他迅速抛弃原先的官职新安太守跑到首都来为桓玄效力,新的楚王朝建立后他当上了侍中,大肆纳贿;不久刘裕起兵打败桓玄,楚政权迅即结束,这时殷仲文又来投靠刘裕,并幻想在这里仍然官居高位,把持朝政;精明的刘裕先稳住他几天,然后很快就把他打发到东阳去当太守,稍后更以谋反罪将他杀掉,其时他还不到四十岁。
《世说新语·黜免》第八则载:
桓玄败后,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意似二三,非复往日。大司马府听(厅)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在朔与众在听(厅),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
殷仲文失去了桓玄当政之时的地位,精神有点恍惚,看大司马府厅前的那棵老槐树,觉得它枝叶偃息倾侧,已经没有生气了——这无非出于一种移情作用,表明在他看来前大司马桓温和他的接班人桓玄已经完蛋了;而庾信却借来抒发自己关于大树将枯的感慨。殷仲文对此槐树叹气时尚未去东阳当太守,庾信大约有点记错了,或故意加以改造。他是在写赋,本无须讲究十分精确。
《枯树赋》里用了许多关于树的典故,令人应接不暇;末了的几句正与开头遥相呼应:
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桓大司马就是桓温,故事的原本也在《世说新语》,见于《言语》之第五十三则: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
赋中也对原始材料有所改造。对于文学家的措辞不宜取考据家的拘执态度,《枯树赋》里的大量典故,只要心知其意即可。
在《枯树赋》的这一头一尾中间,有三个小段,分别写枯树的三种前途,庾信本人看好的是其中的第一种。认清这一点乃是清理《枯树赋》脉络的关键。
这里需要注意此赋的写作时间。按唐朝人张鷟《朝野佥载》卷六载:“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北方文人瞧不起业已失去依靠的南方使节庾信,而庾信对北方文人更不大佩服,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也为了表明自己现在的态度,他拿出了新近所作的《枯树赋》以示之。似此则《枯树赋》当作于作为萧梁王朝使者的庾信陷于西魏不能南归之初,即梁承圣三年(亦即西魏恭帝元年,554)的秋冬——本年四月,庾信以梁散骑常侍的身份聘于西魏;九月,西魏攻陷江陵,庾信失去归路。
故国覆亡后庾信处境很困难,他的使者身份已经自行消亡,在北方十分尴尬,真所谓“妾身未分明”。但是他还得面对现实,重新安排自己的前程。所以这篇赋表面看是咏物,而实为写志,甚至带有某种表态的意思。至于欲借此显露才华,压住北人一头,则尤为重要的当务之急。
庾信自己觉得,在当时北方的政局中他一时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坐标。先前由南朝叛逃去北方的官僚和文人也很有些人,一般都受到礼遇,甚至也有得到重用的,但庾信的情况不同,他是作为使节而来的,从道义上说他不能叛逃,而且故国已亡,也无所谓叛逃了。从实际情形看去,他得另想办法,用一个合适的理由在这里呆下去。
由于他使节的身份,也由于他早已建立起来的文坛声誉,此时他并非普通的阶下囚,而是得到某种规格待遇(实为软禁)的上层人士——这就是后来他在《哀江南赋》中所说的“囚于别馆”——这显然不合于他的心思和需要。外面好看,内里甚苦,年纪渐老,壮志成空,进退皆难,走投无路。所以庾信在《枯树赋》之末写道:
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叹变衰。
萧梁中兴道消,自己无从感会风云,奋其智勇,失去使节的身份,却仍然忧惧谗言(《诗经·王风》有《采葛》篇,郑《笺》云:“桓王之时,政事不明,臣无大小使出者,则为谗言所毁,故惧之。”),只能在长安“食薇”,这样一种特殊的处境促使文学家庾信在枯树上找到了寄托感慨的客观对应物,即以此作为发泄感情的突破口。
这新枯之树曾经很是兴旺,但现在其根已死,至少也是半死,生意尽矣。复活是不可能的,看来它唯一的前途是作为木料进入一个新的生存状态。他期待着这上好的木料在加工的过程中获得华丽的转身:
匠石惊视,公输眩目。雕镌始就,剞劂仍加。平鳞铲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
这大约应当理解为他本人对于未来的希冀。庾信是一个较之坚守教条更很讲究实际的人,他固然不胜感慨地哀叹现在,同时也已经着手规划自己的未来。当下的“匠石”和“公输”亦即识货的高人在哪里?庾信入北之初专门将《枯树赋》公之于众,言外似乎表明他相信自己未必没有翻身之日。当然,这一层意思他并没有也不便过分强调,通篇仍以哀叹为主,他有他的身份,他的尊严,而长期以来形成的“流连哀思”(萧绎语,见《金楼子·立言篇》)的审美趣味也在发挥作用。
庾信清醒地看到,这枯树也就是他自己也很可能并没有什么好的前途,相反将遭到轻重不等的摧残:轻一点的将是“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重一点则是“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欹卧,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戴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睒睗,山精妖孽”。总之,在此水土不服,前途未可乐观,只能抒写不幸,拭目以待未来。
换言之,现在存在好和坏两类前途,坏前途中又可分为轻重两种情形。未来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多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庾信正与这新枯之树异质而同构。大树已枯,旧我已死,未来将走向何方?《枯树赋》的原旨大体在此。至于后来的读者怎样理解,那是另一问题,完全可以就其中某一点痛加发挥,这里海阔天空,略无挂碍。
庾信后来在一首诗中写道:“倏忽朝市变,茫茫人事非。避谗犹采葛,忘情遂食薇。怀愁正摇落,中心怆有违。独怜生意尽,空惊槐树衰”(《拟咏怀》其二十一)。“中心怆有违”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内心矛盾,精神痛苦。这首诗与《枯树赋》正好互为注释。
稍后庾信入仕于西魏,拜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第二年,又升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尽管这些头衔并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但他总算有了某种着落。西魏和此后的北周都非常看重庾信。庾信的乡关之思虽然至死不能泯灭,但留北之初迫切希望有“匠石”“公输”一类贵人来关注自己的意思,则因为问题已经顺利解决而自然消亡了。于是《枯树赋》在他已是过时的绝唱,而同时也就成了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名篇。
附录 庾信《枯树赋》原文
殷仲文者,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声含嶰谷,曲抱《云门》。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乃有拳曲拥肿,盘坳反复,熊虎顾盻,鱼龙起伏。节竖山连,文横水蹙,匠石惊视,公输眩目。雕镌始就,剞劂仍加。平鳞铲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
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迁,森梢百顷,槎卉千年。秦则大夫受职,汉则将军坐焉。莫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东海有白木之庙,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陆以杨叶为关,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岂独城临细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
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木魅睒睗,山精妖孽。横洞口而欹卧,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戴瘿衔瘤,藏穿抱穴。
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乃为歌曰:“建章二月火,黄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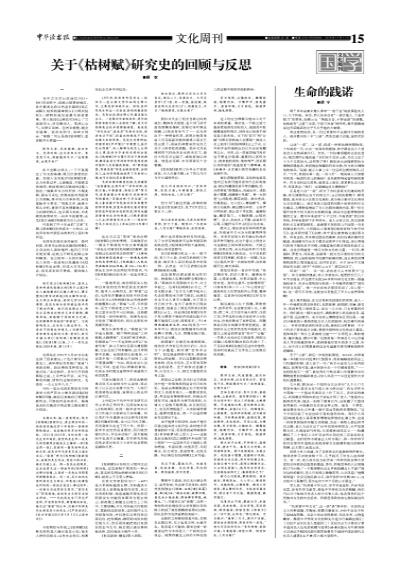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