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怎样看待革命文学,它都是民国文学的一道景观。在以往许多文学史撰述中,它几乎成了唯一的景观。孙郁的讲述试图改变这种荒谬的现象,他在这里提供了民国文学更为多姿多彩的风貌,其中很重要的一脉,便是从文学革命中溢出的另一种眼界和追求。
民国似乎是近些年来的一种新“发现”。有很长一个时期,这个历史性存在几乎被我们“遗忘”。这样的“遗忘”,是一叶障目。至于这一“叶”,大约就是所谓革命与进步。以“革命”和“进步”的名义将民国“裁为三截”,于是有了近代、现代和当代。
很显然,以“五四”为界分割民国文学史,不仅不足以解释文学发展、演变中的诸多问题,反而制造了许多认识上的混乱和误区。孙郁在民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开掘,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道人为的屏障是必须要打破的,文脉也在他的叙事中被重新接续起来。他在谈论新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时,首先从更开阔的视角,描绘了清末民初的文学生态。他特别注意到在西学东渐大背景下文化新因素的产生,以及新学与固有文化的对抗和冲突。有几个人物是绕不过去的,譬如黄遵宪、梁启超、章太炎、严复、林纾、陈季同,包括周氏兄弟,他们的存在,昭示着民初四年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如果说民国文学的主潮是求新、求变的话,那么,它的滥觞就应该发生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个时期,古老的中华文明遭遇了来自西方的严峻挑战,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但它也孕育了改造固有文化而自新的内在冲动,所以,梁启超才大声疾呼“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戏曲革命包含其中)”,他把文化变革看作是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
胡适、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学“革命”,既以梁启超的“革命”为滥觞,他们之间的相关性就不能因为梁启超后来的被“落伍”而予以拒绝。事实上,文学在他们那里都是政治的工具,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当胡适谈论白话文和新诗的时候,他在谈论什么?然而我想,无论他谈论什么,都离文学甚远。虽然他们都视韩愈为异类,但就“文以载道”而言,他们却又有同好,即都以“道”来规范有关“文学”的思考和叙述,尽管“道”已不同,然而,其中的逻辑和思维范式却是一样的,那就是,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思考思想文化革命,又从思想文化革命的角度思考文学艺术革命。抓住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十年后苏俄的“革命文学”如何置换了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并进而理解革命文学何以最终演变成为阶级的、党派的文学。
无论我们怎样看待革命文学,它都是民国文学的一道景观。在以往许多文学史撰述中,它几乎成了唯一的景观。孙郁的讲述试图改变这种荒谬的现象,他在这里提供了民国文学更为多姿多彩的风貌,其中很重要的一脉,便是从文学革命中溢出的另一种眼界和追求。他们不认为文学只有外在目的却没有自身目的,用王国维的话说,具有纯粹美术之目的的文学,是“可爱玩而不可利害者”。沿着这个思路,于是我们看到,有人已经绕过胡适(这时的陈独秀,已从文化领袖演变成为政治领袖),试图从诗的角度思考和创作了,他们强调诗的思维,诗的逻辑,诗的旋律,认为“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才是诗。新诗的园地于是收获了郭沫若的《女神》,汪静之的《蕙的风》,戴望舒的《望舒草》,朱湘的《夏天》,冯至的《十四行诗》,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的《烙印》,穆旦的《穆旦诗选》;新月派更是人才济济,有徐志摩、闻一多、饶梦侃、朱湘等。诗以外,还有老舍、沈从文、萧红、张爱玲,以及左翼作家的小说和曹禺的戏剧,乃至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钱锺书、谢无量的学人笔记。
对民国文学的全面观察和完整叙述,至少需要两种眼界,革命的眼界必不可少,审美的眼界也不可或缺。然而,孙郁笔下民国文学的包容性又不仅表现为对审美眼界的接纳,还有在叙事中对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二元格局的关照与肯定。他对清末民初旧小说及旧诗词的梳理,从旧文本中发掘新的因素,尤为注意写作者的心绪,以及世道人心给予作品的影响,并不因为用了旧小说的形式便否定其文学的审美价值。他从吴趼人的《恨海》中就看到,“作者是忧世很深的人”,称赞他“对现实的忧虑和对生民的爱怜,是颇为感人的”,虽然不可避免地带着旧文人气,但“作为过渡时代的作家,其价值不可小视”。他在谈到鸳鸯蝴蝶派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并不仅仅从读者是否买账的角度立论,还从作品中发现了“作者良知的闪烁”,以及那个时代的氛围和各个阶层的精神面貌。当然,也指出他们的弊病,“是在日常性里陷得太深,不能跳将出来,殊乏创意”;又“因为太市民化,精神多士大夫气,与西洋小说比,精神的含量不高”。
诚然,孙郁观照民国文学的眼界,还是知识精英的眼界,并非民国大众的眼界。也就是说,在革命的眼界与审美的眼界之外,应该还有精英的眼界和世俗的眼界存在着。旧诗词一讲不必论,梨园一讲,尤为明显。其中讲到齐如山、翁偶虹,看他们的眼光还是知识精英的意味多一些。对齐如山,只说他的作品,有“文人品质现代性的表达”,有“士大夫明快的一面与市井里的纯然之风,与新文学里的人文精神相遇了”;对翁偶虹,除了注意到他的创作“与京派文人的趣味相符,或者说乃旧都市文人遗风的再现”之外,虽然也对其中“现实情怀与人生体验的真挚表达”表示赞赏,但其作品中充沛的市民俗趣味,以及民国大众的审美观照,究竟该如何处置,却很少深究。在“草根与政治”一讲中,孙郁看到了所谓大众化其实就是化大众,也看到了走向民间与深入“工农兵”的共谋关系,但他只把思绪停留在这里,未能继续追问下去:“日常性”与“市民化”作为“革命”的必然结果,又该如何被处置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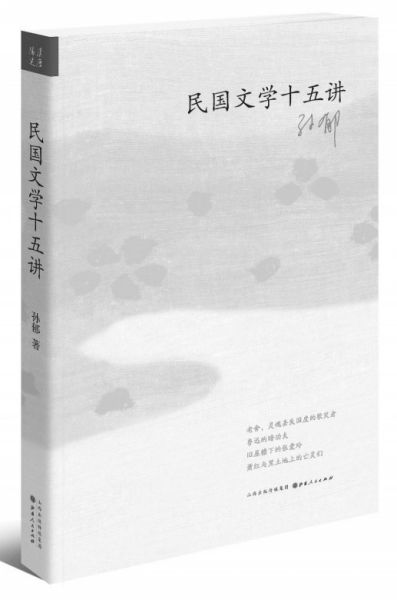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