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谁人不识君”,邓云乡先生便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士君子、文化人。邓云乡学名邓云骧,生于1924年,故于1999年。邓公出名较早,但出大名较晚,他原有红学家之名,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但邓公在全国出名,还是在他出版了《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之后。记得1982年此书刚出时,一位北京学者对我说,“从哪儿冒出个邓云乡,写北京写得这么好!”这本书是邓公出大名的开始。我就是因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了邓云乡的大名。之后,邓公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文章更是常见于各报刊,产量之高,真如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所评,“文章如泉源,不掘地而自出”。
粗略统计一下邓云乡的著作,计有《鲁迅与北京风土》《燕京乡土记》《文化古城旧事》《水流云在丛稿》《水流云在琐语》《红楼风俗谭》《红楼梦忆》《红楼识小录》《红楼梦导读》《清代八股文》《云乡漫录》《云乡琐记》《云乡话书》《云乡话食》《宣南秉烛谭》《诗词自话》《书情旧梦》《北京四合院》《花鸟虫鱼》《吾家祖屋》等近二十种。河北教育出版社为邓云乡出版了《邓云乡集》,最近中华书局增补重编后推出了新版。
人们读邓公的书,都知道他有学问,至有“满腹学问,撑肠万卷”之评,但要说邓公算是哪一种学者,则说法不一。或说是民俗学家,或说红学家,或说文史学家,或说北京史专家。是的,他确是这些方面的专门家,但还没有说够。邓公还是掌故家、社会史家、散文家、诗词家、书法家和美食家。读了他的书便会知道,这些冠冕绝非浪得,而都是实至名归的。这么多的“家”,我看可以用一个“家”来概括——“杂学家”。周汝昌先生曾称邓公的学问为“历史杂学”。“杂”者,非芜杂,博学之谓也,“杂学”乃博杂之学问,“家”是专家。“杂学家”者,学问广博且专深之通人也。邓云乡正是一位在多个学术领域造诣精深的学问通人。
一、“晋籍上海人”的北京乡愁
邓云乡原籍山西省灵丘县,青少年时期在北京上学,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过一段,从1956年起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概括来说,邓公可说是一位“晋籍上海人”,因他居京多年,也可说是一位准北京人。
邓公是记录和研究北京史地的大家。他的《鲁迅与北京风土》《燕京乡土记》《文化古城旧事》《宣南秉烛谭》《北京四合院》,都是可以传世的力作。他对旧京历史掌故的熟悉和精研程度,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史上著名的北京史地专家张次溪、金受申等先生。特别让人感慨的是,他一个“晋籍上海人”,对北京的乡恋乡愁,远过于许多“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土著。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应知故乡事”,但许多极有滋味的乡土物事,我却知之甚肤浅,只是在读了邓公文章后,才恍然知其妙处。
邓公写北京,从宫廷写到市井,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写得精细入微。比如写北京四合院,他写道:
四合院之好,在于它有房子、有院子、有大门、有房门。关上大门,自成一统;走出房门,顶天立地;四顾环绕,中间舒展;廊栏曲折,有露有藏。如果条件好,几个四合院连在一起,那除去“合”之外,又多了一个“深”字。“庭院深深深几许”,“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书情旧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我自幼在北京四合院里居住,从未琢磨过这种住宅有什么好处,更不懂相关的建筑知识,只是浑然瞎住而已。看了邓公对四合院的讲说,才懂了一点四合院的妙处。
邓公讲说四合院的最精微之处,我认为是对四合院四时风韵的概括和鉴赏。他说,四合院是“冬情素淡而和暖,春梦浑沌而明丽,夏景爽洁而幽远,秋心绚烂而雅韵”。(《书情旧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这是多么精彩的描摹,不仅富有诗意,而且带有哲理味儿。在邓公眼里,四合院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居处,更是一种高雅精致的文化事象。比照邓公所讲,这四合院里的冬情、春梦、夏景、秋心,我都是经历过的呀,今日回想,我真辜负了那美好的院落。
邓云乡是学者,他写北京掌故,绝不像坊巷故老那样,只是平摆浮搁地说旧事,而总是要寻出其源流和文化底蕴,使读者建立起史的概念,获得文化上的理解。比如,写北京的名吃豆汁,他从京戏《金玉奴》别名《豆汁记》,讲到古代文人墨客咏豆汁的诗,又讲到古巷中卖豆汁的吆喝声和唱豆汁的儿歌,既讲历史又说文化,使普普通通的豆汁与文化搭上界,使豆汁的掌故成为一种文化史料。
北京人的三冬“围炉”,在常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讲述的价值,邓公却重视这一中国北方古老的生活方式,他钩索文献,从方域特征、经济生活、南人北迁等多个方面谈“围炉”,通过记述缪荃孙、李慈铭、鲁迅等文化名人的围炉轶话,勾画出了旧京居民冬日围炉的生活场景。
二、寻出《红楼梦》后面的真史
在邓云乡的杂学中,红学研究成绩相当突出,“红学家”名号在他的各种冠冕中也显得尤为鲜亮。但邓公之红学不是“大路红学”,他不研究曹雪芹的笔法和大观园的阶级斗争之类。他的特点和特长,主要是善于寻出《红楼梦》背后的真史,以帮助读者从史的视角真正读懂《红楼梦》。我想这应是邓公谈红的主要目的。
关于《红楼梦》,他的主要著作是《红楼风俗谭》《红楼识小录》《红楼梦导读》和《红楼梦忆》。说是“风俗谭”“识小录”,其实绝不只谈风俗,也绝不限于“识小”,而是涉及多方面的历史,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既有微观历史,也有历史大背景。
邓公为寻出《红楼梦》后面的真史,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
一,给《红楼梦》做史注,揭示文学描写背后的真史或史的元素。这需要史家的功夫,邓公深具这种功夫。《红楼梦》多处写到太监,如第十三回有“早有大明宫掌宫内监戴权”之句。邓公认为这是“半今半古”的写法。“大明宫”是唐代长安宫名,曹雪芹时代无此名,因为清廷绝不可能用“大明”作为本朝宫殿的名字。这是半古。清代有乾清宫、坤宁宫等,都是由太监管理的。这是半今。邓公又解说了明清两代的太监制度和区别,并指明《红楼梦》时代的太监官品是以雍正元年为标准的。这样,读者便明了了红楼文字背后的真史,也就自然把文学故事与历史事实区分开了。
二,“以史解红”,即用史实材料来解读《红楼梦》中的一些内容。贾宝玉的才学究竟如何?《红楼梦》写他在蘅芜院辨认花草时引了《离骚》《文选》《吴都赋》《蜀都赋》等诗文,使众人大为吃惊。就是说宝玉的才学十分了得。但邓公列举了《林则徐日记》和《邵二云先生年谱》中的史料,证明宝玉比起当时同龄的读书种子来,还是有相当差距的。《红楼梦》写宝玉作诗时,竟忘了并不生僻的“绿蜡”一词,遭到宝钗的嗤笑,便说明宝玉的学问还不到家。
三,发现《红楼梦》事物的原型。“红楼梦原型”诸问题,是红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如推测大观园的原型是北京恭王府之类。邓公最先推断“太虚幻境”也有原型,即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红学家周汝昌在与邓公的一次闲谈时听到这一推断后为之一震,认为这一见解真是“石破天惊的奇言”。的确,若将东岳庙的牌坊、诸司、寝宫、侍女等设置与“太虚幻境”比照,确可以让人感到东岳庙极可能就是曹雪芹构思“太虚幻境”的灵感之源。
邓公既懂红又懂史,在懂史这点上,他高于许多纯文学出身的红学家。他那些以史解红的著作,实际可以作为红学工具书来读。正因为他在红、史两方面都有渊博的学问,所以他成了电视剧《红楼梦》当之无愧的顾问。
三、掌故家兼社会史家
掌故是很有用的东西,研究历史可作史料,文学创作可作素材,哲学、社会学可做案例……当个掌故家不容易,必须阅历广,博闻强记,掌故家可以说是历史学家的偏师。好的掌故家须有史家素质,既要言之有物,更要言之有据。将掌故系统化,进行学理的研究,掌故家便成了社会史家。邓云乡便是一位极好的掌故家兼社会史家。郑逸梅是掌故大王,徐凌霄徐一士兄弟被誉为掌故巨擘,我看邓公绝不亚于他们,在不少方面还驾而上之,特别是邓公已进到了社会史家的层次,更为郑、徐所不及。
鲁迅曾写名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其中提到章太炎的反袁气节,因是杂文,不可能写细节,这就需要掌故家来补说。邓公有《太炎先生五题》一文,细写了章太炎反袁气节的掌故。他写道:
袁世凯派他的二皇子袁克文,亲自带了锦缎被褥,送到龙泉寺。太炎先生在房中听到外面有人声,而且在窗户缝中窥视,便撩起帘子一看,原来是袁抱存(克文字)送被褥。太炎先生想出妙法,跑到屋里,点燃一支香烟,把被褥一个、一个地烧了许多洞,扔在院中对袁克文说:拿走。这位“太子”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去了。
这些掌故细节,在一般史书中是见不到的,邓公把它写出来了。这样,一个特立独行,有凛然气节的章太炎先生,就站立在了我们面前。这段掌故实际是史料,可作为史学研究参考,若写章太炎传,或拍电影,更是不可多得的细节材料。
蔡锷得到名妓小凤仙之助,从京师返回云南,发动了反袁护国起义。这一段既严肃又风流的史事,被拍成电影《知音》,广为人知。蔡锷是怎样逃离京城的?史书的记述皆大而化之,电影里也只是一两个镜头。邓公《蔡松坡之死》一文详述了这段历史掌故。其中写道,在八大胡同头等小班云吉班妓女小凤仙的帮助下,在梁启超所派的老佣人曹福的接引下,蔡锷乘三等车到了天津,住进了日租界的同仁医院,而后回到云南,宣布云南独立,后又率兵进川,是为“护国起义”。
品读这段细致的文字可以发现,“云吉班”“梁启超派人”“曹福”“三等车”“日租界”“同仁医院”,这些微观史事信息,在一般谈及蔡锷起义的史书上是不易见到的。邓公的记述起了拾遗补缺和存史的作用。梁启超在护国起义中起到何种作用?蔡锷当时与日本是怎样的关系?邓公讲的这段掌故,可以作为研究这些问题的一种史料参考。
邓公不只是记述掌故,也撰写研究历史掌故的社会史论文。如《中国葬礼的历史演变》《清代物价三百年述略》《上海旧时地价与房租》《颜习斋与读书无用论》《汪辉祖及其著述》等论文,都是他对零散的历史掌故加以汇集、整理并进行学理性研究的结果。所以我说邓公不仅是个掌故家,也是个社会史家。
四、为八股文说句公道话
清代以降,八股文的名声逐渐变臭,最终被废弃。清人徐灵胎讽刺八股文说:“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清袁枚《随园诗话》)全面否定了八股文。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更是恨透了八股文。
但八股文果真没有一点好处吗?邓云乡说,不,八股文也有它的可取之处,不然,它怎么能够延续那么多年,而且明清两代那么多英才都是八股出身呢?为研究八股文,邓公研读过八股文选集《眉园日课》,思考了多年,写出了专著《清代八股文》,对八股文产生的制度原因、源流和历史、文体特征、存废争议、与科考的关系、历史作用等问题,都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他发现八股文是个利弊兼存的东西,弊在内容空洞无物,利在对训练思维能力有用。他评说道:在八股文范围和条件的严格限制下,人的思维能力的集中性、准确性、敏锐性、全面性和辩证性得到训练,练出了这样的思维能力,加上先天的聪明才智,再灵活地运用在实际上,“那便无往而不利,要诗要文,要明断、要深思,要什么就是什么了”。(《红楼风俗谭》之《曹雪芹·八股文》)这实际上解开了在八股取士之下也能产生人才的历史之谜。《儒林外史》有句名言,说做好八股再写诗文,便“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我原来对这话不理解,但看了邓公的论说便理解了。
对于八股文的弊端,邓公也做了深入研究,《清代八股文》专设了《八股的历史副作用》一节。
五、文笔雅隽的散文家
从运笔作文来说,邓云乡可说是一位文笔雅隽的散文家、随笔家。明清史家谢国桢先生称赞邓公的文字风格为“雅隽”,我极以为是;然觉得还可加上“清俊”“萧散”“醇美”“举重若轻”“大俗大雅”等赞词。
以雅隽之文字,道凡俗之物事,此为邓公的绝大本事。一件俗事,一经邓公雅隽文字的“点化”,便雅致可人。拿《燕京乡土记》的标题来说,写白云观燕九节,标题作“燕九春风驴背多”,写过年祭灶,标题是“黄羊祭灶年关到”,其他像“鞭影小骡车”,“消暑清供”,“秋风菜根香”等标题,都是雅隽非常的文字。又如禁城蛙叫,大俗事也,邓公却能联想到晋惠帝听宫蛙的笑话和古人“一池蛙唱,抵得半部鼓吹”的雅趣。北京初春的大风,在平庸写手笔下,必是“呼呼地刮,迎来了春天”一类乏味无趣的文字,邓公却写出了“大黄风一直吹到燕山脚下,吹开了冻土,吹发了草芽,吹醒了柳眼,吹笑了桃花,吹起了昆明湖的波涛,吹白了紫禁城的宫娥的鬓发……”这样美丽的句子。
邓云乡是一位特别注意从古代美文中汲取养料的散文家。例如,他认为古人的许多日记虽是随手札记,并未当作正宗文章着笔落墨,但文字却很优美,其功力决不在宏文高唱之下。他写有《日记文学丛谈》一文详论之。邓公很喜欢清人俞樾的日记文字,在《读俞曲园日记残稿》一文中赞之曰“萧散有致”“炉火纯青”。我断定邓公有意向古人的日记文字学习过。多年来我读邓公文章,总觉得他像是随随便便写的,但醇厚有味,不知是怎么弄的,后来才觉出可能是受过古人日记的影响。在邓文的字里行间,好像能看到俞曲园的影子。
我还愿意把邓公叫作文章家。因为他太懂做文章的门道了,他尤其擅长把散碎的材料组织成一大篇锦绣文章。《鲁迅与北京风土》就是用散碎材料铸成的大作品。此书以鲁迅日记为经,以北京风土景物为纬,因人寓景,古今交汇,使鲁迅和旧北京都“活”了起来。读着这本书,仿佛看到鲁迅先生又漫步在旧京的街巷里,故都的景物风情也尽收眼底。从文章学来说,这本书的架构和材料组织真是妙不可言。
六、读书种子
读邓云乡的书,常会冒出一个念头:邓公真是个读书种子!读书种子者,饱读典籍文献、能延续中华文化之大读书人也。明代方孝孺、清代叶德辉都被称为读书种子,明成祖要杀方,姚广孝谏曰不可,叶德辉是劣绅,革命党要杀他,章太炎说杀不得,可见读书种子之可贵。邓云乡也足可称为读书种子,名副其实,绝非虚誉。冯其庸先生曾问邓云乡,你怎么能写那么多东西呀?邓公答道:“天天写,天天读。”这“天天读”三字,正是一个读书种子的自况。
邓公的居室,可谓书山乱叠,他每日就在这书山中读啊,写啊。从他著述的征引中,便可观其读书之多之杂,正史、野史、文集、笔记、杂钞、县志、日记、书信、游记、传记、说部、诗词、俗曲、俚谚、童谣,可谓无所不读。他写的文章之所以那么有血有肉,盖因得益于读书多,掌握的材料多。比如写冰床,一般人只知道《帝京景物略》和《藤阴杂记》二书的记载,但他又引了鲜见的文献《倚晴阁杂抄》和《水曹清暇录》,这就使人对冰床历史的了解更加细致,使读者知道了原来在清代北京护城河里,还有以拉冰床作交通工具的生意和携酒轰饮冰上的趣事。我很看重邓公征引文献的博杂,因为从目录学上讲,若记录下这些文献名目,便是一份很有用的书单。
邓云乡不仅读书,还研究书。有道是“治学先治书”,邓公深通此道。《旧都文物略》是一部北京史重典,汤用彬等编著,1935年出版。邓公写过一篇研究文章《旧都文物略小记》,把此书从编纂到出版的来龙去脉及重要价值,做了深入研究和详尽阐释。这部书成了他治北京史的重要工具。
《圆明园古籍二种》《清史稿琐谈》,也是他研究书的重要文章。《圆明园古籍二种》可谓一篇圆明园文献的导读,也是一篇圆明园史的研究文章,很有助于圆明园的研究工作。邓公对清史非常熟悉,这与他熟读《清史稿》分不开。他说自己的书架上总放着一部《清史稿》,写清代文人历史掌故时常翻阅此书。他一边利用《清史稿》,一边研究《清史稿》,多有心得之后,写成了《清史稿琐谈》一文。
七、我与邓云乡的一点交往
我与邓公有点交往,起于读他的两本书。因我大学曾写过北京史论文,又素对鲁迅文章感兴趣,所以,一在书店见到他的《鲁迅与北京风土》,便如逢故人,立即买下,并因此记住了邓云乡这个大名。后来又读到了《燕京乡土记》,当时光明日报正在全国搞书评征文,我写了一篇评此书的文章,获得了一等奖。估计邓公看到了书评,因我曾听人转述,邓公说,北京有个李乔,不错。我与邓公就这样隔空相识了。
在北京日报,我编辑过文史版、读书版,曾多次向邓公约稿,我们的交往就多了,但主要是书信往来,只是在他担任电视剧《红楼梦》顾问时,我们在剧组驻地见过一面。印象是他太质朴了,不像民国老派学者那样雍容,更没有居高临下的派头,让我惊异的是,他一个上海人怎么说京腔呢。后来我对邓公的了解加深,崇敬也随之增长,他的学问和人品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典范。
我写过三本社会史著作,《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史研究》《中国师爷小史》和《清代官场图记》。追溯三书的写作缘起,多少都受过一点邓公著作的影响。尤其写《中国师爷小史》时,他的《汪辉祖及其著述》一文对我有发蒙的作用。汪辉祖是清代名幕,他的史料是我研究清代师爷所需的最基本的史料之一。
邓公的书斋名“水流云在轩”,取无争、舒缓之意,类如陶渊明之“云无心以出岫”。邓公做人,正派、平实、自然、不张扬、不自夸。我自觉多少受过一点邓公人格的影响,或者自豪一点说,我与邓公属于同一类人。我有过升官的机会,但我舍不得书斋。邓公,还有孙犁、黄裳等先生的书,对于我坚定一辈子穿长衫,不穿补服,有过楷范的作用。
邓公的文稿是极易编辑的,因为几乎无懈可击,几乎不用编。若改动也是因版面有限而删节。邓公有时写得长了,不知能否全文发表,便在原稿上画出可以删节的地方,以使编辑既省事,又不为难怎么删节。我还保存着这样一篇手稿,每睹之,总会心生感动。
邓公身上很有点民国文人气,现在叫民国范儿。他写信常用毛笔和花笺,还特制了一种自用笺,前端印“红楼”二字,末端印“水流云在之室自用笺”。邓公贺年,也沿袭旧俗老派。一次我逛潘家园,看到一张信纸大小的贺年片,毛笔书之,字迹圆润秀劲,署名“晚邓云骧”,有“水流云在之室”印。这无疑是邓公之作,是写给一位前辈先生的,我立即买了下来。以毛笔亲书贺年片,这比时下流行的短信拜年不知要增重多少情谊。传统文化的好东西,邓公总是倍加爱惜并勉力行之。
余话
我赞成止庵先生的话,“世间再无邓云乡”。邓公的本事,难学;邓公的特殊价值,不可再生。有时我看到北京的某个文物被毁了,某条古巷消失了,就想,若是邓公在,写一篇关于这个文物、这条古巷的文章,登在报上,也许它们就保存下来了。但世间再无邓云乡了。惜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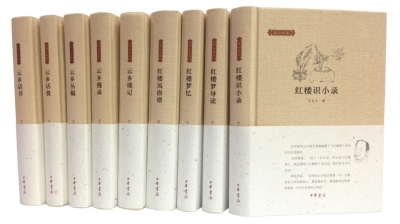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