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刘兵
□刘兵兄,我一拿到快递送来的《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研究》一书,就马上想起一则学术八卦:记得多年以前,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间破旧的办公室中,你和章梅芳两人花了两个小时,试图说服我,让我相信,在引入女性主义视角之后,科学史的研究就会别开生面。不幸的是,当时你们没有成功。我想这一定被你们解读为“江晓原的学术偏见顽固不化”。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我发现我越来越宽容、越来越能够接受以前曾经排拒的东西了,对后现代的某些玩意儿也日见亲近。另一则八卦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激烈抨击北大邀请周星驰演讲之后几年,我居然亲自接洽安排了周星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可见人是会变化的。我40岁前,读书读文章接触人物,首先发现的是其书其文其人的缺点;而40岁后,我读书读文章接触人物,首先发现的则是其书其文其人的优点了。
在这样的变化之下,你得意女弟子的博士论文成书出版,我当然乐见其成,也非常乐意就此书和你讨论一番。章梅芳年轻有为,在学术上勇猛精进,有人甚至将她戏称为“刘兵的钮卫星”。猜想起来,和这样多年一直秉持“君子和而不同”之旨的老友,讨论自己得意女弟子的新著,应该是相当有趣的事情吧。
■确实,你说的那件事到现在我们都还清楚地记得,而且还偶尔会提起,似乎类似的情形还不止一次出现过。现在再次谈起这一话题,自然还会是很有趣的讨论。
这次选谈这本书,其实还有几重特色。你说的“刘兵的钮卫星”——确实章梅芳是我得意的学生,而且她不仅在读期间就表现突出,工作以后依然有着高质量且高数量的研究产出。除此因素之外,女性主义,你也知道,一直是我关注而且非常感兴趣的领域,我们又长期对此有一定的分歧。但正是因为有分歧,有讨论,学问本身也才会有长进。章梅芳这些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对女性主义的继续深入思考和研究。
你说随着年龄增长而宽容心增加,这似乎有些道理,但同时,也可以解释为随年龄的增长而对学术的理解有所变化。我倒是宁愿你不仅仅因为生理年龄增长而对女性主义这样在许多人眼中的“异端邪说”更加宽容,并愿意继续讨论它,而是更想听到你在这么多年之后,对女性主义又有了什么新的看法。
□我现在对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看法——注意不是对“女性主义”的看法——确实和当年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那间破旧办公室中的看法有所不同。记得当年我认为,“女性主义科学史”不会给科学史研究带来新东西,因而它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即使女性主义科学史没有带来新东西(到底能不能带来新东西,我们下面可以再讨论),只要它能够对已有的结论或图像提供一种新的解释,甚至只是提供一种新的描述方式,就有存在的价值——何况我们可以认为“新的解释”或“新的描述方式”本身就可以视为“新东西”的一部分。
打个比方,这有点类似这样的情形:一道科学史的题目,传统科学史已经获得了答案,现在女性主义科学史表示:我可以用另一种方法解这道题。如果女性主义科学史解出了新的答案,它当然就提供了“新东西”——考虑到历史的建构性质,我们可以认为这道题不存在标准答案。我这里想强调的是,即使女性主义科学史解出的答案与传统科学史解出的答案相同,只要它的解法和路径与传统科学史的不同,它就仍然有存在的价值。
我估计,我的这点转变,很难让你满意。我知道,你应该是国内“最早对女性主义科学史给予关注和重视”的人之一,章梅芳在书中提到了你的工作和贡献。她指出:你认为“女性主义科学史本质上有一种科学批判的取向。它能够提供给传统科学史以新的视角、问题和分析维度”。
■呵呵,在这一点上,你确实还是有所变化的——尽管正像你所说的,可能离我希望的变化还略小一点而已。但这已经很重要。
这里的要点是:什么才是“给科学史带来的新东西”?例如,当科学史家没有意识到辉格解释的问题的时候,提出了历史的辉格解释这一问题,从此,科学史家对科学史本身的意识和理解,就已经有许多“新东西”了。
科学史作为历史的一种,不可能没有人的参与,而人,又是有性别划分的,而传统中,对于传统的科学史中所展现的性别上的不平衡的现象,女性主义从性别的立场上给出了新的解释、新的说明,甚至提出了新的性别概念(社会性别),甚至将问题延伸到性别背后更深层的对科学自身的理解,这些还不算是有意义的“新东西”吗?
□这些当然没问题,但“一种科学批判的取向”到底是什么呢?这种取向是不是只有女性主义科学史才有可能提供呢?愿闻其详。
还有,你指出科学史不可能没有人的参与,而人又是有性别的,那么,科学史研究者的性别,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会有哪些意义?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论证“女性主义科学史”学术意义和必要性的重要方面,也愿闻其详。
■关于科学史中“科学批判的取向”,固然许多理论立场或思潮都具有,像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论、后殖民主义等。但与之相比,女性主义专注从性别的角度,提出科学也是打上了性别烙印的观念,却是其他一些理论所不曾明确提出的,而且,这种性别烙印在女性主义科学史发展的后期,又不仅仅限于生理性别的科学家在科学中的表现,而是被用于对科学之本性的分析上,这也是女性主义所独有的。当然,女性主义科学史在这方面特殊的意义并不限于此。总体地讲,可以说是它提出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已有编史纲领的新的编史纲领和研究方法论,其中蕴含了“科学批判的取向”,又不仅限于此。
至于你的后一个问题,可能有一点误解,其实我说的意思,讲研究参与者的性别,本来是指作为科学史的研究对象的进行科学研究的人的性别,而“女性主义科学史”,其实是指从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来考察和解释科学的历史,这样的研究的学术意义和必要性,在对前一个问题示例性的回答中也已经涉及了。而且,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特殊的方法论的问题,在书中亦是有专门论及的。不过,你提出的,科学史研究者(也即科学史家)的性别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影响,这倒是另一个有待研究的新问题,似乎目前还未有专门的研究,而章梅芳的书中也还未涉及。
□我注意到,章梅芳在本书绪论中,已经明确区分了科学、科学史、科学编史学三者的研究层次,并指出三者的研究对象依次为自然、科学和科学家、科学史和科学史家。借用北大刘华杰教授喜欢用的措词,那就是:科学研究是一阶的,科学史研究是二阶的,而科学编史学研究则是三阶的。
注意到这一点之后,再来看章梅芳在本书第三、第四章中,所叙述的由西方学者进行的12个可以归入女性主义科学史范畴的研究案例,就可以发现,在一本编史学研究著作中,提供这样的案例述评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尽管我们明确知道本书是在进行三阶研究,我仍然抑制不住某种强烈的期盼心情在我阅读过程中的萌动。这种期盼最初是某种“不满足”的感觉,后来我掩卷沉思,终于逐渐明白我的期盼是什么了——我是在期盼章梅芳向我们展示某种她自己的二阶案例!比如,在这12个二阶的案例中,有一两个是出自章梅芳之手的工作,那将多么精彩!
也许你会质问:为什么要期盼一部三阶研究著作的作者做出二阶的案例呢?这会不会是求全责备甚至没事找事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对于这位“刘兵的钮卫星”,我有着持久的好感。我的期盼,来源于我对国内科学史界学术生态的多年感受。
其实,在刘华杰教授多次强调一阶、二阶、三阶研究的层次及对象区别之前,许多科学史研究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如果说他们对于“科学研究者”和“科学史研究者”的区分还比较清楚的话,那他们对于“科学史”与“科学编史学”的区分肯定是模糊的,甚至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种区分。因此在评价学者时,很容易因为没有注意到“科学史”与“科学编史学”的区别而产生误解。还在我念研究生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这种误解就已经在我周围的前辈学者中表现出来了。在那样的氛围中,要想得到圈子里的认可,通常必须做出足够好的二阶研究工作。
或许我们还可以有一个适度推广的推论:仅凭N+1阶的研究成果,通常很难在N阶圈子里获得认可。例如,仅凭科学史研究成果,通常很难在科学界获得认可。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我才会期盼章梅芳自己的二阶案例。对于本书而言,没有这样的案例确实不足为病,正如你在序言中所说,作者已经“非常理想地完成其设定的任务”。但是对作者进一步成长来说,展示自己的二阶研究案例,肯定会有助于她更上层楼。不知你以为如何?
■这样说来,我们就没有矛盾了。关于你上面的推论,其实好几年前,我就在《科学编史学的身份:近亲的误解与远亲的接纳》(《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第4期)一文中,有过比较系统的分析,我还进而提出:“被研究者,总是对于研究者和研究者的成果有所保留,甚至于不理解和反感。”例如文学家对于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态度是如此,科学家对于科学哲学家以及科学史家的态度也是如此,科学史家对于科学编史学家更是如此!
而且,因为研究“阶”数的不同,所依据的一手文献便也不同,但作为研究的成果都是原创性的。以往许多科学史家认为,科学编史学的研究并非基于一手文献因而并非原创,也正是混淆了这一点。如按照此逻辑,那科学家们岂不是也可以同样批评科学史家的研究非原创吗?因为科学史家的研究对象不也是科学家及其写出的科学论文而非科学家所研究的自然吗?显然,对研究阶数的理解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
至于你的期盼的“二阶”研究,其实章梅芳一直也在从事中,例如,她与我合作的关于“坐月子”问题的女性主义研究,便属此类。另外还有其它一些研究,包括她指导学生所做的学位论文的选题等。只不过,在这本专门研究科学编史学的专著中,或许是因为经典性等方面的考虑,没有收入她自己所做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直接案例而已。但我相信,未来她一定会专门出版自己的女性主义科学史“二阶”研究专著的。
最后,与我们以前的讨论相比,这次你在字里行间所显示出的你所持的立场和见解,我觉得还真是有很大转变。作为女性主义研究者,能看到这样的转变(哪怕未来仍有可继续转变的更大空间),肯定是非常欣慰的。当然,从一般性的女性主义研究者的经验来看,肯定也会意识到,要让更多的学者以及非学者在意识上有性别立场的转变,依然任重道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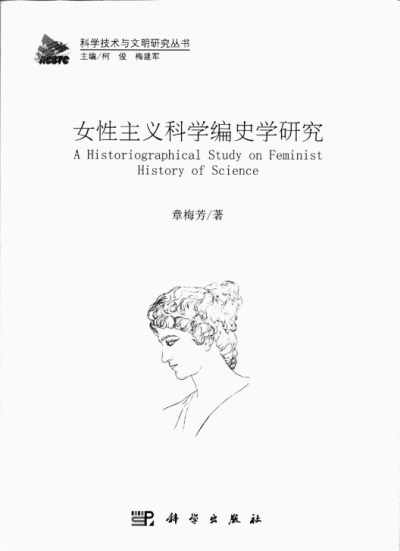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