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出版后,我生活的变化就是从业余写作转为专业写作。从此,文学成了我的职业,也成了我的生计。所幸,我能够靠自己手中的笔养家活口,过上有筋骨、接地气的普通生活。我很感谢文学。没有文学,我不知道自己如何在这世上存在。
我从二十三岁起就在机关里工作,目睹了很多叫人可为感怀的人和事。不平也罢,不公也罢,黑白也罢,一股沉闷压抑之气,越来越逼得我透不过气。于是,我开始写小说。
十六年前,三十六岁的王跃文以《国画》一举成名,也从此被戴上了“官场小说家”的帽子。
创作近三十年来,从官场到文坛,王跃文一路经历了很多,也看清了很多。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小说,王跃文的写作满怀深沉的忧患意识,显示着凌厉的批判锋芒。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对知识分子来说可贵的是其批判态度。任何时代,应该允许有批判的声音。
这种批判的精神在不同的作品中有不同的表达。评论家雷达就从王跃文的小说集《漫水》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这部小说集营造了恬静的世界,体现了传统的道德和人性之美。
走近王跃文,看这位温文儒雅却充满个性的小说家如何在文学的疆场中驰骋,又如何在文字中锋芒毕露。
不读网络文学
读书报:您的作品有电子版吗?在与出版社签合同时,会介意数字版权吗?现在是否有数字阅读方面的收益?
王跃文:电子版权目前很混乱,基本状况是在坑作家。我今后会对电子版权的授权持谨慎态度。我甚至想呼吁作家们团结起来,在电子版权运营未做到诚信之前,拒绝出让任何电子版权。
读书报:您关注网络文学吗?官场小说在网络上尤其盛行。
王跃文:不太关注。我几乎没有在网上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没有看出任何网上的所谓官场小说,所以不能不负责任地评论。
读书报:从唐浩明的《曾国藩》、阎真的《沧浪之水》、肖仁福的《官运》、《待遇》以及浮石的《青瓷》等作品,湖南作家群关注现实的官场小说力作颇成气候。
王跃文:湖南作家似乎确有很重的社会关怀情结,我认为这是值得敬重的。湖南有一批这样的作家,其作品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深受读者喜爱,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
读书报:湖南是否也成立了网络作家协会?湖南省的网络文学发展情况如何?
王跃文:湖南目前没有成立网络作家协会,正在考虑成立网络作家学会。湖南网络作家创作活跃,有很多在全国有影响的网络作家。
参评茅奖遭劝退
读书报:1999年的《国画》使您一举成名。之前您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王跃文:我出版《国画》之前,一直是在机关工作着的业余写作人。当时,我每年创作一两个中短篇小说,但每次发表出来都会受到关注,或被权威选刊选载,或评上有关文学刊物的奖项。我从县级政府机关,一直工作到省级政府机关,都是从事机关文秘工作。年轻时有从政理想,慢慢看破些门道就放弃这个想法了。我后来对同事开玩笑说,你们在这里干为的是做官,我不过是就业而已。这话至今还被老同事们提及。我以就业心态在大机关里呆着,日子过得很平淡自然,完全成了所谓官场的观察者。
读书报:《国画》的畅销也给您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王跃文:《国画》真实地描写了现实生态,反映复杂环境对人的心灵的扭曲,以及人在强大现实面前的挣扎和无助,小说笔触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光明和温暖。
小说出版后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我从此离开了政府机关。客观上讲,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我有机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也算是遂了我平生心愿。别人看来,我离开大机关应该是遭遇了天大的事情,我自己却是自得其乐。所谓得失,要看你需要的是什么。所失并非你所需,反而可能就是得。
读书报:《国画》是否入围过茅奖?王跃文:我从来没有指望过《国画》获茅盾文学奖,我就连申报的积极性都没有。当时,省作协坚持申报,我手里样书都没有。市面已没有《国画》卖了,只有铺天盖地的盗版。我买了五本品相好的盗版书作为申报资料,说来也是件好玩的事。评审过程中,中国作协一位副主席打电话来,说明天到长沙来同我聊天。我问什么事,他说见面说吧。
按理,中国作协的领导来了,我应该报告省作家协会。但是,这位领导说,不用告诉省作协,我们只是以私人朋友身份见面。这是一位同作家关系非常好的中国作协领导,我对他非常尊重。我很理解中国作协的难处,二话没说就同意退出评奖。我们约定,此话不对外说,怕产生负面影响。
后来,听很多当年参加评奖的评委说起这事,因为《国画》给大家的印象很好,而这部小说当时有些敏感,万一评上了怕弄得各方面尴尬。最好的办法,就是作家自己退出评奖。“被”字结构的表述是后来网络上发明的词,但我退出评奖谈不上“被自动”,因为我本来就不打算参评的。
读书报:《国画》有过退稿经历吗?王跃文:《国画》没有过退稿经历,出版很顺利。小说的责任编辑是刘稚和周昌义。说到这部书的创作缘起,可以说是个“阴谋”。我因为在《当代》发表了好几部中篇小说,刘稚看了非常喜欢,就征求周昌义的意见,可否约我写写长篇。周昌义说,王跃文的小说个人味道很足,但仅靠那些个人味道能否撑得起长篇?约他写写,试试看吧。于是,刘稚同我电话联系,鼓动我写长篇小说。
我写了大约一年,小说完成了。周昌义和刘稚看了,都非常激动。拿周昌义的话说,依然是王跃文小说的固有味道,居然就把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撑起来了。刘稚和周昌义作了很辛苦的编辑工作,把个别地方我自己得意的文字去掉了。这是编辑的职责所在,我没什么可说的。事后,周昌义在自己的书里说起《国画》约稿和出版过程,我才知道这些故事。
读书报:《国画》出版后,您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跃文:《国画》出版后,我生活的变化就是从业余写作转为专业写作。从此,文学成了我的职业,也成了我的生计。所幸,我能够靠自己手中的笔养家活口,过上有筋骨、接地气的普通生活。我很感谢文学。没有文学,我不知道自己如何在这世上存在。为官黑不起,经商奸不来,作苦力体格又不健壮。
读书报:直到今天,《国画》仍成为官场小说的标高。回头看来,您觉得《国画》对您而言,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王跃文:我不敢说《国画》写得怎么好,不过只是我的真诚血性之作而已。我从二十三岁起就在机关里工作,目睹了很多叫人可为感怀的人和事。不平也罢,不公也罢,黑白也罢,很多事说起来都是鸡毛蒜皮。但是,正是种种摆不上桌面来说的琐碎之事消磨着我们的人生,让很多看似简单的事情变得无可奈何。一股沉闷压抑之气,越来越逼得我透不过气。于是,我开始写小说。先是写了一系列的中篇小说,后来就写了长篇小说《国画》。我想用这部小说告诉人们,我们的生活本可以变得更好的。小说里的那些人,都被某只无形的手拉着往下坠,他们都是值得同情且应该得到救赎的。
狗皮膏药
读书报:您写过一系列的官场小说。但是从影响力上看,似乎都未能超越《国画》。什么原因?
王跃文:所谓官场小说,我一直以为是媒体贴在我身上的狗皮膏药。《现代汉语词典》对官场的解释是: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虚伪、倾扎、逢迎、欺诈等特点。《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修订时,在“贬义”前面加了“多含”二字。原因也许因为官场这个词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得越来越多了,而从道理上讲又不方便把官场都看得贬义。这是词典编辑们遇到的现实尴尬吧。事实上,某些官场中人的确是把自己“贬义”了。因为“官场”二字的词性之故,我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小说叫做官场小说。这是其一。其二,对作家及其作品任何类型化的描述,都是贬损。我不同意。
《国画》之后,我出版过《梅次故事》《朝夕之间》《苍黄》等好几部小说,都是畅销且长销的。我的任何小说集、杂文随笔集也是畅销且长销的。没有像《国画》那样爆炸性的影响,一则是读者对我作品有了平和的接受态度,二则是我的作品长期没有得到堂而皇之的宣传和评介。影响在民间,读者是判官。所幸,我的所有小说现在都在正常出版。
读书报:在写作中,您觉得心里有没有表达的障碍?是否有意规避很多东西?
王跃文:我不觉得有表达障碍。我的写作是自由的,率真的。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去。如果有人觉得有的文字有什么出格之处,肯定不是我的问题,而是生活本身的问题,而是某些人自己目光有问题。自古固然有写坏书的人,但作家们整体上讲都是有职业道德的。
作家反应现实生活,其笔触永远达不到现实的真实程度。现实的复杂和严酷,大大超过作家的想象能力。即便如此,作家手中的笔稍有不慎,就会背上给现实抹黑的名声。客观存在的某些黑,作家有能力把它抹白吗?白的抹不黑,黑的抹不白,这是起码的常识。但是,我也并不主张作家的创作要同生活比复杂、比厚黑、比残酷。作家的才智是比不过现实的荒诞的,文学也未必非得如此。
读书报:从早期的《国画》到最新的作品,您的创作心态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王跃文:也许是年龄的原因,我的创作心态越来越平和了。同年轻时的郁愤悲凉相比,内心多了些温暖、理解、宽容。但是,这并不等于我认同现实中存在的消极和负面。
《大清相国》有现实意义
读书报:《大清相国》初版是2007年。当时出版反而没有现在的影响,是因为王歧山的推荐吗?
王跃文:《大清相国》从出版到现在,总发行已超过一百多万册,文学作品的发行这已经是个很大的数目了。当然,去年开始再度火爆,原因有些特殊。
读书报:作品塑造了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相,写作中做了怎样的准备?
王跃文:我不是专门做历史研究的,没有能力阅读大量史料。陈廷敬是顺治朝的进士,为官及功业主要是在康熙朝。为了写这部小说,我把顺治十八年间和康熙六十一年间发生的大事桩桩件件都看了。写历史小说光看正史不行,还得读大量杂书才得触摸到历史的体温和肌理。可以说,《大清相国》里写到的任何故事都是陈廷敬做官那些年发生过的,我在此基础上加以文学虚构。
读书报:《大清相国》中最难处理的部分是哪些?这部作品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王跃文:我从陈廷敬二十岁中举,写到他七十岁告老还乡,时间跨半个世纪。最难处理的就是时间问题,中间做了些时间跳跃。有人批评说《大清相国》仍在宣扬封建清官意识,缺乏时代性和现代眼光。这种批评看似有道理,其实未必。简单的清官崇拜固然不可取,但我写历史人物时不能超越历史,况且不论在什么社会背景下陈廷敬身上的清廉和勤勉都是可敬可法的。对简单的清官崇拜的批判,前人早有意识。雍正皇帝登基第二天,就专门对知州知县下谕说不得“或借刻以为清,或恃才而多事”,这比《老残游记》的清官批判早了一百八十多年。
读书报:五年前采访您,您曾经用“痛苦”形容看到自己文字的感受,总觉得小说背后的东西挖掘得不够,缺乏厚重性,更谈不上哲学层面。
王跃文:我现在仍然觉得自己的小说厚重不够,宏大不够,更不够哲学。
读书报:《爱历元年》心平气和又无耐地写尽社会乱象。为什么总是感情出轨?在您的笔下却尽是善良、隐忍、克制甚至真诚。为什么会这么表达?
王跃文:《爱历元年》不过是正视了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状态而已,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善良的,他们的情感变故都是情非得已,而他们的自我救赎或情感回归都是生活的真诚召唤。我坚持认为这是一部真诚的情爱之书、生活之书、命运之书。
读书报:《爱历元年》申报了茅盾文学奖,您觉得希望大吗?
王跃文:《爱历元年》是出版社申报参评茅奖的。谁能保证自己的作品会获奖?顺其自然吧。
读书报:您的性格适合官场吗?
王跃文:我的性格是外柔内刚,讲原则,但不迂腐。《论语》载有子夏的话:“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此话,我深以为然。但是,我的性格不适合在官场里混。我内心有原则,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原则做人做事。我在生活中,不与人争高低,也不争名争利。很多人和事,我会看在眼里而不道破。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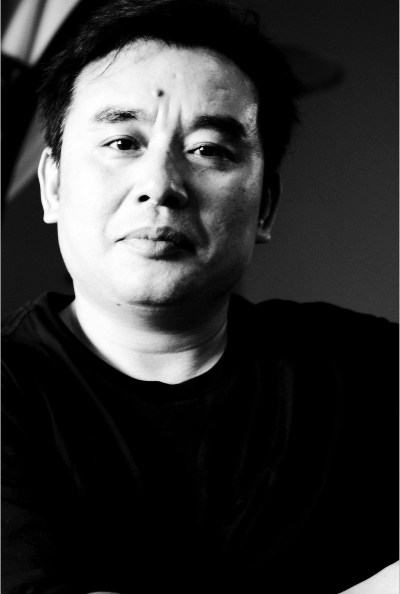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