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知苗德岁先生“中英文俱工”,但听说他要翻译《物种起源》,心里还是暗暗地替他捏了一把汗。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笔者读过的为数不多、但印象至深的长篇巨著之一。除了它对人类认知的巨大影响,这部作者自称的“概要”,长达400多页,内容繁杂而琐碎,论据和论理全面严谨;涉及当时的众多前沿科学:地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人工养殖、动植物杂交……如是,译者即使不是这每一个方面的专家,也至少需要有足够广博的基础知识,才能考虑揽这“瓷器活”。这还仅仅是就内容而言。几乎所有的资深评论,还会一再提及达尔文独特的文字风格。达尔文善用复杂的句式,而且句句话一定要说得天衣无缝。粗读会觉得他啰嗦,艰深晦涩;但仔细品味,又会被他严谨清晰而且独特的表达所折服。这既是一部科学巨著,却又富有个性。这大概才是《物种起源》成为经典的根本所在——如果只想了解进化论,翻一翻现代教科书足矣。而阅读达尔文的书,包括《物种起源》,不仅仅能获得知识(甚至不主要是为了获得知识),似乎更是一个满足好奇心、增加洞察力、甚至如同审美一般的愉快经历。
但对翻译者而言,这样的书无异于译林世界的一条古蜀道: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苗先生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专家,专业与达尔文的学识有相当大的重合;他又是一个好学、好奇心极重的人,爱读善写,确实是翻译这部书的上佳人选。但正因为如此,苗先生大概比谁都更清楚这个课题有多难:哪怕步步谨慎,也难免偶尔一脚踏空,虽无性命之虞,结果凝固在纸上,也够让人“侧身西望长咨嗟”。 毕竟,翻译是为人作嫁,译得好的地方,那是原作者的功劳;一有不合意之处,则是译者的“水平所限”了。 那么,苗先生“蜀道之行”进行得怎么样? 我几乎是被好奇心驱使着,急急地翻开了书。
苗先生丰富扎实的专业知识,在翻译中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整部书,几百页的译文几乎没有错漏,更不用说许多翻译文献里频繁出现的误译和想当然的编写。仅这一条,就是很大的成就了。更难得的是,译者似乎还有意识地下功夫,要把达尔文所用的表达形式,有时甚至每一个具体的词汇都对应地表达出来。这就给了整部书一个明显的、贯穿一致的语气和风格,原作者的文字特点也略见端倪。可以想象,由于中英文结构的巨大差异,在很多时候,这近乎不可能。静夜孤灯下,殚精又竭虑,个中甘苦,大概只有译者自知。
因为读者最愿意体会的,恰恰是“无知”:译得精彩完美之处,文字变得通顺自然、踏雪无痕;翻书的人会浑然忘记自己是在读“翻译的东西”。下面这一段,就让我回想起当初读英语原文的轻快:
就我所熟悉的实例中,一种动物看似纯粹是为了另一种动物的利益而从事活动,最为有力的例子之一当推蚜虫自愿地将其所分泌的甜液奉送给蚂蚁:下述事实显示,它们这样做乃是自愿的。我把一株酸模植物(dock-plant)上混迹于一群大约十二只蚜虫中的所有蚂蚁,全部移走,并在数小时之内不让它们回来。过了此段时间,我觉得很有把握,蚜虫该会分泌了。我通过放大镜对其观察良久,但无一分泌的;我便用一根毛发微微地触动及拍打它们,我尽力模仿蚂蚁用触角触动它们的方式,依然无一分泌的。其后,我让一只蚂蚁去接近它们,从那蚂蚁急不可耐地扑向前的样子看,它似乎即刻感到它发现了丰富的一群蚜虫,于是它便开始用触角去拨动蚜虫的腹部,先是这一只,然后那一只;而每一只蚜虫,一经感觉到蚂蚁的触角时,即刻抬起腹部,分泌出一滴清澈的甜液,那蚂蚁便急忙吞食了甜液。即令十分幼小的蚜虫,也是如此行事,可见这一活动是出自本能,而并非经验所致。然而,由于分泌物很粘,将其除去,大概对于蚜虫来说,不啻是一种便利,因此,大概蚜虫们也不尽是本能地分泌以专门地加惠于蚂蚁。(168页)
下面这个句子,要表达的内容非常复杂,苗文的表达方式却不累赘,并且相当准确:
当这些变种重返故地时,由于它们业已不同于原先的状态,即便也许只是在极其轻微程度上的不同,但却是几近一律地不同,所以,按照很多古生物学家们所遵循的原理,这些变种大概便会被定成新的、不同的物种。(240页)
“‘大自然’虽奢于变化,却吝于革新。”(154页)这一名句译得尤其精彩,因为译文与原文一样工整并言简意赅: Natureisprodi⁃galinvariety, butniggardinin⁃novation.
“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也将从中得到启迪。”(388页)这一句的好处在于与原文一样低调含蓄。所有读《物种起源》的人,都会找这句话,因为这是全书唯一暗示人与生物之渊源的地方。
苗先生最得心应手的一个技巧,是频繁使用恰如其分的成语或俗话,有时并加上机智的再创造和重新组装,来表达相应的英文词意。这样一来,词汇变得丰富多样,表达也更生动;既助读者理解,还能使之不时会心一笑。这里顺手选几个例子:
但是,正如其后我们将看到,“自然选择”是一种“蓄势待发、随时行动”的力量,它无比优越于人类的微弱的努力,宛若“天工”之胜于“雕琢”。(51页)
据说,最好的短喙翻飞鸽中,“胎”死“壳”中的远比能够破卵而出的要多。(71页)
我只能重复我的担保,敝人是无征而不语的。(169页)
令其对时间逝去如斯能有一鳞半爪的理解。(224页)
这将是完全自然的,盖因它通过最密切的亲缘关系,把废弃了的语言与现代的所有语言连在了一起,并且令每一种语言都得以追本溯源。(336页)
偶开天眼觑前程,我们或可预言……(389页)
译者扎实的专业及广泛的背景知识还表现在“译注”中,虽偶尔为之、寥寥几笔,却提供给读者难得的视角和思考的机会,从而增加对内容的领悟。
前面已经提到,整本书的内容翻译得非常准确,几乎没有错误。我只注意到下面几处,提出来商酌。
我们必须假定,该器官的每一种新的状态,都是成百万地倍增着;每种状态一直被保存到更好的状态出来以后,旧的状态才会被毁灭。(150页)
这一句是指些微变异的出现是连续不断地,(些微)好的状态得以保存,淘汰旧的,这个过程不断重复,达“乘以一百万次”计,而不是“成百万地倍增着”,如此慢慢积累,器官因而达到功能或结构的完美。
苗注:作者言及的这两项原理是:一是在发育中,相继的变异出现得迟而不早,就像是在不断地添加似的;也即作者上面刚刚讲过的:“每一物种获得现在的结构所靠的很多变异,其中的每一个变异,很可能不是在生命中的很早时期发生的”……(353页译注)
这个译注的前半句,没有提供比引文更多的信息,而且不准确:原文没有“不断地添加似的”的意思。达尔文观察到,有的变异在生物成体才表现出来,他推测这是因为该变异在幼体时无用。用现在的知识看,或许可以解释为,这是因为调控生长的不同阶段的基因的表达是有时限的;这些基因所造成的变异因而在幼体时期观察不到。
译文更普遍的缺点是,因为照顾原意或原来的行文结构,文字有时显得生硬或者难懂;有些时候副词或形容词堆砌,或选用的多义词的词意差强人意,使得句子不凝练,表达含糊。
在靠交配来生育以及有着极高的移动性的动物里,有些悬疑类型,也会被一位动物学家列为物种,而却被另一位动物学家列为变种,但它们很少见于同一地区,却常见于相互隔离的不同区域。(40页)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些动物类型并不同时出现在同一区域,使得分类学家难以比较,因此容易产生不同的判断。关键词“separated”,在这里主要指彼此分开,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了,而未必是严格的“隔离”。试译:在靠交配来生育并极易迁徙的动物里,那些被一位动物学家列为物种,而却被另一位动物学家列为变种的悬疑类型,很少会在同一地区被发现,但却常见于各自的地域。
但我相信,与所谓本能的偶发变异的自然选择的效应相比,习性的效应是颇为次要的;本能自发变异是由一些未知的原因引起的,这些未知的原因也同样产生了身体构造的些微偏差。(167页)
这句翻译没有表达出原文对不同内容的轻重程度的处理,或会造成阅读理解上的困难。试译:但我相信,相对于在自然选择作用下的本能的(可以被称作)偶发变异所造成的效应,习性的效应是颇为次要的;本能自发变异是由一些未知的因素引起的,同样的未知的因素也造成了身体构造上的些微偏差。
因而能比同一地方的其他生物占有优势的话,它便会攫取那一生物的位置……(148页)
“someother”应该译作“另一个”(不定指的,单数),而不是“其他”(复数)。
尽管每一套地层的沉积无可争辩地需要漫长的年月,我还能见到几种原由说明,为什么每一套地层中……(233页)
“Icansee”:我还可以想到,推测出。
这后一条规律里最为有力的一个明显的例外,即巴兰德所谓的“入侵集群”(colonies),它们一度入侵到较老的地层中,从而让先前生存过的动物群重现;但莱尔的解释我看似乎是令人满意的,即这是从一个不同的地理区域暂时迁徙的情形。(249页)
“apparent”:使用其“表面上如是”的含义,整句话就能清楚很多,因为这里谈到的规律是物种一旦灭绝就不会再现,这个规律是绝对的,不可能有例外的。
但这些都是对细节的吹毛求疵,也包括笔者自己的偏见和局限。我从阅读和对这些句子的推敲中认识到,除去明显的功用和社会意义,翻译名著是对个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的挑战,就好比写诗为格律所限,“戴着镣铐跳舞”。这样的知难而上会激发思考和创新。这是很有意义和趣味的努力。大概每一个学过两门以上语言的人,一生都应该读几本好的闲书,甚至不朽的经典之作。如果热爱到竟然想提笔翻译,中译外,外译中,个人既得乐,他人也得益。
苗先生也因此成了达尔文专家。我要是译林的编辑,一定请苗先生把达尔文的“四部伟大作品”都翻译了。至少,一定要译他早年的《小猎犬航海记》。这部书与《物种起源》相映成辉,对译者和读者都将是又一次获益匪浅、但更轻松愉快的登峰之旅。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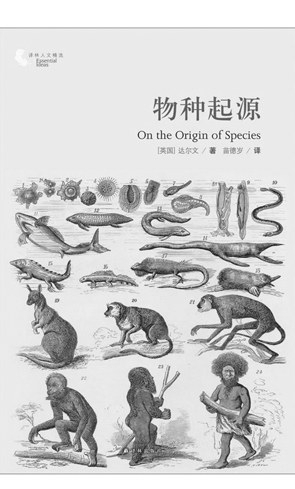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