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文献搜集与研究工作,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已经取得不斐的成就,各类书目、文献集陆续问世,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小说研究。然而,这些工作也有共同的不足:一是著录的书目不全,即使是著录最多的樽本照雄先生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2002年),不仅单行本尚有缺漏,报刊小说也基本未著录;二是皆侧重于对作家作品的介绍。近代小说的时间跨度虽只有72年,却是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过渡转换阶段,若仅是作家作品介绍的叠加,难以展现近代小说进程全貌,且无法解释其行进轨迹的动因。这一领域研究要继续向纵深推进,亟需有系统、立体且更齐备的基础工作的支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华东师范大学陈大康教授的《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就属于这一性质的专著。此书共著录4204种报载小说、1393种单行本以及各类相关资料,其中有千余种作品从未被著录或论及,而大量有关近代小说的资料,也在书中初次面世。
《编年史》的采选标准是遵循“五要素”原则,即作者、出版、小说理论、读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该书作者曾成功地运用“五要素”共同作用的研究模型,撰写了《明代小说史》。近代小说发展过程中,这些“要素”表现出具有时代性的新特征:一是新增了报刊等新的传播方式,传统的书坊逐渐由近代书局所代替;二是翻译小说的出现,也影响了小说发展的走向。根据“五要素”采选原则,《编年史》著录了自道光二十年(1840)至宣统三年(1911)共72年有关小说的重要事件,包括新作品问世、已有作品再版、作家概况、重要理论论著、清政府关于小说的政策以及小说出版机构等。
《编年史》中同治末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部分,载录了不少传统小说出版的资料,这看似与近代小说无关,但却反映了印刷业近代化的动向,它是小说后来迅猛发展在物质层面上的充分准备。又如读者对报载小说这一新的传播方式开始并不习惯,《申报》创办时曾刊载过三篇翻译小说,后因遭市场冷遇而匆匆收场。十年后《沪报》连载传统小说《野叟曝言》却获得巨大成功,此后各家报刊纷纷效仿,终于使刊载小说成了报界时尚,读者接受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逐渐改变了阅读习惯,这些对近代小说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这些资料也在《编年史》的采录范围之内。
《编年史》采用了介于年谱与文学史之间的编排体例,既能直观地呈现近代小说发展的盛衰起伏,又将之置于近代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使近代小说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开放立体的大系统。该书还根据资料的实际情况,在按时序编排的基础上,尽量精确到月或日,并辅以必要的考辨与评述,生动而清晰地呈现小说史行进的线索,也澄清了不少史实。随着时间的推进,与小说相关的事件越来越多,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始,《编年史》按日记载的内容迅速增多,而那些资料在提示人们,“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实际上是渐进过程中的一次显现,并非先前一些学者所认为的“突变”。《编年史》收录了过去人们未发现的北京“小说改良会”的《小说改良会叙》,后来梁启超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可视为“小说界革命”的纲领,可是它的基本论点、论证方式及其行文语气,都与此文相似,只是它以欧美小说为例证,而梁启超是改用日本小说。《编年史》还收录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征集严复、夏曾佑在光绪二十三年发表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的广告,该文的很多见解,都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主张中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他在光绪二十八年末的倡导与鼓吹,实是那些年众人理论主张的归纳总结。至于“新小说”的创作与翻译,此前也出现不少。
作为主体部分的重要辅助,《编年史》的“导言”和“附录”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导言从学理上厘清了“近代小说”的概念,并质疑“二十世纪小说”概念的科学性;对以往因资料局限而出现的误判也予以纠正。如学界历来对傅兰雅之“求著时新小说”的活动评价甚高,认为是晚清“新小说”的先声。然而通过细读150篇来稿及所附信函,考察应征者身份,分析来稿之内容与形式,《编年史》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次活动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应征者多为教徒,应征稿多非小说,即使是小说,其内容与形式与传统小说并无差异,它对近代小说的发展并未产生什么影响,与后来的‘新小说’也无关联。《编年史》的附录部分也为读者提供了诸多研究线索与开拓空间。
陈先生毕十四年之功完成的《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其价值当然远不止此,它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近代小说研究者们案头的必备书,而陈先生严谨韧性的坚持、甘于寂寞的学术精神,也可给学界同人以启迪。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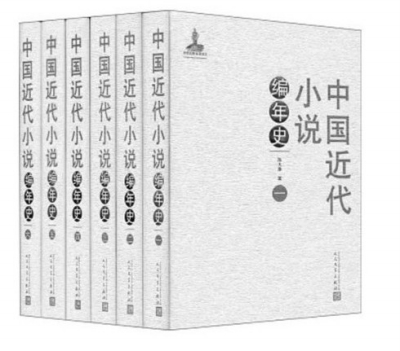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