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看闲书,始知1955年林徽因逝世时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是金岳霖与邓叔存联名题写的。我识见寡陋,只知金岳霖,不知邓为何人,与林徽因又是何种交情,写出如此充满情感、又无限遗憾的诗句。
幸好有网络,上网搜搜。庞杂的网络上,关于邓先生的信息也少得可怜。原来他是怀宁人,1892年出生在“四灵山水间”的白麟坂,叔存是其字,名以蛰。先生乃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的五世孙,“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在美学界,与宗白华被称为“南宗北邓”。按说,也算名人,何故知名度如此之低,不得答案。
浏览相关网页时,留意到安徽教育出版社在1998年曾出版过《邓以蛰全集》,但几家网店都无货。托朋友向出版社打听,说是前几年清理仓库,2000年前出的书基本都没了,而且这书只印了5000册。无奈,又上孔夫子旧书网和淘宝网搜寻,最终以58元,另加12元邮费的价格买得此书。灰黄的书套印着他旅行途中的照片,手拿一顶白色的帽子,帅气中带着微笑,似乎映衬着他的一生。前半生在东西方文化中行走,谈天说地论艺术。后半生却“默默无闻”,如黄裳所记载的“这是一位和善的老先生,沉默着没有多少话”。
作为美学家、哲学家的他,几乎被后世遗忘。甚至在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上他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此书寥寥35万字,远非先生著译的全部。“邓先生当年长期在清华大学以及中国大学讲授美学和美术史,一定也有大量讲稿、笔记及未发表的遗作。惟经十年浩劫,今已荡然无存。一座大厦倒塌了可以重建,这一损失却永远无法弥补了。”该书出版说明如是说。诚哉斯言。当然无法弥补的还有今人的遗忘,时间久了,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于书画艺术是个门外汉,对邓先生的美学观点无从说起,只能做敬仰状。由于这本书,开始在乱翻书中留心关于先生生活情状的小事。或许从这些片段中能从另一个角度感知其人。
宗璞在《三松堂断忆》中曾说,1926年,冯友兰与杨振声、邓以蜇,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酒。“新潮社”的著名小说家杨振声在上年出版了小说《玉君》,自序中说定稿前曾送请邓先生评阅。彼时,冯友兰31岁,邓以蜇34岁,杨振声36岁,都当正好年龄,才华大显之时。邓先生率真十分,豪情万丈。
金岳霖在《金岳霖回忆录》(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称其为“最雅的朋友邓叔存”。“邓叔存先生也是‘星(期)六碰头会’的参加者……谈话的内容,除每次开始时有一小段时候谈谈政治情况外,主要的是谈美术,有时邓先生还拿一两张山水画来。他不只是欣赏美术而已,而且是美术家。他的字可写得好,特别是篆体字;他也能画……叔存是我们朋友中最雅的。雅作为一个性质,有点像颜色一样,是很容易直接感受到的。”
先生素来敬重陈独秀的学识和人品,说“独秀是个质胜文的人”。1934年从欧洲考察归国的他不顾旅途劳顿,冒着濛濛秋雨赶到老虎桥监狱看望陈独秀,带来乡情、友谊和钱物。彼时的陈独秀可是国民政府和共产党都不待见的人物。“最难风雨故人来”,雨中探监使陈独秀感到极为欣慰。他们说着家乡话,回忆起在日本留学时的情形,两人脸上都露出灿烂的笑容。先生后来撰写了探望陈独秀的文章,以《癸酉行笥杂记》为总题目,刊登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
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先生因体弱多病,滞留北京,失去教职,生活陷入困难。但是八年来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的课,就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卖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时间又去卖,决不去上课,决不低头。一位过去的老朋友向他炫耀在伪政府取得了职位,先生勃然大怒,将其赶出家门。
先生去世后,金岳霖曾作一副挽联:霜露葭苍,宛在澄波千顷水;屋深月满,依稀薜荔百年人。不知何故,老金没有写出,更没有送出。挽联境界澄明,似有圆满之感,在霜露蒹葭的苍白之中,薜荔透出点点绿意,较真实地表现出先生一生正直真诚,谦和朴实、温和宁静和淡泊名利之性情。
回望邓以蛰,在唏嘘时,我们的遗忘速度是否太快了?存在不会因为遗忘而消失,但遗忘却是微弱的警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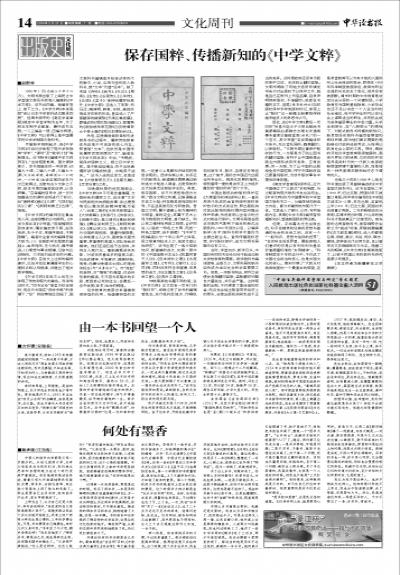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