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出版传媒,郑可和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张克文均有“少帅”之称。被冠以“少帅”美誉,不仅仅指两位社长风华正茂,更指张克文执掌安徽少儿社、郑可执掌安徽美术社期间交出的优异成绩。
去年三月,由安徽出版集团任命,郑可走马上任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在任一出版集团中,教育出版社的体量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任命郑可执掌教育社门户,时代出版传媒显然对郑可有更高期许。
尤其,现在显非教育出版社的黄金时代。诸多此前在一般图书领域、尤其在人文思想领域叱咤风云的教育社退出大众出版,正是缘于教育出版社在此一阶段承受的种种压力。此时接掌教育出版社,是荣誉,更是挑战。
关于教育出版面临的困境和出路,郑可已做了充分的考虑。关于安徽教育社的发展蓝图,也已在他心中徐徐展开。
教育社退守一般图书
从美术社到教育社整整一年时间,郑可考虑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教育出版社目前究竟面临怎样的竞争形势和压力。
行内人都清楚,国内出版社生存的根本是教育出版。“不管是美术社还是教育社,一般图书品牌都要依靠教育出版来支撑,完全靠一般图书走出来的凤毛麟角。”当然,教育出版的形式比较多样,教育社之外的出版社,比较直接的就是教辅出版。“品牌图书当然很重要,但出版社作为企业,现实的问题是,开门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钱。尤其是每年增长的任务都是硬梆梆的。”
可以看到的是,上世纪90年代,包括安徽教育出版社在内的一批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大批的人文社科精品图书,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口碑,但到最近10年,这些教育社都纷纷退守一般图书出版。其原因究竟为何?
郑可就任安徽教育社后的感受是,上世纪80、90年代,教辅市场竞争远没有如此激烈,各个省的教辅出版基本以教育社为主,这让大部分教育出版社都积累了一定的身家,愿意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精品图书出版中。但到了最近几年,随着教辅出版资质的放开,教育社原有的优势逐渐丧失。如安徽,不仅安徽教育社在出教辅,大学出版社、集团旗下的一些出版社都在出教辅。还包括不少省外的出版社,也在争夺安徽省内的教辅市场。
“教育社原来的地盘被别人占有了,很多教育社在本省的出版集团中,可能都已经很难维持龙头老大的位置了,那么,教育社更多的精力就放在了对教辅出版的维持上,收缩了对一般图书投放的精力。”郑可说。
其实,在很多的教育社,一般图书的比例是很少的。且出版单位企业化了之后,各社都要考虑每年实现10%或20%的增长,而教育社体量本来就已经很大,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已经有近6个亿码洋的规模,一年即使要实现10%的增长,也要增长5000万以上。“5000万,如果靠一般图书增长,是什么概念?基本不现实。”所以,近10年来,全国的教育出版社在一般图书都没有太大的作为。
“现在,包括我们在内,教育社的普遍想法是,每年能拿出一两套、三四套精品图书就可以了,不可能把一般图书作为一个最重要板块来经营。”而且,据郑可的观察,大多数教育社在一般图书板块的建设上也是模糊的,没有清晰的主攻方向。如科技社、少儿社,一般图书的方向和脉络就非常清晰。“安教社的一般图书板块叫学术文化,这个板块本来就很大,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有更细的模块?”
在郑可看来,教育出版社做一般书,理论上应该更多还是围绕大教育来做,如成人教育、教育理论等,甚至可包括育儿类的教育图书。目前,有教育社在出教育理论图书,但因为市场有限,所以很多教育社不愿投入太多精力,而且这类图书在评奖时也会受到局限。
无论如何,对于出版社的社长来说,一是注重经济效益,二是注重品牌。“教育出版社目前还有些利润,如果没有品牌图书,在读者中没有影响,在全国没有影响,并没有实现出版的根本目标。”
关于出版的理想,郑可一直有他坚定不移的认识,那就是,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追求,一定高于对利益的追求。“包括对出版企业的考核,我认为,应该把文化传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目前,出版企业的考核体系肯定是先考核方便考核的,如经济指标,每年能完成多少任务,一看财务报表就清楚。但出版企业的软实力应通过什么标准来考核,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出版社。
不仅郑可,很多出版人都有同样的困惑,那就是,怎样的衡量方式可体现图书的文化传承、创新价值?实际上,有些书可能没有获奖,却为出版社的品牌形象加分。
事实上,对出版社的考核,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最大困境还在未来三到四年
这么多年来,教育出版社的主战场就是教材教辅。而传统的教材教辅出版,日益受到国家政策的调控,如减负、教辅评议等,教育出版社的教辅出版空间由此受限。郑可以安徽为例:“安徽2012年秋实行教辅评议,而评议的教辅,可以不一定是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这里还有郑可的一个重要观
点,在他看来,现在还不是教育出版社最困难的阶段,教育社面临的最大困境在未来的三到四年,那就是——国家高考政策的变化。只要高考进行调整,我们的中小学教育都会变化。如果一般图书又跟不上,下一步,教育出版社将会面临更大挑战。
事实上,诸多教育社在寻找可能的发展的突破口,其中,教育培训是一个方向。
安徽教育社也在做教育培训的探索,并有专门机构在运营。但郑可感觉,教育出版社在教育培训领域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培训与传统出版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现在国内的教育培训,如果没有特别的理念,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就会陷入红海战役。
当然,大教育范畴,其中包括教育培训,都是教育出版社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趋势。关于教育综合业务,郑可的考虑是,应该在大众化的教育之上,根据家庭的需求,再给出个性化的教育方案。
郑可时时感受到关于教育出版转型升级的紧迫感:“我感觉,传统教育出版正在萎缩。”传统教育出版向什么方向转型?在郑可看来,对教育社而言,数字出版是最大的挑战。教材教辅全部数字化之后,教育社传统的教材教辅的市场就丢掉了。教育出版社面临数字出版的压力,比其他社更甚。而且,教材教辅数字化之后,印刷、造纸,包括发行业,全部都会受到波及,将对出版整体产业链造成毁灭性冲击。
无论如何,安徽教育社在为下一步的剧烈变革做好准备。郑可希望,国家关于电子书包标准的制定尽快明确。“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输入格式、输出格式,究竟什么样的制式才能适合使用,都要制定标准。不然哪一家公司都可以做电子书包,但是对接不了。”
安教蓝图
现在,郑可在业界倡吁“精品教辅”的概念。“做一本或者一套精品教材教辅,比做一套精品图书难度更大。因为教辅的打造,一要适合孩子的成长教育特点,二要适合我们国家的教育教学特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教辅当中能不能形成品牌、精品的概念?”当然,这里也有教育出版社的难言之隐。“教育出版社一年做这么多品种的教辅,最后评奖的时候,都和我们没关系。”
就任教育社后,郑可要求,编辑、编辑部主任,包括分管教辅的社领导,每年都要到学校里去上课。“不去上课,在家里编教辅,你怎么知道老师和孩子的要求?”在郑可看来,做一般图书需要做市场的调研,做教辅,就要深入到学校里去,紧跟教育形势和教育理念的变化,编出精品教辅来。而有了精品教辅、名教辅,教育社就拥有了自己的口碑。
紧接着,就是数字化转型,教育出版社必须先行一步。
目前,安徽教育社正在搭建教育运用服务平台,依托移动互联网开发教学客户端应用产品,包括微课、网络课堂、智能题库、数字图书馆等数字教学应用产品。下半年,这些产品会面向学校进行市场推广,但郑可坦承,“前期想盈利是不可能的”。
在郑可看来,教育出版社的核心还是为教育服务,为老师、学生提供教育的综合解决方案。在品牌建设上,郑可深知,安徽教育社走到今天30年,如果说还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主要靠一般图书建设,尤其是在重大图书的建设上。“比如《宗白华全集》《胡适全集》《李鸿章全集》,有了这些图书的接力,才形成安徽教育社现在的品牌。”由此,郑可所确定的一般图书战略是,不断推进,细水长流,形成文化品牌,形成大众对出版社的认知。他不讳言其中的难度,“精品图书的品牌与经济效益有时不成正比,这是让出版人困惑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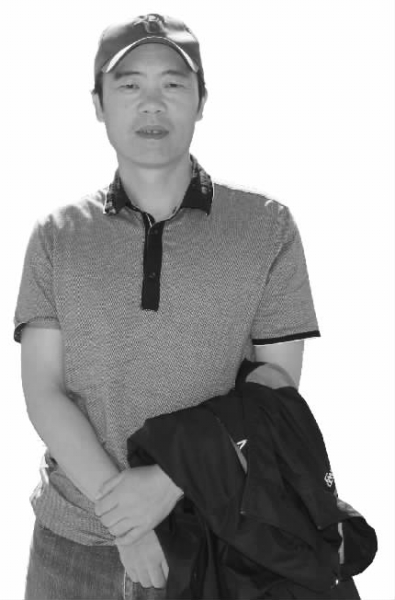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