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芦苇相识近十五年。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成不变的外表和取之不尽的电影智慧。
芦苇似乎永远穿一件圆领套头衫,一条宽松的绿军裤,一双圆口黑布懒汉鞋;他身材高大,鹅蛋型的脑袋上留着平头,稀稀拉拉的胡子茬好像从未刮干净过。从他的外表很难判断他的身份:他有庄稼汉的结实,但无农民的习气;像工人一样淳朴,却无体力劳动者常见的粗鲁;又不同于某些不修边幅的脑力劳动者,他衣着随意却不邋遢,既不吸烟也不喝酒,更无小市民打牌玩麻将的嗜好——他既属于又不属于这些芸芸众生。仿佛在某个时间点上,他已做出了身心的选择和穿着的取舍,之后再也不愿在这上面多花费任何心思了。在他的平凡中,流露着一种贵族的奢侈。
我是上世纪末在美国与他认识的。那时,他已是享誉国际的中国电影剧作家,由他编剧的电影《霸王别姬》和《活着》已分别获得1993年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次年该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我是坐在美国的电影院里看的这两部中国电影。与之前获得国际大奖的《黄土地》和《红高粱》等风格化的艺术片相比,中国电影仿佛在一夜之间具备了好莱坞大片的叙事功力——不但故事横跨数十年,而且人物命运与历史洪流交相辉映,气势堪比西方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日瓦戈医生》《教父》和《摩菲斯特》等史诗巨制。
令人吃惊的是,这两部影片的剧作竟同出自芦苇一人之手。
当时的我,正梦想着将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军》改编成电影。
那时,我正在学习好莱坞电影的编剧技巧。不难看出这两部影片所用叙事手法正是好莱坞的看家本领。之前,美国人看中国电影常常似懂非懂,片中的人性往往诡异凶残,情节每每不可理喻,只因其中的异国情调,他们才有猎奇的兴味。但对这两部电影,美国观众不因故事背景陌生而产生隔膜,反而与人物息息相通,并和中国观众一样看得如醉如痴。
芦苇这个生于1950年的中国人,一无专业学历,二无家庭背景,他是怎样掌握好莱坞电影叙事技巧的?
初见之下,芦苇让我想起西安的老邻居,还有在一个院里长大的兄长一辈人。相识之后,他便告诉我,他的启蒙读物原来正是美国电影编剧的入门书——悉德·菲尔德的《电影剧本写作基础》(Screenplay,作者Syd Field)。这本书我已反复阅读过,它不像中国传统语文教育那样强调玄而又玄却无可操作性的“悟性”,也不以“文章憎命达”的道德说教取代创作技法的讲授。作者像一位亲传手艺的师傅那样,心贴心、手把手,一招一式地教读者编剧技巧。
芦苇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阅读过这本书的中译本。他强调中国没有一本这种实用的剧作教程,而这是美国文化所特有的。芦苇没有将自己的创作经历神秘化,也没有将自己的编剧动机归为苦难经历,而是从技法谈起。他不故弄玄虚,这令我倍觉亲切。于是,我们聊起悉德——一位行家与初学者仿佛因发现同一个宗师而相识莫逆……
至今,也许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芦苇是好莱坞剧作技法在中国的真正传人。
其实,在他普通中国人的外表下,是一个早已深度西化的大脑……
他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通读过契诃夫的小说,在“文革”期间就接触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他在八十年代不但熟读过梅绍武翻译的纳博科夫,还通过爱伦堡的回忆录和《外国文艺》杂志发现过巴别尔——这两位作家都是在二十一世纪才广为中国读者所知的。2007年,我经他推荐才知道了巴巴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这竟是他过去三十年来的案头书,而至今,熟悉这位美国犹太女作家的中国人也并不多见。
相识十多年来,芦苇对外国文学经典与电影杰作的涉猎之广、钻研之深每每令我惊叹——在他的剧作中,可以看到契诃夫的悲悯、黑泽明的力度和贝托鲁奇的格局,他对文化冲突的敏感犹如大卫·里恩,他对区域文化的自觉堪比弗朗西斯·科波拉,他还原历史的追求则在向塔尔科夫斯基致敬……这些品质在《霸王别姬》和《活着》中已经尽显端倪,在他后来的十数部未被拍摄的剧作中更加饱满。
西方文化的角度仍不能完全解释芦苇。《霸王别姬》中的昆曲和京剧,《活着》中的皮影和老腔,又展示了另一个芦苇。除了昆曲和老腔,芦苇对所有中国地方戏曲和民歌都情有所钟。他毕生热爱齐白石水墨画中的乡土气息。
对乡土的迷恋与认同,使他自称为半个农民……他除了拥有一个西化的大脑外,还有一副醇正的中国心肠。
在与芦苇交往多年之后,更令我吃惊的是,芦苇这个外貌平常的中国人,却与他的同龄人大有不同。他堪称是一个将时代从自己身上洗刷掉的异类。
芦苇生于1950年,与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代中国人有共同的经历——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所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然后辍学参加“文革”,“上山下乡”,招工回城……又是所谓“吃过苦”的人。他们中很多人,尤其是其中的所谓佼佼者,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教主情结,他们跟所有人在所有方面比,过去比他强、现在比他强、今后比他强都不行。他们见了比自己年轻得多的人,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人家“没吃过苦”,一方面只有他受的苦算苦;另一方面,好像别人把他们受过的苦再受一遍才行。他们的思维方式仍属于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式的,即将简单的逻辑应用到社会生活中,正着说反着说永远有理……等等,他们都崇拜过毛泽东。
芦苇的剧作《霸王别姬》和《活着》所传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已与教主情结格格不入,也与八十年代流行过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迥然不同。
在生活里,芦苇是个会说“我不知道”的人。作为一名公认的优秀编剧,他却常说只懂正剧、悲剧,其他类型都不太懂。对新的题材,他总是从“我不知道”开始从头学起。可贵的是,芦苇不但上过山下过乡,还坐过牢,但从未说过谁“没吃过苦”。平等待人、宽容为怀,是芦苇本色。他不遗余力地发现和呵护新人,甚至在被他们出卖之后,对他们事业的支持仍不改初衷。
如果一个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没有自觉地清洗并重新锻造过自己的灵魂,是不可能这么不像自己同时代的人的。其实,芦苇不但是他同龄人中的一个异类,而且与比他年轻两代、三代的电影人相比,也仍然是个另类。
这才是他的电影能被全世界的观众接受的根本原因。
这也是他的价值所在。当我终于确认这一点后,我与芦苇的第一次谈话开始了。
2005年,我还在美国工作生活,我请芦苇以“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为引子,做了一次笔谈。2006年,这篇谈话在《天涯》杂志发表,名为“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长大”。这让很多人知道了芦苇,也使我发现了芦苇谈话的魅力与潜力。
2008年,我们在西安曲江编剧高级研究班上以对话形式所做的讲座引起学员的热烈反响,该讲座整理成文并以“电影编剧的秘密”为名在《读库0804》上发表后,不胫而走,不但使这一期杂志加印,而且至今仍在网上流传。2009年,“电影编剧的秘密(续)”又在《读库0901》发表了。这几次谈话之后,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专业媒体,仿佛发现了芦苇,对他的各类访谈接踵而至。从2007年至今,芦苇做了大量关于电影的谈话,他的电影观念已经广为人知,他尖锐而恳切的批评已成为电影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种声音。2013年6月,为补充前几次谈话及近年访谈之不足,我们就芦苇的成长经历,又进行了一次长谈。本书就是我们这四次谈话的结集。
芦苇是怎样掌握了好莱坞的电影编剧技巧的?更重要的是,他在什么时候做出了哪些取舍和选择,使他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其实,这是我们相知近十五年无数次谈话的结晶。这也是近年来罕见的,很可能是唯一一本由中国作家写的具有实用功能的写作指南,遥向我们共同的启蒙读物——悉德·菲尔德的《电影剧本写作基础》致意。但悉德本人并没有剧作传世,他讲的是普遍的编剧法则与剧作规定,而在本书中,芦苇对个人成长经历的追忆与电影编剧技巧的讲解融为一体,既有普适的原则又有实战的案例,还有血的教训。
这其实是我们两人编排的一出大戏,读之如闻其声,观之如见其人,主人公正是编剧芦苇本人,他一如既往地穿着那件圆领套头衫和那条宽松的绿军裤,像聊天那样一边回顾往事,一边品评电影,同时讲解编剧技巧。四篇谈话各自独立又奇妙地连成一个整体,有铺垫伏脉,有对位呼应,波澜起伏、高潮迭起,最后戛然而止,结构与谈话中讲述的正剧模式正相契合。这个主人公和善宽厚,循循善诱,又是直筒子脾气,爱憎分明,他会让你想起自己的兄长或父辈,你听得出来,他是自己人,一不说大道理,二不应付人,他娓娓道出的是那取之不竭的电影智慧。
如果你热爱电影,又曾萌发过写作剧本的冲动,但总有尚未入门的挫折感,那这本书会让你油然而生对创作的兴趣和信心。也许,你在阅读中还会产生独享秘笈的快感,甚至有一种被大师点拨的幸福——你会认识芦苇、认识电影。
(本文作者王天兵,摘自《电影编剧的秘密》,芦苇、王天兵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定价:39.8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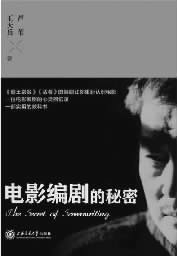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