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本报书评人)
湖南科技出版社2013年一次性推出由《科学的历程》(第三版)、《现代化之忧思》、《反思科学讲演录》、《科学走向传播》四种图书组成的“吴国盛科学人文系列”,这在中国科学文化出版史上是件非常特别的事情。这几部界面友好的学术著作,展示了吴国盛教授多年来对科学之历史、哲学、传播及其可能未来的诸多独特思考。虽然他本人以及部分学界同仁习惯性地把它们视为非学术著作或者普及性著作,但我要强调的是它们的确是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在我看来,学术与非学术出版物的区别主要不在于文字形式,而在于是否有思想,是否创造了新的拟子(meme)。形式是次要的,这个时代有太多形式上像学术的论文和专著而实际上名不副实。
一、一部畅销书的背后
《科学的历程》在出第三版时终于又返回到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我本人也见证了这样一部成功的科学通史著作不断重印、修订的过程。不过,如果忽略了背后的科学观、编史学理念,仅把它视为学术普及著作或科普书,那就会生发出一种假象,以为随便什么学者,只要愿意坐冷板凳,也能写出一部不错甚至畅销的科学通史来。在评判此书的价值时,我也并在乎其畅销与否以及得过什么奖项。另外,仅从这部书的大部分文字来理解作者的想法,也不很恰当。
私下里我曾说过,这部书在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非主流的科学史书写方式被作了主旋律缺省配置的理解,满足了并不符合作者原意的科学主义企盼。国盛在这部书中有意隐藏了自己的非科学主义科学观、科学史观,只有细心的读者才能感受到这一点。
《科学的历程》在第46章才透露出作者的真实用意:“在当代中国人的眼里,科学无疑是一盏神灯,它带给了人类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在两页之后接着说,“科学在带来福音的同时,也造就了危害人类的魔鬼。科学的未来如何,人类的未来如何,这是一个引起现代人深思的问题”(第736-739页)。就字面而论,这种表述也算不了很激进,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科技“双刃剑”、“副作用”之类含糊说法或者对此类说法表现出认知疲劳,但作者的确认同康芒纳的观点,“技术上支离分散的设计是它的科学根据的反映”,即不仅仅是应用环节出了问题,或者仅仅是技术部分出了问题,而是科学(即近代西方科学)在根子上存在缺陷。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信念或者判断与近代科学在知识体系扩张及力量展示上是否成功,要分开来考虑。说得更明确点,如默顿早已明确的,科技的价值不能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得以辩护。按功利主义论证,人们拥护科学是因为科学带来了好东西,那么按同样逻辑人们可以不拥护科学,因为科学也带来了坏东西。作者与普通人一样,都承认科技的效力,并且比多数人更能“欣赏”这类效力;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认可“有力即有理”的想当然理解。
《科学的历程》的特点绝不只是上述一点。“厚古薄今”的编史观念在全书中得以落实,对各时期各学科内容的取舍、提炼等,都显示出深厚的功力,虽然初版写作时国盛只有20多岁。那时候的阳光“少年”有一股挡不住的冲劲儿,做了一些老先生想做但做不了的事。虽然当时理论储备与阅读经验不足,但作者已经具备足够的反思能力,比如在那前后他已经写出了《自然本体化之误》(1993)、《科学思想史指南》(1994)和《时间的观念》(1996),足以表现当时的他已经超越科学观的缺省配置,对近现代西方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方法论有了深刻的体认。在那一段时间中,国盛对自然、时间和生态这三个关键词,做了独特分析,为后来的现象学技术哲学探究、绿色与科技伦理关注、新型科学传播设计、博物科学恢复与憧憬等学术链条的编织等等,布下了几个确立优势的重要棋子。那时,国盛年纪在30岁左右,悟性强,思想活跃。
设想一下,如果湖南科技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李永平先生在国盛年近半百之时(比如现在)才邀请他撰写这部通史,他会答应吗?会那么迅速地写成吗?人文学术通常是愈老愈辣,但不能等到头发白了、思想完全成熟了才开始著书立说。国盛被公认为科学元勘领域的才子,如今年轻学者可从其成才经历中得到若干启示,一是要有超前的学术视角、框架;二是要有胆量,要有舍我其谁的自信心;三要肯吃苦,毕竟“读懂书”与“作好文”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科学的历程》三版有三位重量级院士分别作序,每位都从自己的角度对此书进行了合理评论,不过我认为韩启德院士的第三版序更接近于国盛本人的想法。从韩先生关于医学人文的多次演讲中也能感受到吴韩观念的呼应。当然,《科学的历程》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样,写成后便具有多种不同的功能,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允许人们从不同角度解读。甚至,科学主义者也能从阅读中受益。实际上也大体如此,从反馈看科学主义者收获不小(有的加强了,有的减弱了,也许前者居多!)。
二、现代性之“时间机器”
这里提“时间机器”不是指科幻或赝科学中谈的回到过去的巧妙办法、装置,那类观念是一种可理解的幻想。不过,抽象时间在现代社会中的确变成了控制人类的无形机器。
《现代性之忧思》中最有特色的是对时间问题的思索。“突现时间性:20世纪的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和“普利高津时间与霍金时间”两文紧扣理论自然科学的进展,讨论了“科学之时”如何与生活世界“主观之时”的协调问题。国盛受现象学的影响,想必认为科学之时是导出性的、第二位的,而生活世界中人类主体感受到的不够精确的“主观之时”是第一位的。可是,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人不可能简单地抛弃来自自然科学的观念,特别是不能无视其严格性和有效性,而是期冀基础自然科学进一步完善,能够更好地照顾到主体感受。这一番用意无出“让科学不要遗忘其生活世界基础”的总体旨趣。近代物理学令时空观发生变革,但这离国盛的要求差距甚远;后来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中有一些进展,国盛满怀激情高度评价了普利高津“对时间的重新发现”,还借机调侃了一下霍金。
我在研究非线性科学的历史与哲学时也关注过普利高津的“内部时间”,当时也非常激动。细看后仍然很“不满意”,应当是“不满足”。普利高津说得多做得少、做成功的更少,他在推动数理科学关注不可逆性、复杂性方面倒是有功劳。普氏的“内部时间”概念非常有启发性,但是它只与外部的普适时间有平移变换等简单操作上的差别,根本性质是一样的,在动力系统分析层面针对其声称独特的时间哲学,普氏并没有贡献特别的“拟子”。
技术哲学是国盛用力较多的专业方向,对时间的思索自然会进入其技术哲学。在这方面国盛常能将技术哲学与科学文化写作无缝结合,造出独特拟子,说出不凡语句,给人以启发,比如“时间的客体化与世界的客体化同时进行”(《现代化之忧思》,第82页)。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最重要的机器是什么?国盛毫不犹豫地指出是“钟表”,钟表使其他一切机器成为可能。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这个看法还有效吗?依然有效。稍知道一点计算机运行原理的就明白,计算是依靠时种频率的。没有背后的时钟调节,计算不可能进行,建立在计算基础上的工程控制更加不可能。通常人们不思考这些,即使思考了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大问题。但国盛从中引出一个命题:现代人“不能闲着”。“技术时代的时间意识”一文机智而风趣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农民天然地依赖自然界的周期节律,而工业创造的各种工具设备和机械装置,形成了一个独立于自然界而运行的人工世界,在大都市里,在工厂里,人们就生活和工作在这个人工世界中。时间不再是自然律动的象征,而是机器单调重复动作的象征,而人就被绑缚在这个单调的动作之上。时间的暴政体现在,时间成了生活的指挥棒,时间成了最高的价值标准。”(同上,第85页)在现代世界中,活着似乎就是为了“忙”,忙工作忙生活,一直忙到死亡。“忙”的时候心在磨损,等心没了,就“亡”了。不忙,被认为不道德,时下百姓多放几天假,学者就站出来说经济损失几千个亿,变着法地游说政府减少假期,怎么就不想想百姓是多么希望稍稍休息一下!当正常的休假制度在中国无法实施的情况下,以各种形式多放假便是无奈的选择。通过这种不很正常的放假,下层百姓真正享受到了假期。黄金周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有比没有强,损失几个钱算什么?中国富得只剩下钱了。
国盛对时间暴政的思考仍然沿着现象学思路展开。现象学对于他本人,既是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之后的一个重要选项,也是解释诸多现实问题时要求助的一种有趣理论。在这种意义上,现象学提供一种看世界的态度,犹如当年的辩证法,起思想解放的作用,是超越现代性思想束缚的利器。
当人造自然不断扩大而成为与大自然相比拼的虚拟世界时,人这种动物把自己套在自己缝制的套子中。人书写所谓的自然律法同时让自己服从其条文。平常话语中提到的时间指“客观时间”(中性用法),它根本上来自科学和工业化。是人制造了它,而不是它如实地原初地呈现给人。只有当人走出人工世界、虚拟世界时,客观时间才能同步到感觉时间、主体(主观)时间。在这里“主观”并不意味着不好,相反它意味着更个体化、更靠谱、更自然。胡塞尔要求哲学家关注科学的建构过程,但并没有要求人接受、服从技术化带来的异化,后来的现象学以及其他若干学术思潮进一步明确这一点。了解现代化成立的条件和形成过程,并不等于认命,相反要求有批判的眼光,不断揭示暴政对人性、对自然施压的根源,并力所能及地开出药方。
“技术时代创造了那么多的工具、装置、器械,以减轻人的劳动,可是,为什么人类到现在不是轻松了,反而更加忙碌,更加不得清闲呢?这是技术时代人类的命运,时间意识和时间观念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揭示了这一可悲可叹的命运。”(同上,第87页)真的是注定的“命运”吗?如果真有“命”的话,人类个体尽量不要跟“命”过不去!实实情况可能是,“命”与“运”是相对的(只是一些方便的称谓),经过分析“运”实际上包含着“命”,有些“命”在另一层面、尺度看可能也不过是“运”而已。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识的现代性有相当多的问题,时间机器作为一种暴政控制着我们。这是命也是运,全看我们在多大的尺度上理解以及我们相信什么。当时间机器叫喊着“不能闲着”,我们偏偏要闲着、要忙里偷闲。要尽可能不把自己绕进去。有些人呼唤休闲,自己却比别人更忙、更折腾,这说明现代性的“场”太强大了,休闲的努力还缺少经验基础。时间内在于主体,技术助人挤占时间并消磨时光。我们不是想抛弃一切技术,而是选择适合自己的技术,更好地驾驭时间。时间岂能驾驭?我们自在地生活,时间内在于我们身体。
三、科学传播与博物科学
如果说《科学的历程》适当隐藏了作者的科学观的话,那么发表于1999年的文章“突现时间性”就讲得比较明确:“唯当科学的绝对普遍主义被抛弃,对其正统地位的反省、对非西方文化的科学(包括中国古代科学)的真正理解才会开始。20世纪末,环境问题变得引人注目。近(现)代科学也许不必对环境破坏负直接的责任,但它肯定是支持大规模生态破坏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之忧思》,第91页)国盛的这种科学观看似大逆不道并且荒唐,其实是可以从默顿批评的那种“功利主义论证”中直接推论出来的。科学家及普通人对科学的通常辩护是功利后果论,只要认可了这种论证模式,就可以推导出西方科学要为环境问题负责的基本结论。
如果承认这种科学观,接下去会怎样呢?能够推导出什么样的结论和操作建议呢?国盛充满忧患意识,并不完全悲观。通过科学史、科学哲学及现象学研究,他对科学界已发生的、不应当发生的、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系列说法。他认为科学有禁区,博物学传统仍然有复活的必要。早在1994年国盛就提出了自然科学两大传统(数理实验传统与博物学传统)的划分,并把它们与克服科学危机联系起来,后在在多篇文章中对此又有进一步阐述。两大传统的提法是一个重要创新,对我本人很有启发。
国盛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思考以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为支撑的界面友好的科学传播学科建设问题。这种“科学传播”与“科普”虽然有重叠部分,外表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理念是完全不同的。国盛有改造科普的野心,也确实感觉到中国社会需要破除科学主义的迷信,这既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科技创新的要求。公众应当在一种全新的平台上理解当今世界的科学技术与工程,而不是几十年不变地在唯科学主义的框架下让百姓被动地接受现成的知性结论。这样一种想法落到实处就有如下动作:(1)出版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丛书,后来出了5种,影响巨大。(2)成立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虚体单位,依托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培养研究生。(3)推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并举办系列研讨会。没有国盛的坚持,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做成的。
北京大学学者们所倡导的科学传播有这样几个特点:紧扣“民主社会中的科学”这个中心问题,主张非科学主义式的科学传播;考虑绿色观念,着眼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生存,同时关注一阶与二阶问题;区分狭义的西方科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体系,避免西方中心论;倡导在公众中恢复自然科学的博物学传统,主张博物类科学优先传播。国盛本人理解的科学传播有时包括更多的内容,他甚至设想用这个概念来重新整合“自然辩证法”覆盖的多个领域。能否覆盖得住可以再议,但是这种努力的确为自然辩证法开拓了新天地,在新的形势下至少为研究生就业指明了方向。国盛还有一个重要判断:科普主力队伍将由科学家的业余创作转变为大众传媒的职业科学传播。这代表了一种趋势,相应地国家的有关政策需要调整。这种转变不仅仅是身份、主体的转变,同时也必然伴随着观念的转变。如果科普主要由科学家或者“退役”科学家来操作,唯科学主义就很难不附体。
在国盛领导下北大开展的科学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在当下中国唯科学主义氛围下显然处于边缘地位。多年来,这些工作得以坚持,主流观念也不得不羞羞答答地采用相关表述。要头脑清晰地看到,这种新型的科学传播理念虽然是中国急需的,却是超前的。超前性是相对于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而言的,特别是相对于科学共同体长久以来未加反思的缺省配置而言的。传统观念的惯性不可低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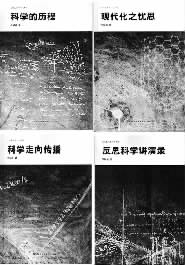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