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书这个名字在中国内地读者中不算耳熟能详,若对海外华文文学保持关注且不曾忽略马来西亚华文(下称马华)文学,大抵对这位今日马华文学极富代表性的女作家不陌生。去年,她的首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在内地出版,这部作品为黎紫书带来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专家推荐奖等奖项,更广大范围的华文读者,特别是内地读者认识她,看到她的实力,进而藉此接触马华文学。
最近在内地问世的《野菩萨》是黎紫书的短篇小说集,收入她2010年写完《告别的年代》之前之后几年的13篇作品。相较一部长篇,也许这些写作时间跨越十年,人物、故事、风格或有不同的短篇小说更能呈现她的文学轨迹。书中所收篇目排列,以《假如这是你说的老冯》为界,前面是更早些的作品,大多为若干文学奖获奖之作,后面则距今更近,体现她的写作近况。她在《野菩萨》“后记”中说这是她“目前为止最珍爱的短篇小说集”,这些近作是她历经此前的写作后“更有把握”的写作,“我不确定‘更有把握’是否意味着写出来的小说就能更成功或更有可读性,但我知道自己比以往更能享受写作过程中的自在和从容”。
在黎紫书身上,有些看似对立但不乏出处的矛盾。她的小说常予人以忧郁、孤独、回避之感,但面对读者,她显得开朗、健谈。前不久现身北京的她,对谈、讲座、媒体访问、读者互动,转战几个场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文学和写作,她既自信又谦卑,对自己的状态和此后的路向看得很清晰,觉得能写出更好的作品,但也强调作家在不断成长的这个现实,在某些层面,她依旧“战战兢兢,仿佛学生自知不才”。
读书报:《野菩萨》中这些短篇小说的叙事格调、文字氛围大多忧伤甚至阴郁,看上去你本人挺开朗的,你的文字和你这个人之间有多大反差?
黎紫书:我的写作和我个人没有冲突,我是个相当诚实的作家,很多时候我的写作是在出卖自己的经验、过往。当我想要做一个写作者,从来没想过以作者身份去面对读者的问题。我喜欢写作才想要当作家,最初选择做一名记者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锻炼文笔、搜集写作素材。后来,我把写作中的自己和真实的自己分开对待。
真实生活中,我确实比较“阴暗”(笑),一直比较孤僻。有一天我成为作家,才意识到需要面对读者,站出来和大家谈话。那时我几乎是用小说家的姿态来想象“黎紫书”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应该有怎么样的形象。今天我坐在这里,觉得是被自己设计出来的小说家形象。可能读者在小说中读到的“我”是那样的阴郁、消极,事实上,我在生活中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我不认为有这些想法就代表我是个悲观的人。我对人性的所谓不信任或者洞察,只会使我更珍惜现在所拥有的美好关系,可能比其他人更懂得珍惜变质之前的时间。相对而言,我有某种角度上的乐观,明知道人会变老,就在年轻时好好珍惜。
读书报:评论家王德威在《野菩萨》序言中评价,书中这些短篇小说代表了你最近十年的写作,但“这也代表了黎紫书与家乡的人事、历史对话方式的改变”,你认为这种改变是指什么?
黎紫书:作家在那么长的时间段里人生观和信念都会有所改变。不管年龄多大,我们总是在成长,在调整自己的姿态、想法。我最近在读韩少功的短篇小说集,书中的小说时间跨度很长。我会觉得,哦,他也曾经写过很生涩的作品,之后慢慢走向圆熟,笔调也有改变。我喜欢看到作家有这样的过程,相信这种过程是必然。过去十几年,我人生的变化很大,放下从事十多年的记者、传媒工作时完全不晓得以后的路要怎么走。我决定尽可能地多往外跑,去看世界看社会,专事写作。到目前为止,回头看这个决定,觉得自己选对了方向。人生历练上的转变必然会带来一些写作态度上的改变,我想,王德威指的应该是这些。
读书报:从《野菩萨》书中能看出来,你的写作往往无意针对宏大历史背景、文化寻根等等主题,更乐意将视角放在普通人的情感、内心世界上,这是否因为你比前辈马华作家少了一些历史的、精神上的包袱?
黎紫书:我并没有经历过他们那个年代,我整个成长过程的经验、环境,都没有那些东西。当记者的时候,我接触这些大命题是职业需求。我也会写下《国北边陲》这样谈论国族命运的作品,但那是环境的需要、参赛的需要。抛开这些因素,我真正关注的是人,是人生存的困境。那些家国、历史的主题,如果离开马华的历史、文化环境,让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读者去看,人家并不当回事。我会回想,到底马华这个历史包袱有多大?事实上它对我本人的生活经验、我的家庭,都没有什么影响,我为什么要在写作中强装着这个事情对我很重大?就回到自己的内心吧,问自己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读书报:这本书里写到人与人的关系总是疏离、无解,人终究还是孤独的,这反映了你的悲观吗?
黎紫书:孤独感是我的所有小说中撇不开的,不是我刻意要这么处理。我相信,不管你跟多少人在一起,跟别人有着怎样的关系,你终究还是一个个体,免不了有孤独感。我认为,我很难找到一个伴侣就能够解决我的孤独感问题。我小说中的人物显然是一批对孤独感比较敏锐的人,不能说他们都为孤独感所苦,但他们都是自觉自己处在这种孤独感当中。
读书报:你的作品有很强的女性特质,你怎么看性别角色对写作的影响?或者说,女性身份带给你的写作某种优势吗?
黎紫书:女性作家,像你说的,确有某种优势。这在于一种体察的细腻,尤其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不管是亲人之间、朋友之间、男女之间,我都能深深体会到。我常跟男性朋友混在一起,因为我觉得男性世界比较简单,相处起来比较轻松,可是我还是有属于女性的对人际之间的那种敏锐触觉。这种敏锐,在写作上来说,如果我有自己风格的话,那就是形成我的风格的重要因素。《告别的年代》也好,这本短篇集也好,我的写作都热衷于把细微的人性里的变化表现出来。
可是,小时候的经历又让我把自己当男性看,家里都是女生,姐姐很小就不在了,我就充当大女儿,像男性一样去处理事情,承担家里的需要。因为这层关系,我觉得我对男性的心理、男性世界的了解跟体会也比一般的女作家要多。我在写作时可以随意用男性角度去切入,以男性做第一人称的写作对我来说不是刻意的事情。我像是个中性的作家。
读书报:你的作品中,荒诞、超现实与日常、写实这两种特质都很突出,这是你写作的两极吗?
黎紫书:荒诞和写实的世界,还是同一个世界,可是你把不一样的人放进这个世界里,他们对这个世界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跟体会。我当过记者,知道现实中的荒谬要是写成小说都很难说服读者相信,可我还是尽可能地把打动过我的、让我觉得震撼的荒谬事情放进我的小说里。像《生活的全盘方式》,那就是完全真实的事情。我把这个素材写进小说,就会想要怎么处理才能写得像自然发生,让读者能够进入。我能够体会当事者的状态,把它写进小说是想要告诉我的读者,我了解这个人的困境。像《卢雅的意志世界》里,那个卢雅其实就是我自己。许多真实人生中的荒谬,不管你怎么去处理,都无法完全撇开那种荒谬性。在小说中,我就顺着处理它。每种素材都有最适合它的表现方法。
读书报:看过一个访谈,说你很懂得如何参加文学奖比赛,这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你的写作有成熟的职业性、计划性。
黎紫书:写作很难有计划性,特别是大的计划性。某天我想要写一篇小说,我的计划就是如何把这篇小说写好。你说我懂得参赛,这是小时候在学校考试时学会的策略。如果上学只是为了考试,不用上学也可以做到,只要你知道怎么去考试。我参加文学比赛,也是这个思维。如果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得奖,得奖才能被人发现和注意,那我就去发现到底要怎么写才会得奖,去看看历年得奖作品,看评审记录,就有了底。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挺成功。
读书报:在从事媒体工作的那些年,你是做哪类记者?这种职业经验对你后来写作有很大帮助吧?
黎紫书:大部分时间在做社会新闻,后来做专题记者,也做过时事评论的专栏作者,最后离职时是在做一个时事月刊的主编。与马华同辈作家相比,我最占优势的就是有过这一段当媒体的经验。我接触到的社会事件、人群层面和带给我的思考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搜集到的素材肯定也比别人多。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宝藏。
读书报:下一个长篇在酝酿中吗?
黎紫书:已经在计划了,它基本的结构和故事已经想好,应该在今年六月开始动笔。
我算是回到马来西亚一年多了,但还是会不断到处跑。我要写长篇的这段时间,会离开马来西亚,在老家,时间通常会被各种事务啊人际啊分割得非常碎。(本报记者 丁杨)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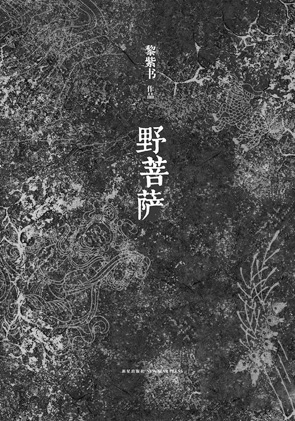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