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赵雅茹
■嘉宾: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 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雅茹: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它引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近年政治题材的焦点,影片《大而不倒》就围绕美国联邦政府与华尔街的共谋救市展开。美国现有的政治框架是否能解决越来越多新的经济、社会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否预示了某种新的可能?
戴锦华:《大而不倒》和《规则改变》的确有趣。《大而不倒》是根据畅销书改编的。本书号称,《纽约时报》的名记者访谈了五百多个人(包括所有的决策人物),写出了这本厚重的纪实报道。此书曾长时间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而后HBO将其改编为电视电影。
我们在《大而不倒》这部几乎具有新闻纪实性的电影中,看到了金融海啸的爆发,看到了美国政府、主要是联邦财政部的应激对策;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危急关头、力挽狂澜的新美国英雄——这是前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影片清晰呈现了这位新美国英雄的三重身份:一重是小布什政府的共和党部长;一重是他原本的身份——高盛投行的总裁;第三重身份颇为含蓄——一位恪守基督教科学派教义的信徒。三重身份清晰勾勒了一个共和党保守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取位。保尔森的三重身份也在不期然间曝露了美国政治中的最大的潜规则,即美国政府与美国大公司之间的二位一体。
影片中,保尔森扮演了一个规则改变者。准确地说,是规则的僭越者。他在危机关头近乎果决地僭越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绝非以“看不见的手”,而是极具力度的、可见的手,干预市场。他运用权力迫使各大公司违背对自身利益的判断、注资岌岌可危的投行;他施加压力逼迫政府“忽略”不得直接插手市场的原则及规定,划拨巨款给各大投行,令其“大到不会倒”。如果说共和党作为保守主义者,他们在理论上说应该是美国政治理念的恪守者和市场规律至上的捍卫者。但众所周知的是,共和党作为大企业、大财团的政治代表,其倾向大财团、无视规则救助大财团,无疑是逻辑的选择。影片中,保尔森之为新美国英雄,在于他迫使政府不是太迟地作出了救市的决定,令新自由主义经济造就的美国20年大牛市的巨型彩虹泡沫在破灭之时,不致引发生多米诺式雪崩,再度造成经济的大萧条。然而,也正是影片所呈现的保尔森救市过程,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所谓“美国政府注资大银行和大投行,被迫将金融业国有化,采取了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完全是幻觉或错觉。因为即使政府的投资份额已经达到了控股的程度,但其注资的前提正是政府不使用自己的股权、不介入公司事务的保证。这真可谓是“无私援助”。保尔森由此成了一个新保守主义的英雄。影片具有批判性、暴露性,同时成了对美国价值的重申。
然而,如果我们意欲通过电影获知巨浪起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和保尔森在其中的角色,《大而不倒》就不太够了。我们至少要参照相关文本才能一窥真相。比如说:鞭辟入里地呈现金融海啸的历史成因与现实状态的纪录片——《监守自盗》。其中你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尤其是金融政策如何造就了世纪之交的绝对“繁荣”,而且早已埋下了这颗定时核弹。你会看到官、商、学——不是相互勾结,而是高度相互内在。腐败,这个词在其中有了全新的却极为恰切的定义。在这里,保尔森的角色就相当不同又极为明确了:任高盛CEO之时,他正是令美国政府放宽(甚或放弃)监管的主要推手,他本人从中获得暴利——华尔街最“昂贵”的CEO;当他完全免税、悉数将高盛股份套现而变身为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之后,他对金融界已临悬崖的状态事实上全无作为。是他,拒绝英国银行要美国政府为雷曼兄弟公司担保的条件,并强迫其即刻执行破产,引爆了这颗核弹,其多米诺显影顿时波及全球,短短两年间直接造成3000万人失业,5000万人由此跌入贫困线之下。但继而保尔森以大大高于破产估价的天文价格救援AIG,其政府款项的大半却中转流入他昔日的雇主高盛公司的腰包。更为深刻的是,正是由于保尔森的“成功救市”,巨款注资大投行,令其前所未有之“大”,不仅“大到不会倒”,而且“大到不能碰”、“大到不可改”。于是,一切如故。
《监守自盗》中受访人的几句话,令我难忘:金融衍生品正是“大规模杀伤武器”;其销售是世纪未有的全球“传销诈骗”。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是“真正的工程师”的“4倍到100倍”;但“工程师造桥,金融师造梦,一旦这些美梦变成梦魇,自有别人埋单”。影片告知,这个“别人”,是美国的中下层,是全球的底层,是金融海啸余波所及,纷纷倒闭的中国沿海加工厂,更是因此而失业的几千万农民工。今天,我们,整个世界仍坐在这座金融泡沫的火山口上。等待其再度喷发?其中一个数字耐人寻味:世纪之交,仅金融业的用于竞选经费的政治捐赠就高达50亿美元。勿怪共和党的“英雄”里根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奇迹,大力助推的却是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这恐怕正是规则改变的内在动力之一吧。
王炎:我接着您提到的突破问题,谈一下对美国民主制的突破。电影《规则改变》开头便是主人公施密特与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通话,麦凯恩试探施密特是否适合做竞选班子的经理。麦凯恩是个老兵,笃信美国传统,有信念、重价值。但他被竞选班子摆布了,纵使班底出些馊主意,他也照单全收。比如选佩林做搭档,显然是幕僚的下策。片中有位忠实的助手,私下建议说:“如果你与佩林合作,失去的可能不仅是竞选,还要搭上一世英名。”麦凯恩答道:“如果我输了竞选,才身败名裂呢。”电影要说明的是,一位体面绅士原本不该为争一次总统宝座而丢了人格,而事主却用行动表明:如果失掉竞选,才叫人格丧尽呢。政治伦理败坏、世风日下,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主政治的精髓,其后果便是竞选规则与民主原则的改变。现实中的麦凯恩参议员,在2008年大选失败后,确实失去了人们的信任,阴影一直笼罩其政治生涯。
没有理念和精神支撑的民主制度,每人一票,政客为选票而作妥协,不再坚持己见,无论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在竞选中不断折中妥协。最后,两党意识形态虚化,甚至改弦更张,另立议题。其后果是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激进政治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中庸的民主选举。茶党在体制外,无顾忌地宣扬白人蓝领阶层最保守和反动的政治理念。“占领华尔街”则散布颠覆性的革命口号,剑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两种观点不可能在民主体制内得到表达,一旦说出便会被边缘化,被大多数的声音彻底淹没掉,所以草根运动是个突破。
但有意思的是,电视剧《新闻编辑室》却揭开个秘密:茶党真是草根运动吗?片中有两个茶党成员接受电视采访,他们自以为是纯粹“草根”,不依托任何党派或利益集团,大家为崇尚保守价值而聚在一起,形成无组织、无上下级关系的民间运动。但电视主播告诉他们:茶党背后有大财团支持,而且是比巴菲特还有实力的最大利益集团做后盾。这样两部片子便形成一种互文关系,《规则改变》预言政治规则将会改变,而《新闻编辑室》却似乎在说,任何改变都在利益集团的掌控之下。如何解读两个维度之间的张力?我刚看过一部2012年底的“新黑色”(neo-noir)影片《温柔杀戮》,主线是黑帮动作类型,但该片自始至终的画外音,却让人意识到此片的政治指涉。影片在情节发展过程中一直有车载收音机或酒吧间播放的电视节目做背景,画外传出小布什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表态、财政部长保尔森的救市讲话、奥巴马第一次当选时的就职演说等。故事前景是杀戮打斗,背景是政治人物演讲,前景与背景相互指涉。结尾处,职业杀手(布拉德·皮特扮演)向雇主索要赏金,背景是奥巴马庆祝竞选胜利。新总统向欢呼的人群说:“从今天起,不管我们曾持保守、自由或温和的立场,大家要捐弃前嫌。我们是一个国家、一国之民,上帝祝福美利坚合众国。”杀手对雇主说:“美国不是个国家,我们也非一国之民,美国是个生意场,少废话,付我钱!”全片戛然而止。一部冷峻的政治寓言片,它揭示出美丽的政治话语之下,赤裸裸的商业逻辑所统摄的政治现实。也许我们该转换角度,从全球化资本这个维度,去理解美国这个新型帝国的规则改变,而不只纠缠于政治观念。
戴锦华:不错,民主政治就是平均数,票高者胜,所以民主决议必须是妥协的结果。但问题不是平均数或多数,问题是平均数的基础和“谁”的“多数”。不用说,数量极为可观的非法移民当然与选举无关,他们不是公民,也可以说不算“人”,只能算“魍魉鬼魅”。即使在美国公民当中,选民的基本条件设置——守法纳税的年限、在本州稳定居住的年限等等,令许多“公民”也不具备投票资格。多说一句,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实现了所谓“数字化生存” 的国家,你的社会身份就系于一个数字:社会安全号。而维系其连续纪录的关键是其中的“永久通讯地址”。一旦你因金融海啸、失业而失去了住房,进而租不起房子的时候,三个月之后,你的纪录便中断了,你便事实上经历了某种社会性的死亡——不再是人或公民,而成了无家可归者或魍魉鬼魅。此外,我们说世纪之交的20年间,美国民主政治脱序、失效的表征之一,便是国民的政治冷感:注册参与投票的人数比例不断下降,最低时勉强达到人口百分之三十几。也是在这样的参照,“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是99%”才振聋发聩。现代世界的危机表象、“规则改变”的成因之一正是政治代表性的混乱和失效。
赵雅茹:我们知道媒体对于美国政治发挥着巨大作用,现在又有微博这类新媒体的介入,这些对美国政治有怎样的影响?
戴锦华:好问题啊。通过好莱坞电影、HBO的TV film来讨论美国政治的时候,我们多少有点“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我们会不假思索地使用“表现” 、“反映”这类的词去谈它们与美国社会、政治、公众心态的联系。其假定性的前提是媒介所扮演的角色只是“media”:中介、介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稍作追溯,便可以发现,战后欧美政治的内在改变,事实上与媒介时代的莅临密切相关。这无疑是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景观社会等命名的另一个时代面向。记得我少年时代读到的“内参书”之一——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几个细节,说明当电视成为两党选战的重要甚至是主要介质时,它整体地改变了政治家的角色意义和功能。政党理念、政治主张让位于甚至蜕变为形象营造与表演技巧。尼克松曾自述:他在一场电视辩论中因适时落泪而令支持率大增;但那眼泪不是动乎于中,而是成功运用了中学戏剧表演课上学到的技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美国的政治已经开始变成媒体政治了。从这时起,总统(/竞选)班底已不是此前的智囊或智库,而是形象营造“公司”。
我们上次说到,奥巴马的当选表明了美国社会政治对某种胶着状态的突破,是面对金融海啸成功启动的应激机制。我的确认为美国民主政治再度表现了它的活力。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事实本身的意义,正是在于形象——黑人形象的胜利,当然奥巴马本人颇具感染力和号召力。黑人、新移民候选人的当选,本身表现的是对新形象的需求。唯此,才可以告知美国公众,我们正在改变规则,我们已然启动了应激机制,一种全新的、可以拯救美国、带领大家安度危机的力量已经出现。尽管奥巴马的第一任期作为甚少,甚至如《监守自盗》所揭示的:“照方抓药”。可以说,不再是媒体“表现”现实,而是影像、再现本身成为了唯一的现实。现代政治在相当程度上被虚拟化。选战的内涵成了对媒体份额的争夺和媒体形象的比拼。
王炎:近年不少学术论文都在探讨新媒体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的作用。竞选的重头是资金,筹款是竞选活动的重要部分,各级竞选其实都带着铜臭味。传统筹款往往靠大财团赞助,大额捐赠以支票方式或银行汇款寄给竞选委员会。但如五块、十块的小额捐款,传统方式就有问题了。因特网的出现改变了竞选资金的构成,奥巴马吸引普通民众和年轻选民,他收到的捐款大部分由小额资金汇集而成,网上支付使小额捐款成为可能。奥巴马的当选,是新媒体改变竞选的好例证。奥巴马擅长利用Twitter、Facebook与选民一对一互动。这点老牌政客望尘莫及,他们不习惯零距离沟通,技术上也没那么娴熟。
当然最核心的还是形象,竞选辩论意义最大。2012年大选,总统候选人第一次电视辩论,奥巴马状态不佳,结果失分很多。罗姆尼此前处境低迷,很多资助人、大财团本已撤资,认为他获胜无望。但在这次辩论里,罗姆尼发挥超常,反败为胜,资助人又回来了,还招揽了不少新捐助,支持率大升。第二次辩论,奥巴马汲取教训,发挥正常,支持率又上升回来。至于辩论内容,公共政策、外交政策、政治理念之类,双方常相互交叉,甚至彼此易位,三次电视辩论矛盾百出。比如,罗姆尼在第一次辩论中攻击奥巴马与中国互通款曲,把市场份额、利润拱手转给中国人。第二次辩论时,奥巴马反攻罗姆尼旗下的企业与中国人交易,罗姆尼则辩护说,这个时代不与中国做生意就没法生存。选民不在乎观点前后矛盾,只关注现场表现。你说他们是选演员呢,还是国家元首?不管谁输谁赢,媒体最后都一样收个盆丰钵满;不管谁上谁下,美国照样会与中国做生意。皆利益驱动使然。你说是主义之争还是表演政治?
戴锦华:恐怕数码时代、新媒体是今天最具挑战性的文化议题之一。新媒体的突破点之一是移动通信。联系着选战(也可以是任何的实况转播,社会动员、行动或运动),你打开你的 iPhone、iPad或任何安卓手机,都可以通过Facebook、Twitter、微博或人人介入其中。如果说,当年电视令公共事务闯入了私领域,那么数码移动通信则取消或抹除了公私领域的区隔,抹去了距离与时间差。它令曾经存在的各种区隔,比如电影与电视在观影方式上的差异,不再具有本质性的规定意义。但是,必须注意到其双刃性的社会效果。一边,互联网构成了一个打开的民主实践的空间,在媒介特征的意义上,它令跨界的联合、异质性人群的相遇成为可能。然而,在另一边,它不仅可能,而且或许已然取消了人们直接交流的可能,进一步瘫痪了社会行动能力;同时有可能强化政治的虚拟化。
其次,我们前面说到媒体政治的特征之一,便是所谓选战成了形象之战,成了对媒体份额的争夺。而民主党或奥巴马的技高一筹之处,在于他们率先意识到新媒体的潜能。于是对新媒体的借重,令其事实上拥有了更大的媒体份额,因此胜出。
也是从这里,引申向第三点:当再现成了唯一现实,对媒体份额的争夺成了权力的演武场;不能占有任何媒体份额的人们,全世界的边缘人群、弱势群体,便真的成了今天世界的子虚乌有、魍魉鬼魅。不是“庶民无法言说”,而是他们的声音无从传播或被听到。于是,他们便成了拉康术语中的“实在界”,成为今日世界的某种不可见也不可触摸的“创伤性内核”。因此,后冷战时代的左翼社会运动的特征之一,便是必须寻找某种道具甚至是表演性元素,才可能消除其社会隐形,暂时获取某些媒体份额。反全球化的第一枪——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在不期然间,首创了一个成功的先例。起义者头戴的最初只是为了御寒的滑雪帽,后来却成了他们获得媒体关注和世界瞩目的标志:“蒙面军”——“我们蒙面才可能被看到”。这以后,有反WTO游行中的韩国农民身着纯白的民族服装,一步一跪;有台湾反贪腐的“红衫军”,十数万人构成一片红T恤的海洋;有“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全球抗议者戴着“V字仇杀队”的面具……。在精神分析中,被压抑的创伤性内核最终会以扰乱象征秩序的方式显露“实在界的面庞”;在社会现实中,遭隐形、被消声的人群同样会以报复性的形态骚扰“太平盛世”。就美国政治这个题目而言,茶党和占领运动便是政治倾向完全相反的、极端相遇的一例。
我想再提一下媒体或是景观政治的双刃性。我们说当年的尼克松、肯尼迪选战事实上是第一次电视媒体形象战。但是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激进社会运动也可以视为媒体效果。人们也把美国的反战运动和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描述为“B-52效应”和“切·格瓦拉效应”。第一次,欧美世界的年轻人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美军在越南用B-52轰炸机狂轰滥炸,看到美国的诸多暴行。人们也是在媒体上看到了切·格瓦拉的形象,看到了CIA支持的玻利维亚军方对切的杀害和陈尸。这一切导致了整个西欧、北美社会和青年的激进化。
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奥巴马对新媒体的借重。但与此同时,则是内部构成相当复杂的“阿拉伯之春”把新媒体作为被剥夺了媒体份额的人群相互连接、呼唤和动员的手段。启动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事实上是在“阿拉伯之春”中获得了灵感和启示。然而,我还是要说,新媒体、反叛者的“表演元素”是重要的,但并不充分。媒体的角色和功能取决于社会的整体状况、尤其是基层(所谓草根社会)的自我组织程度。
王炎:我想补充一下社会运动中的形象建构,“占领华尔街”运动很具表演性。我在华尔街边的祖科提公园里观看抗议者弹唱、表演,摆弄各种机器怪物、玩偶。没有对抗的运动不能称为运动,于是和平表演之后,还需上演“猛料”——与体制冲突、对抗,这是“全剧”的高潮。你能感受那狂欢般的激情涌动。与历史上的抗议不同在于大家知道被抓的人在警局转一圈就回家了,没有什么后果。
戴锦华:恐怕没有这么轻松吧。尽管后冷战的社会运动大都采取了某种“道具”或“表演元素”,但镇压却事实上正在“恢复”其残酷程度。我从美国知识界和媒体反应中了解到,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警察的残暴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没有出现过的。不仅是动用催泪弹、胡椒粉驱散和平示威的人群,而且是肢体冲突和殴打、伤害。我目击了一次加州大学学生抗议学费大幅上涨的小规模抗议,他们象征性地试图占领一座教学楼。示威学生近百,当局却调度了周边几个城市、几倍于示威学生人数的警察先行“占领”了整个校园。而我从加州大学声援学生抗议学费上涨运动的教授那里得知:每次运动后都有学生被立案传讯。类似的“案底”,对美国最大的负债人群之一——大学生,尤其是公立大学学生来说,是极为严重的威胁。没有清白的纪录,便无法在分外艰难的工作市场上立身,而没有工作、无法按时(毕业三个月后)还债,便意味着信用破产——那是另一个意义上的社会性死亡。而对外籍学生,则可能意味着无法继续获得签证以完成学业。
王炎:事情是多面向的,“占领华尔街”既有表演性的一面——其实整个后冷战时代的社会运动都有这一面向,它也有影响持续的一面。它的持续性不仅停留在社会影响维度,还构成对思想界的巨大冲击。我发现很多美国大学、研究机构,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个运动,有学术会议也以此为题。比方说,康奈尔大学人文研究所每年组织系列研讨某一专题,2013学年的主题就是“占领”。学者意识到,占领运动不是个孤立事件,如果说伦敦、巴黎暴乱过去也就过去了,但“占领华尔街”却让学术界、思想界和媒体渐渐深入下去。“占领”意味着什么?它不局限于运动本身的内容,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金融危机、世界动荡、资本主义危机,美国社会各方面深刻的矛盾——使这场运动的意义深远,这不是表演性所能涵盖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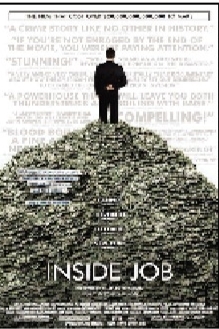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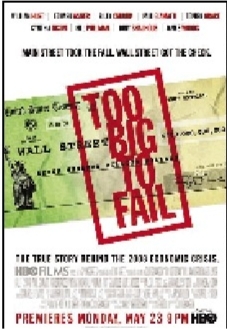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