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当下,中国学界关于“后殖民”研究的讨论已经持续二十多年了,在此次大讨论的后半期,相关学者在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历时性逻辑上也把“殖民”的问题带入进来,给予承上启下的思考与研究。客观地讲,国内学者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殖民”现象并不陌生,所以在此次大讨论的初始期,大家对“后殖民”这个概念的翻译与使用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然而我们注意到,很多的论文与著作在讨论“殖民”与“后殖民”这两种文学与文化现象时,往往没有对“殖民”、“后殖民”与“后—殖民”等相关概念给出学理上的明晰界定,而是混杂在一起使用,从而产生了研究中的误读与一厢情愿的过度诠释。
我认为,学界特别有必要对“殖民”、“后殖民”、“后—殖民”及相关概念的翻译与使用进行一次学理上的清理。
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学界注意的是,英语源语文本关于“殖民”、“后殖民”与“后—殖民”研究的讨论,至少有两个概念需要我们在翻译与使用中界分清楚,即“postcolonial”与“post-colonial”。准确地讲,“postcolonial”的汉语译入语应该是“后殖民”,而“post-colonial” 的汉语译入语应该是“后—殖民”。
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移居者的隐喻》一书的《引言》中,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对“postcolonial”与“post-colonial”这两个概念给出了重要的理论界分:“根据晚近的用法,后殖民(postcolonial)必须要与更为常见的带有连字符号(hyphenated)的概念后—殖民(post-colonial)加以区别,在这部著作中,后—殖民将作为一个分期概念以指称后—二战时代(the post-Second World War era)。当然,这两个概念不只是适用于英语世界,也不只是适用于文学。”值得提及的是,从90年代初以来,国内学界几乎没有学者就这两个概念的翻译与使用进行过严格的学理意义上的界分。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汉语学界,国内学者几乎没有人专门使用过“后—殖民”这个译入语概念,并以其专门指称“后—二战时代”的文化殖民现象。
准确地讲,中国学界热衷于讨论的冷战时期及之后的文化殖民现象,应该使用“后—殖民”这个概念予以界定,而不是“后殖民”。但学界完全是使用“后殖民”这个概念在误读中替换了“后—殖民”,以指称“后—二战时代”的文化殖民现象。
需要强调的是,在博埃默的这部著作中,齐努亚·阿切比(Chinua Achebe)与V. S.奈保尔(V. S. Naipaul)这两位作家,即是被严格地置放于博埃默所定义的“后—殖民”时期及其语境下进行讨论的;当然,作为尼日利亚伊博族小说家的齐努亚·阿切比与作为英国移民作家的V. S.奈保尔,他们两位在族裔身份、生存背景、文化观念、政治立场与创作手法等方面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又怎样理解与解释“后殖民文学”呢?在概念使用的学理逻辑上,博埃默在操用“后殖民文学”(postcolonial literature)这个概念时,则把这个概论的意义指向了对宗主国与殖民地双方所形成之张力关系的颠覆性批判。这里所言说的“张力关系”是指宗主国对殖民地进行侵略及殖民地对宗主国进行抵抗所构成的国际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而“后殖民文学”即是站在殖民地的抵抗立场上对这种张力关系的颠覆性批判。
在这部读本中,博埃默就“后殖民文学”这个概念曾给出过一个描述性定义:“后殖民文学通常被界定为批判地或颠覆性地考察殖民关系的书写,而不是简单地指涉帝国‘之后来到’的书写。殖民文学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陈述抵抗殖民主义者视域的书写。”从博埃默在他关于“后殖民文学”定义的逻辑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强调的对帝国时期宗主国与殖民地双方关系进行批判的张力性书写就是“后殖民文学”。因此,他进而陈述道:“另外一个问题是,后殖民的诸种界定趋向于认为这样一种书写即是直接地反对殖民文学。”
总纳博埃默上述所言,我们需要澄清的是,“后殖民文学”一定不包括国内学界一般理解的“后—二战时代抵制文化殖民现象的书写”,从这个逻辑推导的学理上来看,后殖民文学作家一定是坚定的反殖民主义者(anti-colonialist)。因此博埃默继而论述道:“后殖民作家为了表达他们被殖民的经历,在主题与形式上,对支持殖民的诸种话语——权力的神话、种族的等级划分与从属意象等追求釜底抽薪(undercut)。所以后殖民书写深深地标志着帝国下的文化排斥与文化分割。特别是在其早期阶段,后殖民书写也经常就是民族主义书写(nationalist writing)。正是建基于此,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种状态,即在逐渐全球化的世界中,被殖民的人民以强力或相反的方法寻求作为历史推动者的地位。”注意,这里的“后殖民书写”这一修辞性学术表达,指涉的就是“后殖民文学”,同样,“民族主义书写”指涉的即是“民族主义文学”。
在上述的表述中,博埃默对“后殖民”、“后殖民文学”、“后殖民性”与“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了描述性界定。平心而论,博埃默关于这四个概念的界定至少应该引起国内汉语语境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与文艺学研究等的学者的警示与思考。也就是说,“后殖民文学”是殖民地作家对外来宗主国的殖民侵略所进行的抵抗性书写,其当然在本土文化、本土资源及本土身份的维护中呈现为一种“民族主义文学”的姿态与立场。请注意,“民族主义文学”与“后殖民文学”这两个概念是包含和被包含的逻辑关系:“后殖民文学”作为一个小概念从属于“民族主义文学”;然而,我们又不能笼而统之地认为,作为大概念的“民族主义文学”都是“后殖民文学”。
我们特别建议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在操用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概念时,能够从汉语译入语概念追问到印欧源语概念所负载的意义上,准确地把握原创学者赋予这些概念的原初意义。并且,我们还要学会对相关同义概念的替换性使用,如在某种学理意义上,“后殖民文学”就是“民族主义文学”。同时,也要学会对相关反义概念的区别性使用,如“后殖民”一定不是“后—殖民”,否则大家就会陷于一眼看上去差不多的汉语译入语概念中不知所措,其结果就是把“后殖民”误读为“后—殖民”,或把“后殖民文学”与“后殖民主义文学”混为一谈。
在这里不妨把我们的思考逻辑再度深入下去。博埃默对“后殖民”给出自己的定义后,接着给出了关于“后—殖民”这个概念的定义。非常有趣的是,至少在博埃默的这部读本中,“postcolonial”与“post-colonial”是在历史发展的历时性(diachronic)上先后有序连接的两个不同概念,这两个不同概念连接的时间逻辑点是二战这一历史界标。也就是说,“后殖民”与“后—殖民”绝不是两个在同一历史时期可以相互替代与相互指称的概念。准确地讲,这两个概念不是在历史发展的共时性(synchronic)上有着共谋意义的同义概念。我们必须声称,“后殖民”不是“后—殖民”,以二战为历史界标,“后—殖民”是“后殖民”之后的另外一种反对文化侵略形态。从概念使用的修辞及理论的情感上来判断,“后殖民”是一个抵抗性术语,而“后—殖民”则必然不是一个抵抗性术语了。
而中国汉语学界在晚近20年来讨论“后—二战时代”的文化殖民现象时,可以说,所有的论文与著作几乎都是使用“后殖民”这个概念来完成自己的学术思考与表述的,几乎没有人在明确的学理意义上使用“后—殖民”这个译入语概念。让我们无法忘却的是,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及其对宗主国文化侵略进行批判的相关理论,在90年代初曾对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冲击与影响。赛义德在《东方学》中的思考曾启示了一批中国学者对张艺谋等第五代电影人进行批评,如有批评张艺谋、陈凯歌等的电影作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旧日风情贬损性地贩卖给西方受众猎奇等,以此掀起与推动了那个时代旷日持久的关于“后殖民”问题的文化讨论。现在看来,关于这场文化讨论的理论定位,似乎应该使用“后—殖民”这个概念,这样才更为准确。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并没有使用过“postcolonial”或“post-colonial”这两个概念。国内学者把西方相关概念及其理论翻译到汉语学界后,往往偏爱从汉语字面上提取意义,给予过度性诠释与扩大化使用。
我们不妨把自己阅读的视域投射到西方相关源语读本的命题与概念使用上,不难发现,西方学界有许多著作与论文都使用“post-colonial”这个概念来陈述自己的思想与命题。
陈述到这里,我们不妨再度回过头来阅读博埃默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移居者的隐喻》这部读本。这部读本主要是讨论大英帝国的殖民经济、殖民政治与殖民文化,同时,也讨论了相关殖民地非宗主国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抵抗的书写,即后殖民文学。严格地讲,这部读本与中国学者所理解的关于“后—二战时代”的西方国家对落后的国家、民族与区域进行文化侵略的“后—殖民”没有太大的逻辑关系。尽管在第五章,作者涉及了一些“后—二战时代”的“民族主义文学”问题,然而,作者也仅是讨论“非殖民化”时期“民族主义文学”对帝国进行批评的声音。非常有趣的是,无论是从英语字面上还是从汉语字面上,这部读本特别容易引起读者望文生义的误读,即被理解与解释为是在时间的先后序列上讨论“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的问题,而这部读本的主标题是《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也正是如此,90年代,当中国学界把理应冠于“后—殖民”这个概念的文化侵略问题,作为一个热点理论思潮来讨论时,这部读本也被不失时机地翻译到国内学界,替代了中国学者了解“后—殖民”问题的主流读本。我们无法不再三强调,“后殖民”不是“后—殖民”,如果说,“后殖民”是一个修辞性上的抵抗性术语,那么,“后—殖民”则是一个情感性上的侵略性术语。
不错,倘若说不同于“后—殖民文学”,“后殖民文学”是对“殖民文学”的抵抗性书写,那么,“殖民文学”的确切性定义又是什么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博埃默在其读本中的界定:“作为较为宽泛的概念,殖民文学(colonial literature)主要用于指涉关于殖民观念及其经验的书写,其作者主要是殖民时代来自于宗主国、西印度群岛或拉丁美洲之欧洲移民的后裔(creoles)与原住民。 因此,后殖民文学也许有争议地包括了殖民时期在英国和帝国其他区域所书写的文字,即使其没有直接地涉及殖民事务,然而宗主国书写——如狄更斯(Dickens)的小说或特若罗普(Trollope)的游记——参与了构成与强化英国作为一种支配世界之权力的观念。对使帝国主义看似合乎事理的方面,这些作家作出了方方面面的贡献。”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见出,博埃默及相关英国学者关于“殖民文学”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其中包括了宗主国作家、欧洲移民的后裔与殖民地原住民的书写,甚至还包括了狄更斯、特若罗普等作家的作品。概述而言,即只要他们的书写从方方面面以参与和推动的姿态涉及了殖民观念及其经验,就都可以被纳入到“殖民文学”的领地。
既然是如此,那么我们又怎样理解“殖民主义文学”(colonialist literature)呢?因为“殖民文学”与“殖民主义文学”这两个概念经常被国际学界与国内学界所操用,再让我们来看一下博埃默在其读本中关于“殖民主义文学”的界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殖民主义文学正相反,其特别是关涉殖民扩张的文学。总而言之,殖民主义文学是由殖民的欧洲人为了他们统治的非欧洲土地所书写的。其表达了帝国主义者的观点。”较之于“殖民文学”,“殖民主义文学”这个概念的外延更为狭窄,所以“殖民主义文学”的内涵更是集中且专门地指向殖民的欧洲作家的“帝国书写”。在这里,又凸现了一个概念——“帝国书写”。当然,众所周知,“殖民主义”(colonialism)是宗主国以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对弱势国家、民族与地区进行占领、奴役与剥削的侵略政策,所以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帝国书写”就是“殖民主义文学”,两者是同义概念。我们反复强调,一定要学会对两个以上的同义概念进行相互之间的替换性理解与解释。可以说,如同“后—殖民”这个概念一样,“殖民文学”、“殖民主义文学”与“帝国书写”,这三个概念在修辞的情感性上都是具有侵略性的术语。
当我们把上述若干概念在学理的逻辑上清理完毕后,我们需要设问的是,反思晚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学界在讨论与研究“东方学”、“东方主义”、“殖民”“后殖民”与“后—殖民”等问题时,在使用上述相关概念时,学界是否有着准确的译入语翻译与明晰的理论界定呢?学界又是在一种怎样混乱的概念使用中来操用这样一套术语呢?并且,学界又给出了怎样的误读性思考与过度性诠释的研究呢?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在她的著作《后—殖民批评家:访谈、策略与对话》(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的标题中就使用了“后—殖民批评家”这个概念。
的确,如果让我们浏览一下国内学界晚近二十多年来关于“殖民”与“后殖民”研究的文章与专著,在清理所使用的相关概念时,我们会遭遇一系列茫然不知所措的困惑:那么“postcolonialism”(后殖民主义)又是什么呢? “postcolonialist literature”(后殖民主义文学)又是什么呢?又怎样理解“postcolonialist criticism”(后殖民主义批评)呢?又怎样理解“postcolonialist theory”(后殖民主义理论)呢?这四个概念在学理意义上的价值陈述是指向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呢?也就是说,这四个概念在修辞上是侵略性术语,还是抵抗性术语呢?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设问,既然博埃默已经就“后—殖民”这个概念给出了一个严格的界定,那么,“后—殖民文学”(post-colonial literature)、“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与“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等概念是否还有可能成立呢?这三个概念在学理意义上的价值陈述又指向谁呢?其在修辞上是侵略性术语,还是抵抗性术语呢?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概念作为能指,而这个能指与其所指的逻辑关系是怎样合法化的问题。我们主张在理论上清理“后殖民”与“后—殖民”等相关概念,是极为重要的,否则,这些概念会成为文化研究中能指游戏玩家的把玩物,可能蜕变为滑动的能指而被链接到无数的所指上,在学理上呈现为无限放大的无意义术语。
较之于博埃默关于“后殖民文学”的定义,当下国内学界所操用的“后殖民批评”与“后殖民理论”这两个概念,其在学理意义上的价值陈述又应该指向那里呢?我们不妨翻阅一下国内相关的文章、著作,显然,晚近2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上述三个概念的使用,是把其价值陈述指向“后—二战时代”的文化殖民现象的。现在看来是不是误用了?
博埃默在其读本中就“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给出了严格的界定,那么“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这样一个概念又是否可以成立呢?这个概念一旦成立,其意义的价值陈述又指向何处呢?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学界在操用汉语译入语“后殖民性”时,恰恰是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
毫无疑问,在这些概念之间的确存在着学理意义上的细化区分,如仅就《维基百科》关于“postcolonial literature”(后殖民文学)与“post-colonial literature”(后—殖民文学)这两个概念也有着不同于博埃默的界定性表达。我们发现即便是西方学界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也存在着相当的逻辑混乱。即便是博埃默在其读本中就上述多个概念所给出的界定,也是需要我们存疑的。
诚恳地讲,我90年代时也多少参加过关于应该被称之为“后—殖民”问题的大讨论,当时,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后来,我在扩展性的阅读及相关博士论文与博士后论文的指导与评阅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混乱性与重要性。因此,我特别建议现下正在作类似相关课题研究的青年学者,能够关注这一国际学案,并在自己的课题与学位论文研究中对上述若干概念的使用予以逻辑上的清理与界定,给学界一个准确且明晰的学理性总结。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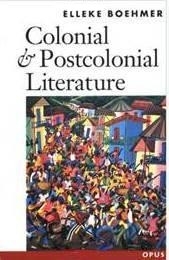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