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经济发展蹭蹭蹭,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观念倒了一个个儿:同一种活动,过去叫“投机倒把”,现在叫“市场经济”。过去曾经对着那件皇帝的新衣啧啧赞叹,现在一觉醒来,民众突然不干了——你害臊不害臊,怎么什么都不穿?
素什么质
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里,有一个就是“素质”。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么呢?译成“quality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他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么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 2009年研究显示,中国18.3%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么也不算很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着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里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候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锒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锒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某政府官员飞机上打乘务员。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么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的是源于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像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如何如何”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如何如何”。
敲开最好的可能
在我剑桥的家里,几乎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不过前两个星期收到的一封邮件,却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X月X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领取,并捐给XX机构转卖……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十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可以说是密密麻麻。就我家附近一公里左右,我就见到过十来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 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保护流浪猫的Cats 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 of Romsey 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去统计那些我没有路过过或者注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乍一到剑桥时我还奇怪为什么这个小镇怎么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慢慢地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人叫卖“Big Issue”的声音,所有熟悉剑桥的人恐怕都习以为常了——Big Issue是专门雇佣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必须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提高。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则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200万—800万);此外, “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百分之九十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筹款工作开展困难,也使得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也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入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天然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在广场上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10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
我读中国历史很少。最主要当然是因为懒,但隐隐一直还有一层原因。中国史的写法——无论是古代的正史,还是当下的戏说——大多都充斥着那种“皇上听了奸臣的谗言,杀害了忠臣,然后王朝就垮了”的“忠奸”历史观。我不相信历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我觉得“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罕见“个体权利”的位置。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隐隐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就像如果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读国史,部分是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但读刀尔登的文字,我却没有戒备之心。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与网上很多资深的“三七”粉丝不同(刀尔登原来的网名叫“三七二十八”),我并不知道刀尔登在网上早已享有盛名,更不知道他象征着某种隐秘的阅读品味。我孤陋寡闻,得知刀尔登才一年左右,还是蹲在厕所里读《新世纪》的专栏偶尔撞上的,撞上了之后立刻决定不上厕所了,开始搜寻他更多的作品。
在我眼里,学历史的人,专业学者也好,发烧友也好,学“进去”的多,学“出来”的少,刀尔登却是少有的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学进去的人多半喜爱钻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热衷于和其他学进去的人PK谁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细致,郑和下西洋的船舰到底长宽多少米,《吕氏春秋》里第十行第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古代诗人使用过“自由”这个字眼……学历史学到那个份上当然不易,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知识少得可怜的人,读这样的历史基本上和围观杂技表演没什么区别,看的就是个惊险。不过,技术精湛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要说那样的杂技表演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乃至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处,好像也说不上来。而刀尔登却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集体与个体关系,道德与制度关系。讲东林党之痛恨阮大铖,刀尔登说中国历史上这种长盛不衰的“捉坏蛋运动”,原因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象力的儒士们要为政治失败寻找替罪羊。讲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读者,“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若大旱之望云霓’;一个是列队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到皇朝延绵不绝的统治基础,他指向东汉以来地主阶层的儒化,“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讲传统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残暴程度相比,“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讲知识分子们的亡国之恨,又说“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在我这个无可救药的个人本位主义者看来,才不至于读坏了肠胃。
当然刀尔登的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优美的文字有音乐感,刀尔登的文字就有难得的音乐感:有节奏,不徐不疾,完全没有时下,“愤青”的燥热感,更没有当今文人们纷纷引以为豪的市井气,好像他所置身的环境对他的文风与思维方式毫无影响,似乎他不是“红旗下的蛋”。前一段刀尔登刚出一本又古怪又雅致的小说,叫《七日谈》。读完之后,我觉得这书完全不像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写的,倒像是一个活了一千年又在沙漠里修行了一千年的老头突然开口说了话。大约历史读多了,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当下。“此时此地”对于他,无非是游荡于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暂时寄存自己的柜台而已。
据说刀尔登当年北大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石家庄。在石家庄工作数年后,又放弃了体制和单位。现在虽然以写文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说他是“隐士”,我却不觉得他有要成为一个“隐士”的刻意,也没有“隐士”们那种自我陶醉的表情,无非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活着而已。一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种能力很让我妒忌,但我同时也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大约只有“合理地生活”的人才能写出这么从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让我这样的读者愉快,那种走在一个初夏的黄昏微风迎面吹来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
(本文摘自《观念的水位》,刘瑜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定价:36.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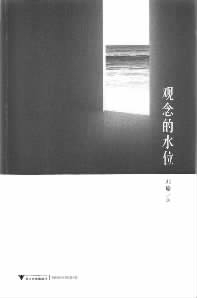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