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21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诗人、书法大师赵朴初先生与世长辞。朴老在住院期间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
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从最后一句“不劳寻觅”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朴老低调的心态。但是我今天依然要写一些文字,沿着朴老佛学思想(《佛教常识答问》)的足迹,来纪念朴老。
一、佛教是文化
赵朴初先生是现代中国佛教的宣讲者、传播者和光大者。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血脉相连,要懂中国文化不能不关注佛教思想,更不能轻视和放弃它。假如中国文化的传承缺少了佛教,是不够的、不丰满的。梁启超说,“若成大学者,无有不治佛的。”(参阅《佛经翻译与佛典》)《佛教常识答问》的序言中还记载着范文澜的补课(“补佛教这一课”),说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所以,佛教并非无知者所想的和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
“宗教是文化”,赵朴初先生在《答问》中借钱学森先生的话如是说。此话不假。为什么这样说呢?考察佛教的思想,处处体现着大智慧。大乘重“利他”(利益大众的行为),小乘重“自己”的解脱。佛主要教人断除内心的烦恼,以求解脱,对现实生活抱容忍态度。佛教对生死也体现了大度、智慧。“生死”是所有哲学及宗教都面临的问题,而佛家对生死体现出来的是安详自若。因为生的欲望,使人生在世走向沉沦;对死的畏惧,又使人生在世走向澄明。人,就在这生与死、有与无之间。
朴老就是一个大智慧的人,或者说是佛。朴老的一生,渡过诸多劫难(参考朱洪《赵朴初传》)。所以,朴老这位集佛学大智慧思想于一身的化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化史。
佛教就是这样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出污泥而不染”、“花开莲现、花落莲成”的清静文化,最适合凡夫俗子在铜臭的浊世除躁、去翳,是绝好的“心灵鸡汤”。
二、《佛教常识答问》
《佛教常识答问》篇幅不长,只有八万字,但言简意赅,高屋建瓴,凝聚了朴老六七十年来对佛教的理解和新见,以及他参与佛教活动的切身体会。据朱洪《赵朴初传》记载,“该书1983年第一版,后印过两个版本,其中一个为内部流通版,九次印刷,总印数达二十万余册。近年还被译成日、韩、英等文种,影响很大。”《答问》的汉英对照本于2001年9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英译者为赵桐,2012年又收入《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重新修订出版。
1998年6月,朴老在《答问》新版序言中写道:“我喜欢小题大做,而不喜欢大题小作,更害怕无题空作。”这体现了朴老实事求是、小处着手的精神。《佛教常识答问》语言活泼易懂,读后顿觉高深莫测的佛学问题,在朴老的讲述中豁然开朗。因此,该书译者在前言中说:“这透露出一位大家的睿智,一位善知识的亲切,一位学者治学的严肃与公允的态度,以及一位真正的佛教徒对佛教正信的立场,因而与一切迷信、假信和伪信划清了界限。”
《答问》全面系统、通俗易懂。这样说原因有二:其一,佛教两千五百年来龙去脉的大部分问题在《答问》中均已涉及,一般人若想了解佛教,读了此书不至于走偏,这便是译者在前言中所说的“正确的导入作用”的意思。而且读此书可对佛教的创立,佛法的基本内容,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衰灭和复兴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有详尽深刻的了解。其二,对于想了解中国佛教的外国人,读此书可览知其全貌。另外,《答问》的英译更加有助于它的对外宣传。据笔者了解,西藏大学及国内一些佛学院都把《答问》汉英对照版当作教材在学习,足见此书及其英译的影响之大。
三、英译述评
笔者是学翻译的,最能体会翻译之苦。一个译者要想拿出真正好的译作,所下的功夫有时也许会数倍于原作的创作。写于公元224年的支谦《法句经序》就记载了“翻译之难”,可见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先河一开始就是从探讨“翻译之难”开始的。
那么,本书的翻译之“难”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是专业知识的翻译。由于《答问》是赵朴初先生一生对佛学进行研究的总结之作,所以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佛学的专业知识。全书五章共计251个答问,分别阐述了佛教的创立,佛法的基本内容,僧团的建立、僧侣的生活、戒律与仪轨,印度佛教的发展、衰灭和复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这样高度浓缩的专业作品,对译者翻译能力要求之高是可想而知的。
本书的译者——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副教授赵桐老师,1981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在斯里兰卡获得佛学硕士学位,精通中文、英文、巴利文和梵文。即便如此,她译此书仍然历时三载,从1996年开始翻译,到1999年底才全部译出。正如赵桐老师在《译者前言》中所说的,“这是对译者佛学知识、中文修养,尤其是外语水平的全面挑战。”此乃实话实说。赵桐老师在翻译时所使用的英语是最通俗易懂的英文,这无形中又加入了一层“深入浅出”的难度。
如第三章《僧伽和佛的弟子》第五问:“‘出家的制度是佛教创始的吗?’答:出家制度不是佛教创始的。在佛陀时代,出家修道在印度已成为风气,但是佛陀本人以王子出家的榜样,使出家风气在佛教中得到了鼓励。因此佛教徒中便有出家男女二众和在家男女二众。出家佛教徒一般称为僧人或僧侣。”朴老将一个我们熟知的但又不清楚渊源的问题用寥寥数语解答得清清楚楚。再看英译:“Q: Was the institution of renunciation initiated by Buddhism? A: No, it was not initiated by Buddhism. By the time of the Buddha, religious mendicancy (paribbājaka) had become common practice in India. But as a prince, Buddha’s renunciation set an example to inspire his followers to discard the attachment to home life. Therefore, there are those who renounce home life and become itinerant or monastic disciples, both male and female, as well as lay followers, both male and female among Buddhists. The itinerant or monastic Buddhists are generally called Buddhist monks or nuns (Bhikkhus and Bhikkhunīs).”源语文字涉及“出家制度”的历史,专业知识高度浓缩,非熟知这一制度之人而不能译。但读完赵桐老师的译文,清晰明了如原文。
另外,佛教术语(佛教中称为“名相”)是翻译中的难中之难。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踯躇”之论,可谓译事中对翻译术语之“难”的写照。对源语术语的翻译,在译入语中有创造“新术语”的功能。如在中国规模最大的翻译活动——从汉至宋持续千年的佛经翻译中,“法界”、“无明”、“众生”、“因缘”、“涅槃”、“瑜伽”、“刹那”,都是在翻译佛教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据梁启超统计,新术语有三万五千个。“夫语也者所以表达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
但对于赵桐老师而言,翻译工作恰恰是逆向的,即将佛教的中文术语移译至英文,其做法自然不同。赵老师的做法是:“对于绝大多数佛教术语,尽量找出它们的巴利语原词以及被接受的英文译法。”这一做法虽然减少了“创造新语”的工作,但查找巴利语原词和英文对应词的工作却大大增加了。此外,书后所附的《巴、英、汉佛教术语对照表》,似乎是译者三载翻译工作的副产品,但其中所费心血却不一定比翻译原文简单。《对照表》三位一体,一目了然,大大减轻了我们在浩如烟海的佛学资料中搜寻佛家术语的痛苦。
第二,是翻译中的灵活处理。翻译的最高境界莫过于钱锺书先生倡导的“化境”,即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也就是译文与原文有同样的感受,达尽善尽美的境界。罗新璋《翻译论集》有言:“传神云云,本谈何容易;入于化境,当然更难企及。”所以,钱钟书说:“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译者赵桐老师固然知道这是一个悬设的“标准”,难于企及,但她也不愿意“退而求其次”,所以她把翻译当作“学佛的过程”,“在真正搞清楚之后,才能表达”,这就需要“理清思路,领会作者的意趣之后再遣词运笔”,“故而历时三载,数易其稿,方成现在这个样子”。在绝大多数情况遵循原文的情况下,译文也有“变通”,旨在将原文的内容表达得更为清晰。因为《答问》的英译主要是为外国人了解中国佛教的全貌提供全方位的素材。变通处如下:
1.意义增补。就是为了把译语意思说清楚而增加必要的信息。如朴老讲到“如来”,“如”即“真如”,即一切法(事物)的真实状况。译文为了把“真如”说清楚,加入“or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再如,第17个答问中讲到“转法轮”,原文为“轮”(Cakka),先说“轮”,后附括号加入巴利语,译文为“Cakka (wheel)”,这就将朴老的巴利语加注换成原文,而把英文的“wheel”换成加注,译文更加清晰。
2.省译。如第20个答问讲到“归、皈”的区别,因为无法对应英文,所以只好略去不译。再如第42个答问,朴老讲到“现世止恶行善的因,会获得来世安乐的果”,译文为“desisting from evil and doing wholesome deeds in the present world would bring happiness to future life as effect”。译文省去“因”,而将“因”的意义“化”在行文中,而通过“as effect”使得这一意义得到彰显。
3.转换。词性的转换在译文中比比皆是。这里谈的转换是译者对原文的顺序进行变化,对信息进行重组,以使译文更流畅。如第14个答问中,朴老讲到悉达多王子成佛及成佛后的情况,译文对这一段就进行了顺序调换、信息重组。再如第23个答问,“现在暂不详细解答”,英文采取了反说正译的方法,译成“This will be fully explained later”,更加符合英译表达习惯。又如,第33个答问,讲到种姓制度,朴老行文过程中用“最高的、其次、其次、最下的”,英译则转换为The highest caste,the next,the third,the fourth,这是考虑到英文在语篇的构建上更注重逻辑顺序的转换。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赵桐老师的英译,为朴老一生的结晶——《佛教常识答问》——的对外宣传增色不少。当赵桐老师译完《答问》并写出《译者前言》拿给朴老过目时,朴老在听完陈邦织先生的朗读后,给予赵老师的评语是“Good English”,虽然简单,但表达了朴老对其英译的肯定。
德国学者本雅明给予译作以原作来生(afterlife)的崇高地位,原作由于译作而重生。在译文中,原作的生命得到了完美的展开,并由此在译文中得以升华。译者的任务就是要表达译语的意图,让译作与原作产生共鸣,成互文之势。同为德国学者的罗森茨威格更近一步说:“每一次翻译《圣经》都是弥赛亚的拯救行为,使救赎越来越近(Every translation of Bible is a messianic act, which brings redemption nearer)。”基督教经典的翻译是神圣的,佛教经典翻译的道理亦然。在这个意义上,赵朴初先生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那豁达的笑容以及借《答问》所传达出的深邃的佛教思想,而赵桐老师生花妙笔般的英译又让朴老的原作找到了“来生”。用本雅明的话来说就是:“译文中,语言间的和谐是那么完美,以至语言触及意义就像是清风拨弄琴弦。”英译使朴老的思想传遍世界。我想,这就是朴老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而翻译,尤其是宗教经典的翻译,依然神圣。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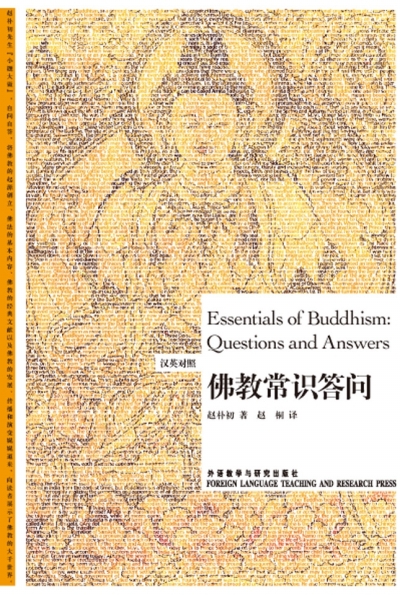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