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世纪巨富、纺织大王张松樵的儿子,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期间,著名作家邓贤的父亲有太多机会到国外留学或者明哲保身,但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儿子他却不听家人劝阻,执意报名参军,到滇缅战场前线杀敌。前不久,邓贤以自己的家族和父亲为原型,创作了长篇传记小说《父亲的一九四二》,讲述了这段感人的故事。哪怕父亲胸前没有勋章,甚至因此在战后遭遇到不公正的对待,也给子女带来很多磨难,但在邓贤看来,父辈的故事不应该被历史遗忘,自己几乎全部的写作也是在为他们“颁发”他们应得的勋章。日前,记者采访了邓贤,请他讲述了书里书外的故事。
——编 者
读书报:在《父亲的一九四二》之前,你曾创作《大国之魂》等多部抗战题材的作品,对你自己而言,此次的写作与以往有何不同?
邓贤:我从前的抗战史写作,像《大国之魂》、《落日》、《黄河殇》、《帝国震撼》、《同一面战旗下——二战中国老兵回忆录》等等,更多以发掘、还原、重现和深入剖析历史为目的,将一些不为人知或者被人为遮蔽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历史过程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真实地呈现出来。
而《父亲的一九四二》不同于以往。其一,与其说我在写一段抗战史,不如说我着力于刻画一群生于战乱中的年轻知识分子,着力写出他们人生经历和命运的巨大变化和落差,而他们的人生道路折射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史。 其二,家族史的写作使我更加贴近历史的血脉,使我对历史的认知和情感落实到父亲和与父亲有着同样经历的父辈们身上,而这些老人,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倾听着他们的声音,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这样我就渐渐走进了他们的世界,走进了更加具象的历史过程中。
读书报:你的家庭出身曾给你带来很多不幸和麻烦,你对家族和父亲的认识,有着怎样一个变化过程?
邓贤:我从小一直背着“黑五类”、“狗崽子”的家庭包袱。别人告诉我,我的爷爷是剥削阶级,父亲当过国民党兵。总之我生于这样一个家庭,无论怎样努力,当兵、上学甚至打乒乓球进专业队都与我无缘。我至今仍记得中学时代被赶出乒乓球队,那时领导与我谈话,义正词严地要求我与家庭“划清界限”。当然无论怎样划清界限也没用,我还是被赶出乒乓球队下乡去当知青。知青年代我很努力地劳动,希望用汗水改变人生,但还是没用,1973年上级党委给我做了结论,就是像我这样家庭出生的人永远不能保送上大学,等于宣判死刑。直到1977年高考改革,我才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离开边疆农场。
1987年,我从云南大学调回成都前夕,因创作假途经怒江大峡谷西岸的松山,偶然听说这里曾经是抗战遗址,当年中国远征军在这里与日寇血战,“伤亡逾万,血流成河”。我这才恍然记起,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就是因为他在学生时代曾经参加中国远征军,难道他老人家当年也在这里打过仗?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留下来,独自登上松山采访。在这里,当年的战争遗迹仍历历在目,山头被炮弹削去了三米高,战壕壁上的血迹已在岁月的河流中变成了黑色,然而剥下表面的泥土仍是一片触目的鲜红。我匍匐在这片土地上泪流满面。父亲光荣而神圣的抗战历史,父亲可歌可泣的战争经历竟然连他的儿子都一无所知,儿子甚至曾对他老人家产生埋怨,这不是不肖子孙是什么?同父亲这一代人经受的战争苦难和付出的鲜血乃至生命代价相比,我所经受的那点个人委屈算什么?简直微不足道。从这天起,我开始走进中国抗战的历史之门,三年后我写出《大国之魂》。
读书报:你父亲口述这一段历史的《重庆参军第一人》讲的很简单。除了他自己的口述之外,你从哪些其他途径获得了你父亲的情况?
邓贤:这段尘封的历史年代久远,父亲的回忆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但是很亲切,很生动,你难以想象,他们那一代人当兵和参战的历史是那样鲜活,那样生动有趣。身在异国,又是与英美盟军融为一体,接触的都是当时最现代化的战争武器和技术装备,这些年仅十七八岁的年轻学子该是怎样的好奇、兴奋和充满迎头赶上的力量!父亲眼睛不好,他陆续写过一些回忆片段交我保存,成为我宝贵的写作素材。
我的《大国之魂》出版并引起广泛关注后,我逐渐认识更多的远征军老人,在成都和四川,他们经常不定期聚会,约有六七十人吧。这些老人基本上囊括了中国驻印军(学生兵)的各个军兵种,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奇经历,都有自己色彩斑斓的个人世界,我庆幸自己成为这些老人的朋友。他们是我深入这段历史的指路人。
读书报:本书105页你父亲参军时,和你祖父张松樵先生对话这一段让我很感动。
邓贤:我爷爷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赫赫有名的纺织工业巨头,他当然需要儿子作为庞大家业的接班人而不是去上战场打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是千百年来人们的传统观念。面对儿子的背叛,他当然不能不伤心和痛心。但是爷爷又不是糊涂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焉能不知道国家兴亡对于个人事业的重要性?所以爷爷在儿子的坚定抉择面前终于让步了。
家族故事和冲突历来就是我最重视也最感兴趣的素材,豪不夸张地说,此前我的全部写作,十余部长篇和数十部中短篇都不过是“练笔”,都是为了最后的写作冲刺,也就是写作我的家族史系列做准备。
我的爷爷从七岁进城逃荒要饭,活到九十岁建立起一个拥有七座现代化纺织工厂并涉足铁路、矿山、银行和运输业的财富帝国,假如是在今天,他可能能在中国财富榜上排在前几名。而我父亲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所经受的苦难折射了一个时代。而我自己,则是喝着狼奶长大的“狗崽子”。无论爷爷还是父亲,他们的人生都充满传奇性。我对自己的家族充满感情,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会完全肯定他们和站在他们一边。作家,毕竟代表了社会的良知和理性。
读书报:你父亲的口述显示,他是1943年12月入伍的,而你的小说名是《父亲的一九四二》,那么,这本书中虚构和真实的内容分别有哪些?在两者的取舍上你秉持着怎样的原则?
邓贤:因为1942年是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的时间节点,而最早一批学生兵加入远征军也是1942年末,他们是被输送到盟军做翻译工作的。为了强调这个时间节点,我将父亲从军的日子往前提前了一年,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展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我认为类似细节的改动应当是允许的,无损于历史真实。
在创作上,我强调的是“本质真实”,即不局限于表象的和个人的真实,遵循文学典型化的原则。请注意,我这部作品是“长篇传记小说”,父亲这一个文学形象不仅仅属于我个人的父亲,而是整个“父辈”,即浓缩了父亲和他战友那一代学生兵的共同经历。在我对学生兵的采访中,接触了大量的个人经历和故事,我将它们浓缩在父亲和他的一群战友身上。因此在“父亲”身上,既有他自己的影子,也有他的战友的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已经超越了某个具体的个人,他应当是一代抗战学生兵的典型形象之一。
读书报:你父亲当年是战时重庆第一个报名参军的学生,正如你所强调的,远赴印缅作战的学生军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占20%,高中文化程度的占50%,这样一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军队,在二战时的英美盟军中也无出其右。你如何看待他和他这一代人的家国情怀?
邓贤: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规定在校生可免服兵役,这是出于政府对于人才的爱惜,是为了保留战后中国发展经济和科技的血脉。但是面对日寇步步入侵和国破家亡之际,学生们终于怒吼起来,纷纷投笔从戎,“十万学生十万军”就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到走出校园抗战救亡,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历程。知识分子应当“忧天下忧,乐天下乐”,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情操,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
读书报:正如你在书中所述,“四川王”杨森的儿子,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儿子卢乐礼等官二代,以及像你父亲这样的富二代都报名参军,这样的情形非常普遍,除了日寇入侵所造成的同仇敌忾之外,是否也有其他因素?
邓贤:从父亲来讲,他作为当时典型的“富二代”,没有沉溺于吃喝玩乐极尽享受的个人奢靡生活,其一是因为战争的环境所致,如果国家灭亡了,人人都是亡国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其二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品格在起作用。一百多年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到处割土赔款的历史和现实成为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培养基,国家衰亡的现实唤醒他们沉睡的心灵,即使是所谓“富二代”、“官二代”也无法脱离这种时代的精神气场。
战争结束后,这些曾经上过战场的学生兵们回到祖国,此时国共内战即将开始,蒋介石违背“抗战胜利学生兵将重返校园”的诺言,欲将他们送上内战战场。此时学生兵身上独立的人文品格发挥作用,他们纷纷以做逃兵的行动反对内战,反抗这种不讲信用的政府行为。据父亲说,他们战车营里的学生兵几乎全部逃走,那些军官领着宪兵大街小巷地捉拿开小差的学生兵。脱下军装的学生兵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机会,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选择回到学校重新学习。举个例子,在我认识的成都的印缅学生兵约六十多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具有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不乏国外留学归来的人才和国家级专家学者。我想这很能说明问题。
读书报:《父亲的一九四二》塑造了一个败类的形象“老庾”,在战场自伤以保命,胜利后迅速腐败中饱私囊,可见即便是学生军中,也有良莠不齐的现象。王树增在其《解放战争》中强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迅速腐败导致了最后的失败,在你看来,抗战期间的国民党是否相对“清廉”?
邓贤: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抗战年代的国民党政府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加上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战争压力也不允许个人欲望无限之膨胀。但是抗战胜利之后,作为胜利者的国民党政府一度权力失控,“接收失地”和“接收敌产”成为刺激各级官员和军官个人欲望膨胀的加速器,贪腐如强力腐蚀剂迅速瓦解了这个政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当是至理名言。古人云:“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艰苦的抗战成就了国民党政权,抗战胜利也成为终结这个政权的起点,历史的发展就是这句哲理的最好诠释。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群都不是绝对单纯的,所以学生军中出现一些败类也是正常现象,更何况在那样严酷的战场上,动摇、退缩和背叛应是我们自身人性软弱和人性缺陷的反映。老庾的出现,即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同时也是作者对那个旧制度下中国军队为何会出现那么多弊端、那么多不公平和黑暗现实的追究。在一个缺少完善制度和法治精神缺失的时代,要杜绝老庾们的产生是不可能的。老庾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掩卷追问,这不正是我们今天阅读“老庾”的意义所在么?
读书报:著名学者齐锡生在其《剑拔弩张的盟友》中强调,以往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英美的学者往往强调,印缅战场的最后胜利,主要归功于英美指挥官的指挥有方,而齐锡生先生则强调,中国将士的浴血奋战和巨大牺牲,同样是这场胜利的核心因素。作为多年从事这一领域写作并有多部著作问世的作家,你如何看待这种分歧?
邓贤:对于过往的历史,当事双方各说各话,当然强势一方声音大,久而久之就成为历史主流声音。印缅战场胜利是中美盟军共同努力的结果,缺一不可,如果一定要划分其作用的话,我想这样概括可能更恰当:美国出钱,中国出人。人与钱哪个作用更大,大家可以自己得出结论。印缅战场的各级地面指挥官以及作战军队主要都是中国人,美国人控制飞机和作战物资分配,另外总部里制定计划的都是美国人,后方修公路是美国工兵团,大致格局就是这样。
2005年我出席一个美国二战学会主办的研讨会,有中国学者向美国飞虎队老兵鞠躬,感谢他们帮助中国抗战,结果美国人反而很奇怪,说我们也是为美国打仗啊!我当时就感觉到,我们自己的谦恭度好像出了问题,美国人出钱出物资武装中国军队不仅仅是“帮助”中国抗战,他们更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了减少美国军队的人员伤亡。
抗战时期,中美两军因为共同的战略利益结成盟军,一道完成反攻印缅乃至于最后打败日本强盗的伟大任务,记住这段历史当然是为了告知未来,不要重蹈纵容侵略者和法西斯强盗的历史覆辙。请有理智的读者不要忘记下面这个历史事实,在抗战初期和中期,在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炸弹落下来之前,美国人一直公开和暗中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废钢铁、战略能源物资和军火供应商,大发其战争财。这一时期日本人杀死中国人的子弹和炮弹,包括日本飞机轰炸中国城市的炸弹,很多都来自美国本土的军火工厂。正视历史只是为了牢记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记者:据我所知,有很多在滇缅战场作战的抗战老兵流落异乡,有的在国内也晚景凄凉。你在书后也提到,你父亲和他的战友大多数重返校园,走上了知识精英科学救国的道路,但他们后来遭受了不公平待遇,那段慷慨悲歌的光荣经历反而成了历史污点。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有关部门向所有参加抗战的离休干部颁发荣誉勋章,你的父亲和他的战友却无一人获得。作为后来的观察者,你如何看待?
邓贤:我的全部写作,浸透热泪、心血和感情的文字不正是为我的父辈们——不仅仅是我的父亲而是那群渐行渐远的老兵们颁发军功勋章么?我相信,历史会记得他们,会有更多年轻人把鲜花献在他们的墓碑跟前。(本报特约记者 牟尼)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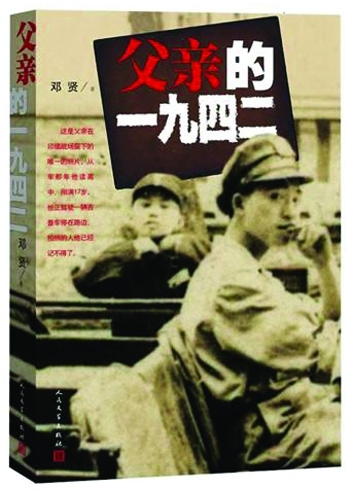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